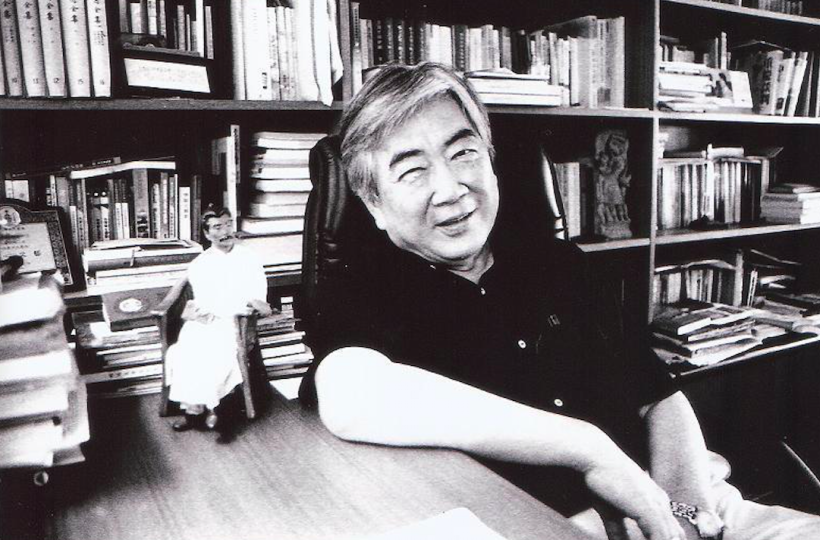然而,趙剛這一系列的文章,卻往往有過度詮釋之嫌。這些文章描述出來的「思想意涵」並非不佳,但看起來更像是趙剛本人披著陳映真的外皮在說話,而不是合法合式的文本分析結果。那樣的解讀,似乎預設了一種沒有時間性的、神學一般的知識體系,彷彿陳映真不是一個在思想上會成長和變動的知識份子,他一生下來就是戰後台灣思想最深邃的左派了,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對陳映真的傳記資料略有認識的研究者,大概都不可能同意這種讀法。畢竟陳映真1950年代開始與台籍作家往來、進入文壇、認識日本左派人士淺井基文、乃至於入獄親炙許多地下黨員,這都是有明確歷史軌跡的。很弔詭的是,最強調應「歷史地認識事物」的左派,閱讀陳映真時反而是去歷史的。關於趙剛詮釋文學作品的方法有何問題,我曾撰寫過〈為什麼過於熱愛作家是危險的:商榷趙剛的若干陳映真小說論述〉一文,在此不贅述。
陳映真有那麼「孤獨」嗎?
在〈「不合時宜的」陳映真文學〉這篇近作中,我們可以看到趙剛除了在文學詮釋的方法上有問題外,也過於輕忽了台灣文學史的基本成果,導致這篇講稿充滿了不可思議的錯謬斷言。
討論這篇講稿之前,我們必須稍微說明一下「文學研究」或「文學史」的基本性質。事實上,文學研究或文學史,是一門以「比較」為基礎的學科。在漫長的歷史當中,我們劃定出帶有某些特徵的作品,將之稱為「文學」,然後將這些作品、以及寫出這些作品的作家串連起來,編纂成一系列文學史。而這種編纂,並不是純粹客觀的史料收集,「有寫有保佑」的;這個過程其實充滿了研究者的價值判斷——這篇作品夠好,好到值得寫入文學史嗎?這名作家的表現,與其他作家的表現有何不同?他的特出之處何在?他有哪些形式上的創新或思想上的洞見?
所以,當我們討論任何一篇作品、一名作家時,一定要將它們放回文學史的脈絡裡面,去與已知的所有作品、作家來做比較。透過比較,我們才會知道他到底是庸才還是天才,作品是珠玉還是砂石。
由此回看該文,「陳映真是台灣當代文壇上唯一賡續五四傳統的一個作者」一節,就頗讓識者愕於其信口開河的程度了。在這一節當中,趙剛試圖描述出一個「五四、魯迅、傳統中國文學」三位一體的文學傳統,並且認為陳映真是當代台灣文壇唯一繼承這個文學傳統的作家。但仔細分辨他所描述的這尊三位一體大神,其特徵也不過就是兩點:一、這樣的文學,往往是與政治目標深刻結合的,比如主張反帝、反封建。二、這樣的文學,有其道德上的核心,是「文以道而尊」的。
我們可以姑且不挑戰這三位如何能夠一體,但無法不問:這不就是寫實主義的文學傳統嗎?這種文學主張,無論在過去一百年來的中國文學史還是台灣文學史,都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光說台灣,日治時期就數度有作家以「為人生而文學,而非為文學而文學」為旗幟,來指導文學活動、創辦刊物、進行寫作。當他說陳映真是繼承這種傳統的唯一一人時,那可是信口開了一條黃河那麼大的河啊,這條黃河一瞬間就淹沒了以賴和、楊逵、呂赫若、吳濁流為首的一大票作家,淹沒了將五四之火接引到台灣來的張我軍。就算把範圍限縮到戰後,也至少淹沒了鍾肇政、鍾理和、葉石濤、李喬等人。
因此,趙剛的這個無知得理直氣壯的段落,就更讓疑惑他是真的如此無知,還是被某種政治判斷遮蔽了視野:
有沒有第二人?當然有,我上面列舉的就不只二人了。但我們或許可以寬容地理解,其實他所謂的「道德性、時代性、思想性、政治性」,是限定在「左派-統派」的組合當中的。趙剛真正想說的是,在這條左統的路上,陳映真是唯一一人,因而是「魯迅-五四運動-傳統中國文學」這尊三位一體大神的孤獨繼承者。畢竟我們大概可以理解趙剛心目中的價值階序:只有左派稱得上理想,只有統派稱得上值得追求的政治,這是他所定義的道德與時代。正是在這個歷史脈絡下,我們得以描摩陳映真的文學實踐的核心精神樣貌。陳映真文學是魯迅、是五四,也同時是一種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在當代台灣的孤獨繼承。「孤獨」並非修辭,而是一個歷史事實的描述。我們只需以這樣的一個提問即可作為充分的回答:在戰後台灣的這半個多世紀以來,除了陳映真,能找出第二個如此嚴肅面對文學的道德性、時代性、思想性,與政治性的文學創作者嗎?
我當然完全不同意此一價值階序,但我願意暫不在此進行挑戰。我只想推薦一位完全符合上述條件的作家,既左且統,其作品在「道德性、時代性、思想性、政治性」都有深刻的表現。而且也完全繼承了那尊三位一體大神的文學傳統。(只是他還有很多來自別處的養分)
那名作家叫做郭松棻。一名我不知道為什麼,明明文學成就更高、思想訓練更紮實,卻總是被台灣的左統忽視的作家。在他的小說作品裡,〈月印〉寫的正是左翼在白色恐怖中的潰敗;〈秋雨〉寫了自由主義者的終局;〈雪盲〉和《驚婚》有著明確的魯迅線索。在政治活動上,他投入保釣運動,喊出了將保釣運動連結五四運動「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精神的口號。在文學創作之外,他更有一系列探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文字,明眼人一望即知,他在左派哲學上的浸淫有多深。去年底出版的《郭松棻文集:保釣卷》和《郭松棻文集:哲學卷》兩本書,都能夠證明上述的歷程。
本文的目的並不在介紹郭松棻,只是希望透過這一名幾乎為了趙剛上文量身打造的反例,提醒論者:在你粗率幫你熱愛的作家加冕,宣稱他在文學史上是各種「第一名」或「唯一一人」的時候,請你確定自己盡了最基本的資料爬梳義務。當你說:「陳映真長期以來對於日本的關注,我想在台灣的思想界與文藝界裡是少有的堅持的。但整個島嶼的知識潮流是反向的,也就是拒絕把對於台灣的自我認知拉到日本殖民時期」,請你不要忘記鍾肇政、李喬的大河小說,不要忘記陳千武的《獵女犯》。當你說陳映真首先「檢討了台灣初生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城鄉移民與貧困議題」時,請你不要忘記台灣在1930年代已經有過一次資本主義社會的繁盛期了,呂赫若早就寫過〈牛車〉,楊逵的〈送報伕〉已經遠赴東京,而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已經痛苦過了。當你說陳映真「首先探討了所謂『外省人』與『本省人』的關係」,請你記得先上網google一下吳濁流的〈波茨坦科長〉。
陳映真當然有其成就,但其他台灣作家也並不都是死在那裡沒有動作。
陳映真是不是一名現代主義者?
在〈「不合時宜的」陳映真文學〉一文當中,趙剛糾結於另外一個問題上,即:陳映真是不是一名現代主義者?從他處理這個問題的方式,我們可以再一次看到他過度輕忽文學知識而產生的謬誤。
在趙剛預設的框架裡,「現代主義」乃是一個貶義詞,代表了西方的主流霸權、重視形式輕視思想的文學流派,因此他當然極力否認陳映真與這個流派的關聯性。這再一次證明了,趙剛安置陳映真的框架,其實就是很普通的寫實主義。這仍然不脫張誦聖在《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中設定的「寫實主義對抗現代主義」文學史框架,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然而,趙剛的區辯並不完全正確。
作為小說家,陳映真確實不是現代主義者。如果我們回到現代主義最根本的精神,即「銳意創新,對傳統的創造性破壞,旨在透過『新』來震撼讀者」的話,台灣並沒有太多作家符合這個條件。不管是在1930年代,從日本引進的新感覺派;還是在1960年代,台大外文系系統引進的英美「現代主義」,其實都不是真正的現代主義。關鍵就在於「引進」二字:如果現代主義的根本精神是創新、是反傳統,那你引進一套別人寫過的東西,照著那個方法寫,如何能宣稱自己是現代主義?這裡面沒有任何實驗性可言,因為大部份台灣作家只是重做一次別人早已成功的實驗。
在這個定義下,王禎和、七等生、舞鶴、施明正、王文興等作家,或許比較可以算是現代主義者,因為不管成就如何,他們確實在某些層面上創造了新事物、背離了某種文學傳統。但像是白先勇這樣的作家,無論其自我宣稱如何,他其實是沒有現代主義精神的,我們可以輕易地在他的作品中找到福克納的影子。但麻煩的是,他雖然不是現代主義者,但他有著「現代主義的外型」——因為他挪用了英美現代主義者研發出來的寫作技術,寫出了有同樣特徵的作品。
我們只要抽換幾個動詞來想這件事,輪廓就會很清楚了:
1.有一名作家非常創新,發明了寫法A。因為他的創新,所以被稱為「現代主義者」。
2.另一名作家學習了寫法A,寫出了自己的小說,因此也宣稱自己為「現代主義者」。
很顯然,2.的陳述是有問題的。1.的作家,並不是因為寫了A才被稱為「現代主義者」的,而是因為他創新;在這個意義下,2.並沒有創新任何東西,所以不能這樣自稱。我們或許可以稱他為「擅長A寫法者」。因此,我們可以說白先勇擅長「意識流」手法,但白先勇並不是「現代主義者」。
以此來區辨陳映真是否是現代主義者的問題,答案就很清楚了。趙剛大可不必煩惱:陳映真本來就不是現代主義者,因為睽諸文學史,他的創新程度並不大。但不管在思想層次上如何抗辯,陳映真早期最好的作品,就是帶有過去某些現代主義者研發出來的「寫法」,比如〈麵攤〉裡那顆「橙紅的早星」,〈蘋果樹〉裡癲狂的思緒流動。而且,正是因為這些趙剛所鄙夷的「形式」,才使得陳映真的小說勝過1960年代前後的大部份作家(特別是台籍作家)。當陳映真出獄,開始「華盛頓大樓」一系列寫作,力圖滌清作品中的「現代主義式寫法」時,反而使他的小說來到拙劣不堪的生涯低點。
因此,在一個文學研究者看來,趙剛無疑熱愛陳映真,但他熱愛陳映真的姿態總有些古怪。為了意識形態上的要求,趙剛必須反對「美帝」,從而必須反對「美帝的文化霸權:現代主義」,所以總是努力地在作品詮釋中剔除陳映真的「現代主義毒素」,希望這名作家只剩下純粹的「思想」。然而,弔詭的是,趙剛的閱讀感畢竟是敏銳的,那些意識形態的雲霧並沒有辦法遮住他最誠實的感覺;筆下說不要,讀起來倒是很老實。趙剛在《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的自序中就提到:「陳映真這個名,與以此名出之的小說,以一種我所不能理解的怪異力量,引出了二十出頭的我的那點微薄得可憐的熱情。」這種「我所不能理解的怪異力量」是什麼呢?不多也不少,那就是文學,就是形式帶來的神秘經驗。那是純粹的思想著述不會有的(在這方面,趙剛比陳映真高明非常多),那是困於語言而顯得笨拙的鍾肇政、葉石濤這些寫實主義者也不會有的。如果不是這樣的「形式」,恐怕趙剛也不會開始閱讀陳映真,正如他不會去閱讀差不多時期當中,才份不如陳映真的鍾肇政等人一樣。
誠實面對自己的感覺吧。喜歡陳映真的小說,真的不需要找那麼多外圍的藉口來壯膽。同樣的,想要發揚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民族認同,也不必塑造一位假的先知來壯膽。放過陳映真,也放過自己,好好地自己把自己的話說清楚吧。
(刊載於「鳴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