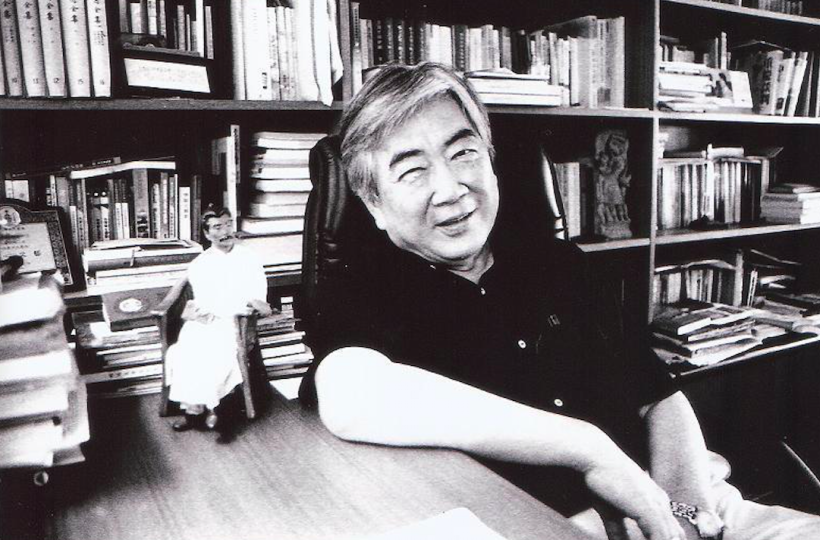(作者記:我在網路上發表〈趙剛教授,您或許還是需要一點台灣文學〉一文後,趙剛寫文章「回應」了我的說法,並語多輕薄。因此我也在臉書以長文回應,此即當時的回應長文。
首頁選了陳明成《陳映真現象》,略記當年「準備了但沒派上用場」的材料。)
說好的回應來了。我怕如果再拖下去,哪天我家三叔公的小姨子曾經上過趙剛教授開的通識課並且得到八十七分之類的往事就要被翻出來了。這時不免慶幸我沒什麼家世可言,可見的家人既沒有跑社會運動的,也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文人」,不必也來被摸頭一番。
這篇文章有點長,因為有三個問題,而且第三個問題要引用的文本不少,所以我會以網誌的形式發表。以下的前兩個部分,依序就是趙剛教授問我的前兩題,而第三題牽涉較廣,因為內中涉及許多創作者的心法和技術,我即使盡可能扼要講解,篇幅大概也短不下來,所以寫超過一節的說明。
如果有人已經忘記趙剛教授問我什麼的話,可以見底下的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693844484102396&id=100004305516738
跳過前面六成篇幅的暖場,就可以看到那三個題目了。
而這三個題目,又是從我這篇文章裡面出來的,建議先讀完,才會比較看得懂我在幹嘛:
http://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7344/1942888
好的,接下來我要開始補充這三個基本不會影響我們論點的問題了。
一、關於「現代主義」
事實上,這是我的一個失誤。在我的原稿當中,有這樣一段話,認為「現代主義最根本的精神」是「銳意創新,對傳統的創造性破壞,旨在透過『新』來震撼讀者」,以此作為判准,認為陳映真不是現代主義者,因為他並不是抱持著這樣的精神來創作的。在我的原稿當中,這段話是有加註腳的,標明了這個說法來自彼得・蓋伊的《現代主義異端的誘惑:從波特萊爾到貝克特及其他人》,正如有些朋友已經看出來的那樣。但文章刊出之後,我自己疏忽了,沒有特別請編輯把此書的連結或註腳放上去,所以看起來很像是我自己編造了一個奇怪的說法。
在《現代主義異端的誘惑:從波特萊爾到貝克特及其他人》一開頭,彼得・蓋伊就指出:
雖然有種種具體可觸的差異性,但各方各面的現代主義者皆分享著兩種決定性的態度⋯⋯第一是抗拒不了異端的誘惑,總是不斷致力於擺脫陳陳相因的美學窠臼;第二種態度是積極投入於自我審視。(p.21)
很顯然地,我那個追求「創新」的說法,出自他所說的第一種「決定性的態度」。他更進一步補充:
我提到的第一種態度(即抗拒不了異端的誘惑)完全不讓人陌生。現代主義詩人給傳統的格律傾注淫穢內容;現代主義建築師在他們的設計裡把所有裝飾給取消掉;現代主義音樂家蓄意破壞和音對位的傳統音樂規律;現代主義畫家的作品乍看之下就像是草草畫成而未經修飾的。這些人不只樂於走別人沒有走過的道路,還以顛覆主流的清規戒律為樂事,就像是創作激進作品的一半樂趣來自於擊敗反對勢力。『給它新!』(Make it New)——這個洋洋得意的口號是龐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前向同道叛逆者揭櫫的,而它也扼要總結了一個世代以上的現代主義者的志向。(p.21-22)
在更前面的段落,也提到:
現代主義者整體來說都要更熱衷走向極端,都是不熱衷於政治或學說上的中道。不管喬哀思或馬蒂斯這些重要人物有多自由主義取向,很多現代主義者都認為『走中道』既無聊乏味又布爾喬亞調調(這兩個罵名被許多現代主義者當成同義詞使用)。這並不讓人驚訝,因為幾乎就定義來說,現代主義者都是義無反顧的冒險家,更喜歡走在美學安全界線的最前緣,甚至超越。(p.19)
以上段落,來自本書的導論。而這本書的結構基本就是在上述兩種「決定性態度」的基礎上,再分章細究繪畫、文學、戲劇、音樂、電影、建築等領域的細微差異。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能夠說服我的說法,很好地概括了我所知的現代主義者,因此時常引用。
但也如同一些網友的反對意見所說(比如廖啟余),這樣的定義並不能說清楚「現代主義」的內涵,並且也似乎忽視了它傳入台灣之後,在地化的過程與脈絡。
這我同意。然而我要說的是,當初援引這個定義,只是要暫時解決「陳映真是不是現代主義者」這個命題,因此我的思路很簡單:找出一個「現代主義」的「必要條件」,然後指出陳映真缺乏這個必要條件,那就結案了。這也是為什麼彼得・蓋伊提出兩種決定性態度,我只引用了「創新」的原因。而我從未宣稱「創新」是「現代主義」的「充分條件」或「充要條件」,因而一時很難理解趙剛的回應為何會拉出「莊子、離騷、史記、人間喜劇、莎劇」這一排作品。
當我說「人類有心臟」的時候,並不是在主張「有心臟的就是人類」啊。
當然,彼得・蓋伊的說法並不是無可質疑的,這幾天的各方討論,也讓我受益良多。或許可以再多說一點的事,「創新」其實是一個比較性的詞彙,「新」是相對於作家所面對的「舊」,所以衡量一名作家寫成了什麼樣子可謂之「創新」,應該要看他的作品與他所處的時代能接觸到什麼文學資源來對比。因此,在我鳴人堂的原文當中,我舉出的對照組就是白先勇。從1960年代台灣的中文小說來看,他的意識流手法確實是新的,但我們可以看出他優秀地繼承了幾位西方小說家的技巧,並且確實寫得很好。然而,那畢竟是「繼承」的,在精神上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創新;即便他有著標誌性的技巧。相較於(包括但不止於——我從來沒想過,我只是舉幾個例子,竟然還會被曲解成「誰說只有這幾個」)王文興、王禎和、施明正等人,他們雖然也是挪用西方的技巧,可是他們都在這個基礎上,更徹底地把中文小說變成了別的樣子,更貼近前引的「決定性的態度」。
另外一個可以作為對照的是,當1968年白先勇出版了《遊園驚夢》的同一年,鍾肇政也出版了《中元的構圖》這本他生涯罕見的現代主義作品。根據他自己的說法,這正是受到了1960年代文壇上流行「現代主義」的刺激,所以抱著一種「證明我們也會」的心態去寫的:
事實上,我對《台灣文藝》的創刊滿心期待到了興奮莫名的地步,除了可以有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學雜誌,可解決許多作家發表問題之外,同時也是因為可以寫實驗性作品。好比「現代主義」技巧即其一──其實當時被某些人士所提出來的所謂現代主義,充其量只是類乎意識流手法的技巧,早已落後在西歐現代主義之後不啻數十年。而我在「自由中國文壇」開始有了上述的所謂現代主義萌芽以前,即試寫過若干意識流作品,均到處碰壁,未獲發表機會。有了《台灣文藝》,我認為當然可以在這方面試試身手了。故而當吳老要我至少也要隔期交一篇小說稿,我便也欣然應允,並將土俗與現代結合,懸為我這方面作品的實驗目標。(鍾肇政〈鐵血詩人吳濁流〉,《鍾肇政回憶錄(二)文壇交遊錄》。台北:前衛出版社,1998,頁77-78。)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另外一條本省的、連接1945年前後的,「現代主義」(技巧)的受容線索。但我們會不會因此說鍾肇政是一名現代主義者呢?(或至少,曾是?)我個人是不會,因為這還是繼承來的。在我看來,「創新」仍應是此一傳統的最根本精神,只是所創何物可稱之為新,必須考量台灣當時的脈絡,而不是用西方的標準來衡量。
由此,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考量趙剛教授〈「不合時宜的」陳映真文學〉關於現代主義的段落,很明顯地,整個行文邏輯是把「內容」(關於文學所表達出來的倫理關懷)和「形式」(作家對文學作品之自為價值的經營——或,我們前面提到的現代主義「技巧」)對立起來的。但這樣的對立是有道理的嗎?能夠拿來解釋陳映真嗎?不妨看看以下兩段文字:
1.
問題不在於「現代」或「不現代」,不在於「東方底」或「國際底」,不在於「禪」,不在於「靜觀」,不在於⋯⋯問題的中心在於:「他是否以作為一個人的視角,反映了現實」。文藝是現實的反映;而反映現實的製作者,是人;是一個具備了思考、愛和批評能力的人。文藝的形式歷有有變革,但作為思考的人的那種追求人的完全的心靈,卻永未間斷,而且——因為我的某種樂觀——,應該奔向一個更高的層界去的罷。
因此,走進形式主義的空假以及思考的貧困的現代主義之錯誤,之不足取,固然十分明顯,但對於這種錯誤採取機械性的批評,也是錯誤的。現代主義文藝,因為要反映「現代」這一個未曾有的特殊現實,而必須要求適當表現這現實的特殊形式。當內容和形式完全統一的時候,被商業化了的、硬變了的、迷信化了的「現代」,便消失了。現代主義文藝,便在這一個觀點上,被承認了它一定的存在價值,對它做無分別的、教條式的攻擊,是不正確的。
2.
他大體上是屬於思想型的作家。沒有指導的思想視野而創作,對他是不可思議的。然而,他認識到、並且相信,創作有一個極為細緻而有一定程度自主性的領域。真正的創作之樂,也在這個神奇的領域。
這兩段都在講「形式」與「內容」必須調和,並且文學不能丟失掉二者其一的文字,我完全同意,但都不是我講的。我想趙剛教授必然清楚,這都是陳映真自己講的。第一段來自〈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演出《等待果陀》底隨想〉,第二段來自陳映真描述自己創作歷程的〈後街〉,那是他的自我定位。如此看來,陳映真本人是否是個現代主義者,或許我們可以再談,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陳映真本人對於文學形式的經營,對於那種現代主義的「技巧」本身並非深惡痛絕。他只是覺得兩者應該高度統合而已。
二、關於「當代」的分期問題
第二題,是關於文學史分期的問題。
首先,台灣文學史需不需要分期?當然需要,為了教學和研究的方便,分期是必然的。但趙剛教授可能不清楚的是,在一般台灣文學史的討論裡面,並不會很頻繁的使用「現代」和「當代」這樣的劃分。粗略一點的話,我們可能會以1945年為界,那之前稱之為「日治時期」,那之後稱為「戰後」或「國府時期」。如果要再細分,日治時期還可以以1937「禁止漢文」為界,大致區分出漢文、日文為主流的兩個時期。而在戰後,也有一系列大致以十年為框架的粗略標籤,比如「1950反共、1960現代主義、1970鄉土文學⋯⋯」之類的分法,或者以「解嚴」做為分界線,去談解嚴前和解嚴後。
而通常是誰在用「現代」和「當代」的區分呢?通常是中國。中國學者高玉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反思》一書中,就以〈當代文學及其「時間段」劃分〉這個專章討論了相關定義的問題。在中國普遍的通說裡,大致是將1919年-1949年視為「現代文學」,然後將1949年視為「當代文學」。(p.154-156)
正如趙剛教授所說,這些文學史分期有其理論意涵和政治預設。「當代」真正的意義,是「跟我們所處的此刻,屬於同一時期的上限時點」。在中國,我們可以看得出以1949年為界,是有它的脈絡和合理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確實是一巨大的、對文學走向有大規模影響的事件。但在前引的高玉也提到,他認為「當代」這個分期應該要隨著時代的轉變一直往前挪移,他就主張把「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給「切出去」,劃為「現代」。(p.156)
而在台灣,我們顯然並不能率然採取1949年這一分界。這一年是中華民國政府敗退來台,帶來二百萬軍民的一年。然而台灣島上不是只有這個政府帶來的二百萬人,況且中華民國政府早在1945年就開始了對台灣的實質統治,如果這樣切分,1945-1949這四年,就會形成曖昧的模糊地帶。而在1945之後,如果我們也要把某個時段「切出去」,會有非常多種可能的選擇。比如說,我可以主張1960年代的現代主義風潮至今仍影響我們的文學品味,所以從1960年《現代文學》創刊起算;或者我也可以說,本土化浪潮是至今最具影響力的力量,所以我從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起算。每一種切分都是可能的,但就看解釋力如何,有沒有必要這樣切。
因此,當趙剛教授說「台灣當代文壇」的時候,我其實不太知道這確切指涉的年代是什麼。所以在我原文的舉例裡,我選擇了9位作家,這9位作家的活躍時間,基本上橫跨了1920到1980之間——是的,我就是在亂槍打鳥,因為我根本不知道鳥在哪裡。
當然,「當代」一詞在台灣文學研究領域不是沒有人用,但並沒有一個比較統一的用法,目前的幾個用法,怎麼看都不像是趙剛教授所指涉的年代。陳映真一鳴驚人的〈麵攤〉發表於1959年,高峰〈山路〉在1983年,大部份的小說也都寫於這兩個時點之間。但在目前的台灣文學研究裡,切起來都不太合身,比如許琇禎《台灣當代小說縱論:解嚴前後》是從解嚴前十年起算(1977),陳國偉《想像台灣——當代小說中的族群書寫》是從解嚴起算(1987),劉乃慈《奢華美學:台灣當代文學生產》是從1990年代起算。如果是採取許琇禎的劃分,那會切掉陳映真早期的小說;依照劉乃慈的劃分的話,那陳映真就只剩下三篇小說了,呃,而且還不是代表作,基本上就沒他的事了。
所以趙剛教授的這個問題,我的簡答是:文學史當然需要分期,但未必是要用「現代」、「當代」來劃分。如果真的很喜歡「當代」這個詞也無不可,只是在台灣的脈絡下,我們不適宜跟著中國的分期來走,畢竟兩國有非常不同的歷史經驗。
而這一切會不會影響我們的論題呢?完全不會。因為我舉例的9位作家,基本上可以包覆與陳映真有關的所有時期了,不管趙剛教授的「當代」在哪裡都沒差。在這些時期裡,陳映真都很難說是唯一「嚴肅面對文學的道德性、時代性、思想性,與政治性的文學創作者」。
三、關於「華盛頓大樓」系列的評價(上)
在這一節,我要先來談談我進行「文學評價」的標準。也就是說,我是用什麼依據來判斷一篇小說寫得「好不好」。以及,我對陳映真小說作品的大致評價。
需要先說明的是,以下的評價,跟學者的觀點可能會有很大的差異。包括台文所在內,大部份學院論述的要求,是看能夠從文學作品中析出多少思想、議題上的「意義」。但能夠析出意義的作品,不見得是好作品——從作者端來說,它可能手藝很粗糙;從讀者端來說,它可能讀來索然無味。我個人經驗中,最能體會到二者分離的例子,就是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每一頁我都可以看到好多分析的切入點,但小說實在很難看;你可以看出作家超認真在查資料跟埋藏歷史線索,但身為讀者,我比較希望作家認真把小說寫好、把文字磨好、把佈局弄得漂亮一點。
這種「學者觀點」,在實務上很容易產生一種效果,就是「對作者寬容、對讀者嚴苛」。因為擱置了文學評價的價值判斷之後,理論上任何文本都能夠榨出意義了,都可以延伸出非常多外圍議題。但與其說這是作家的貢獻,不如說是展示學者很會讀。而先帶著學者觀點的進去讀,也會忽略掉「作家可能寫壞了」的可能性,而費盡千辛萬苦在劣作裡面榨汁,比如陳映真早期的〈獵人之死〉、〈蘋果樹〉,就很明顯屬於習作,讀來覺得晦澀難明,是因為他真的沒講什麼。這時你硬要榨,只會讓自己累個半死而已。這種等級的作品,換個名字拿去投稿現在稍有水準的高中校園文學獎,恐怕是完全沒有出線機會的。
因此,在進行文學評價的時候,我們預設的會是一種「知道得沒那麼多」的讀者,以此去推想,此一文本可以「合理」地「解讀到那裡」,或被「享受到哪裡」。之前有人認為,我談論陳映真終究只是紙上談兵,因為我不認識陳映真本人、缺乏很多讀解的脈絡。這讓我有點啼笑皆非,如果照這個邏輯,文學系所的必修課應該是觀落陰。事實上,如果我意外得知某作家的八卦,而這八卦又是不能公開、未曾公開的資訊,普通讀者無法取得的話,那我就會判定「這不是讀者應該知道的」,從而在評估此一文本時,刻意地忽略這個資訊。
因此,幾年前的拙作〈為什麼過於熱愛作家是危險的: 商榷趙剛的若干陳映真小說論述〉當中,我雖然指出趙剛對〈祖父與傘〉和〈我的弟弟康雄〉是過度詮釋的,但我在文章中也提到:我承認這些解讀是「有可能」的,陳映真真的可能是這樣想,但從小說文本本身和目前的資訊看起來,我們無法確證此一可能性。——這一附加說明,就是上述思路的產物,因為我並不知道趙剛教授是否知道什麼我不知道的;特別是陳映真的許多小說往往是有所本、有所影射的。
如果大致要列出我的標準,依序大概會是:
- 在技術上,是否能夠盡量減少失誤。所謂失誤,包含角色塑造、情節邏輯、敘事觀點的合理性、文字的基本表現之類的。
- 能否巧妙運用小說的「形式」,來增幅「內容」的威力,達致兩者之間相輔相成的狀態。
- 能否發揮小說此一文類的特長,寫出「只有小說能寫的事」。
這三個標準是有不同權重的。一般來說,能做到越下方的事情,我們就會給予越高的評價,就算它在上方的失分太多或得分不高也一樣。
以此來說,我認為陳映真較優秀的作品,至少有:〈麵攤〉、〈我的弟弟康雄〉、〈文書〉、〈將軍族〉、〈淒慘的無言的嘴〉、〈一綠色之候鳥〉、〈兀自照耀的太陽〉、〈鈴鐺花〉、〈山路〉等篇,特別是〈山路〉,基本上寫出了他在台灣文學史上無可動搖的地位。(不要再相信沒有根據的說法了,台文系所從來沒有忽視過陳映真的重要性;早期有些程度很差的台派民間學者,確實不喜歡陳映真,但那些人也早就不是台灣文學研究的主流了。)
作為第一篇作品,〈麵攤〉是令人驚艷的作品。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作家有不錯的佈局概念,比如那顆「星星」出現的次數顯然是經過計算的,讓它能夠形成讀者必然不會忽略的象徵物。另一方面來說,我們也可以看出作者生澀之處,比如在第二節末尾,作者透過一個強行插入的括弧,生硬地置入「星星」這個意象:「(唉!如果孩子不是太小了些,他應該記得故鄉初夏的傍晚,也有一顆橙紅橙紅的早星的。)」這裏的假設語法(如果、應該)顯示了作者沒有能力安排一個自然的場景,來讓這個重要的象徵「星星」出場,只好出此下策,產生了結構上的突兀。這種失誤,就屬於前列的1.。但綜觀全局,我們又知道「星星」的第二次出現是必要的,否則就沒辦法醞釀出結尾「橙紅的星星=血紅的煙蒂=孩子的生命」一同殞落的爆炸性情感。前面必須至少鋪陳兩次,才能帶給讀者足夠的暗示,注意到第三次的情緒破口。所以在整體佈局「戰略」上,這是對的;但塞進去的手段不好,是個「戰術」上的失誤。而此一「戰略」的正確認識,就屬於我說的2.,因而小疵不掩大瑜。
而什麼是3.呢?大約就是〈淒慘的無言的嘴〉結局處,那種在醫師和敘事者之間流轉的詭異心思;或者是〈一綠色之候鳥〉那句撼動人心的台詞:「⋯⋯能那樣號泣的人,真是了不起呵!」(小抱怨:如果沒有「呵」,在2016年的讀者看起來會更順眼一點);或者〈兀自照耀的太陽〉和〈山路〉裡面,那種決然地奔向死亡的,神秘而又誘人的一探的絕望。
3.是一個比較抽象的觀點,但我想趙剛教授並不是一名沒有感知能力的讀者(不然就不會熱愛陳映真如斯了)。它基本上是一種難以用後設語言去捕捉的瞬間,知者能夠清楚感受到其存在,但無法轉述。而與其相反的,就是過度直白的、大量的後設語言,形成的一種「說明」文字。當小說開始「說明」,而不是「演出」或「鋪排」的時候,這篇小說基本上就要墜毀了。(當然,也有例外,比如張亦絢的《永別書》,但那是極為罕見的例外)
四、關於「華盛頓大樓」系列的評價(下)
承上,我們可以來談談「華盛頓大樓」系列了。
這個系列,由四篇小說組成,依序是〈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雲〉、〈萬商帝君〉四篇。這一組曲,首要探討的主題,就是關於美國的資本主義力量,如何透過跨國企業的商業模式,滲透、扭曲了台灣人的心靈。這四篇小說的共通點,就是他們的男性主人公(這很重要,都是男的,因為女角另有功能)都在這棟「華盛頓大樓」裡的某間美國公司工作過,整個故事的過程,就是描述他們如何或與美國-資本主義對抗、或被收編、或被玩弄的故事。
這四篇小說,如果真要說哪篇最好,我選〈上班族的一日〉,其次是〈夜行貨車〉,這兩篇勉強算是陳映真有失誤、但不算太糟的作品。但〈雲〉和〈萬商帝君〉則都有著慘不忍睹的硬傷。
首先是〈上班族的一日〉。這篇小說的梗概是四篇中相對簡單的:
主角黃靜雄在外商公司拼命工作,因為他的上司承諾讓他升副經理,卻被台灣這邊的老董搓掉,安插了自己的人。主角盛怒之下,跟上司大吵一架,蹺班一天。原本打定主意不管上司如何挽留都要辭職,去完成大學時拍紀錄片的夢想。卻在結尾處因為局勢逆轉,被安插的人不願意上任,讓他重又放棄夢想、乖乖回到公司。
這篇小說在技術上沒什麼問題,由於人物、時間、場景都嚴格鎖定,敘事觀點也沒有亂飄,除了某些時候概念太直白淺陋地說出來,略嫌生硬以外,大致上沒有什麼失誤。(生硬處如在觀看25歲的結婚影片時,心裡想「為什麼那時候的生活裡,充滿了另外一種力量?」——這句對白不能直接用說的,要想辦法在場景描述中,自然建立起來。)雖然以2.或3.的標準看來,並沒有什麼特殊表現,不過也是不過不失,中規中矩。
〈夜行貨車〉講的是一段複雜的辦公室三點五角戀情。已有家庭的林榮平,跟他的秘書劉小玲有性愛關係;劉小玲又愛上了公司裡桀驁不遜的新秀詹奕宏,並且懷了他的孩子。這幾位的上司是美國人摩根索先生,故事開場的爆點,就是摩根索先生性騷擾劉小玲,而林榮平又屈服於洋人上司而無力保護她展開的。
從這篇小說開始,我們會接觸到陳映真「華盛頓大樓」系列最大的硬傷,亦即許多不喜歡他的讀者所批評的「意念先行」。首先,我必須先澄清,批評陳映真的小說「意念先行」,是也對、也不對的判斷。對的部分是說,他的小說確實有這種特徵;但不對的地方是,他並不是因為這樣,才寫壞某些小說的,因為理論上,這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小說都是意念先行的,而這些小說有好有壞,無法一概論定。「意念先行」作為一種批評,意思是「寫作者在下筆前有了過於強烈的、缺乏彈性的價值判斷(簡稱:教條),導致寫出來的小說很生硬」。比如說,有個作家認為「同性戀是不好的」,所以凡寫到同性戀的角色,必定要在情節上「懲罰」之,為此寫出破壞結構的、不合理的段落也在所不惜,那就是「意念先行」了。但仔細觀看上述說法,真正的問題是出在「後續處理失當」,而不在「持有某種強烈的意念」上。小說家當然可以有強烈的意念,他的工作就是利用好的文字手段,把這些意念轉化成優秀的作品;甚至可以說,「意念先行」是小說書寫的常態,作為一種非常需要預先謀劃的文類,動筆前心裡有個底是正常的,只是你得找到一個好辦法來處理這些東西。當讀者抱怨作家「意念先行」時,其實真正讓讀者不舒服的不是意念本身,而是這些意念未經適當的調理,難以下嚥。
所以,我並不認為陳映真某些小說的失敗是因為「意念先行」。比如〈山路〉,其意念非常明確,就是一個同情白色恐怖受害的地下黨人的立場,但仍不妨礙他寫出台灣文學史上罕見的高峰。這篇小說從謀篇佈局、敘事口吻到文字的細微操作,都是難得一見的精品。
而〈夜行貨車〉的問題,就是陳映真不但意念先行了,而且還用非常粗劣的手段表達出來。隨著故事的進行,我們很快就會發現,唯一的女角劉小玲變成了三個男人的慾望投射點,這三個人都在「搶」這個女人。摩根索先生有權勢、林榮平有職務之便和舊情、詹奕宏則擁有有劉小玲的愛情,而貫串其中的爭搶關鍵,就在於個人意志與權力關係的對抗。因此,在小說結尾,懦弱而不敢對抗美國人的林榮平雖然保住了權位,卻失去了劉小玲。而在宴席上,因為美國人講出了「fucking Chinese」而暴怒,怒嗆洋人、然後憤而辭職的詹奕宏,卻在奔出會場之後,成功了爭取到劉小玲的認同,讓劉小玲願意捨棄赴美的機會,和他結婚、返鄉。
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意念先行」最糟糕的操作手法之一:他把複雜的權力關係和理論爭議,化簡為「誰有反抗的勇氣,誰就能抱得美人歸」。女性角色在這一系列的小說,有兩個常見的功能:
- 被洋人上司性騷擾,以象徵美國人對「我們」的「掠奪」。
- 作為有勇氣的台灣人的獎賞,從洋人手中把「我們」的「東西」「搶回來」。
這使得所有女角及其相關的段落扁平化了,她們的意志和決定都不重要,就算詹奕宏整天毆打劉小玲,前幾天還對懷孕的她拳打腳踢,就算美簽已經下來了,只要男人敢當場對美國人嗆聲,作者就可以把女人賜給你,完全不必在乎前面的情緒和動機是否連貫。為什麼?
因為作家有意念:他要獎勵那個敢對抗美國人的人。這個人先是個男人,所以我賞你個女人。
這裏的批評,不只是出於性別的政治正確而已。政治不正確是一回事,但這在文學效果上也是很糟糕的。這種寫法會把四個角色的互動圈線在非常平板的狀態裡,彷彿現實的複雜考慮都不重要,就只是有沒有(道德?)勇氣而已。但小說之為小說,正是因為它能把角色放進複雜的處境裡,讓讀者陪同角色一起面對困境啊。
就在這平板的模板下,就算是〈雲〉裡面那個開明的美國人艾森斯坦,在他的秘書端咖啡進來時,也必須「毫不掩飾地、安靜地注視著她輕微地隨著步伐跳動著的、她的渾圓的乳房。然後他無言地、惡戲地像張維傑眨眨眼。」而系列作的每個台灣人男主角,也非常工整地對應這個「獎賞公式」。〈上班族的一日〉黃靜雄最後屈服,他真正牽掛的情婦Rose也走了,而且是跟著一個「敢愛」的美國人走的。〈夜行貨車〉的林榮平輸了,詹奕宏贏了。〈雲〉裡的張維傑辭職,離開華盛頓大樓出去打天下了,所以他得到女工小文的日記(憂悒的少女的心啊),並且在結尾約會了自己的秘書朱麗娟。〈萬商帝君〉裡面每一個男角都屈服在美帝淫威之下,所以整部小說只有一個平庸的、無法引起慾望的女角Rita,而且跟任何人都沒有發生情感關係。
整個系列作也不過就四篇小說,如果只是重複寫同一型態的樣板人物,何必寫四次?更好的方式應該是從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呈現更多元的「眾生相」吧。
而在〈雲〉和〈萬商帝君〉這兩篇令人頭痛的作品裡,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低級失誤。從敘事結構來看,這兩篇小說都非常散漫,隨意插入的日記、長篇累牘的企業管理知識,三不五時就冒出來打斷敘事動力。
〈雲〉先做了一個「張維傑開了新公司,雇用了一名超棒的秘書朱麗娟」為外框,中段主要的情節是透過女工小文的日記,回想當年跟這群女工一起組織工會,卻內遭工賊抵制、外被洋人背叛的往事。整篇小說最好的一段,就是女工們的工會改選投票被工賊暴力阻撓,其中一名女工「魷魚」在大庭廣眾之下赤裸上身,讓其他男性工人礙於道德壓力不敢上前碰觸;乃至於整個投票失敗,小文哭著求大家就算不敢投票,能不能至少表現出大家的同情,結果整廠工人一起揮舞帽子的段落。在這裏,陳映真展示了他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在工賊與工運人士對決的刻板戲碼理,借力使力,寫出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讓人永誌難忘的情節。但可惜的是,張維傑與朱麗娟的段落完全是累贅,與主線情節毫不相融,如果不是陳映真硬要塞一個「獎賞」給張維傑,前後段落是一點必要性都沒有的。(而且如上所述,塞了更糟⋯⋯)我們完全可以想像,直接把工會事件寫成一篇完整的小說,會是更為緊湊的決定,但這樣就必須悲劇收場,沒辦法獎賞我們勇敢的張維傑了吧。而小文的日記雖然有輔助回憶事件之功,但關於小文私事的片段十分冗餘,除了再次打造一個「貧窮、上進、純情」的女工刻板印象之外,並無太多效果,幾十頁的日記大有壓縮的空間。——或者,為什麼非用日記不可?艾森斯坦訓練張維傑的段落,則連續抄了三頁的艾版管理學理論,這種會讓讀者的閱讀感瞬間失速的段落,更是會讓小說創作者眉頭一皺:你是在偷懶嗎?
是的,就是偷懶。因為在小說當中硬塞入理論、論述、資料等段落,這行為如同廚師直接把沒煮熟的食材塞到客人面前一樣。準此,〈萬商帝君〉的後半段,就是驚人的大規模偷懶。在小說的前段,雖然也會有零星的劉福金演講段落,但比例不高,還不至於太過枯燥。最有趣的角色,並不是刻板的「本省人劉福金vs外省人陳家齊」,而是壞掉的小人物林德旺。這個鄭清文式的卑屈人物一無是處,魯得十分入味,在金錢的誘惑與權勢者的冷待夾擊下,他的精神崩潰頗有可觀,很好地襯出公司內看似嚴整、理性、文明的「行銷」、「管理」體系,是踩在什麼東西上面的。如果這篇小說只留下林德旺的話,那還真沒什麼好挑剔的。
只可惜,陳映真志不僅止於此,他花了更大的篇幅,去寫整個公司如何「美國化」,被管理學的知識話語籠罩的轉變過程。這安排也無可厚非,但顯然還得花更大的力氣融合不同的主軸才行。開場安排了劉福金和陳家齊的對立,維持了一定的敘事動力,至少讀者會想知道他們要怎麼鬥。劉福金在提案時被陳家齊擊敗的戲碼,也保持了不錯的張力和水準。壞就壞在第六節,整整23頁劉福金的日記,鉅細彌遺地寫了那場企業管理研討會中,每個講師、每堂課講了什麼,然後偶爾穿插中美斷交的歷史事件和會議中吃了什麼。不要懷疑,就是23頁的企管、行銷講義。而這當中,真正具有小說感的,只有發瘋的林德旺衝進會場,吶喊自己是「萬商帝君」然後被攆出去,總計0.8頁。
你根本放棄了對吧。你何不直接印一段彼得・杜拉克給讀者算了?
用小說去直寫理論,這是揚短避長,你再怎麼寫都不可能比真正的專業書籍精到。而這樣的寫法,也放棄了小說之為一種文學形式的感染能力,你或許覺得自己傳達了重要的訊息,但無聊的東西只會讓讀者通通跳過而已。我不是主張小說當中不能置入知識,但是在文學作品裡,每個段落都必須有機地和其他段落扣連在一起,這樣硬塞只是一團油水分離的失敗品而已。
以上,簡略地說明我為何覺得「華盛頓大樓」系列是劣作的理由。當然,這只是舉一些比較大的問題,如果還有其他的疑問,可以隨時補充。
⋯⋯不過話說回來,就算我對「華盛頓大樓」的評價有誤,好像也不會影響到我原來的論點齁?
五、其他
最後,雖然我已回答了趙剛教授提出的三個問題,但說真的,我個人認為,這三個問題的釐清,對於我最初主要的論點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我還是要重申我的兩個論點:
A.陳映真並不如趙剛所言那麼「孤獨」、「唯一」,台灣文學史上是可以找到其他類似案例的。
B.陳映真並非一個具有「現代主義(創新)精神」的作家,但無疑地是能操作許多「現代主義技巧」的作家
而我之前也提出了三個問題,就教於趙剛教授:
1.
您是基於什麼樣的論據,去認定陳映真的「『孤獨』並非修辭,而是一個歷史事實的描述」?並且是以什麼樣的論據認定,除了陳映真,在「戰後台灣」找不出「第二個如此嚴肅面對文學的道德性、時代性、思想性,與政治性的文學創作者」?在我看來,幾乎就在陳映真發表〈山路〉同一時期,也發表了〈月印〉的郭松棻,是完全符合上述條件的。且不管我們對「當代」一詞有何分歧,這兩位小說家有一段活躍的時間是重疊的,這點殆無疑義。
2.
是否能夠更進一步說明,「中國傳統」、「五四傳統」和「魯迅」這三者如何能夠調和?在我看來,這三個標籤各自的內涵都十分複雜,雖然有可能取出「文以道而尊」這個三者交集之處,但一來這未必是它們最核心的概念(比如說,五四真的可以被如此化約嗎?),二來它們所在乎的「道」恐怕不是同一個。如果說只是蘊含了一個「道」,就能夠被視為等同之物的話,那這幾乎就可以包羅所有的文學上的寫實主義者,他們也都是在乎內容大於形式、在乎寫作的公共面相和倫理內核大於「藝術自覺」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在最初的文章中,會羅列那一群寫實主義者。
3.
承上,為何「現代主義」(在我做出回應前,您可以先採取您的定義),必然對立於上述傳統?事實上陳映真在文學形式的經營,並不妨礙他在小說中開展思想。在這一點上,郭松棻如如此,魯迅也是如此。在郭松棻的小說〈論寫作〉中,對於這兩造(但不只這兩造)之間的關係亦多有辯證。我倒不是要主張文學形式應該與道 / 德脫鉤(如您在文章中所預想的質問),我反倒是主張這兩件是不應脫鉤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陳映真才會是陳映真,而不是另一位思想同等精深,但未必能寫的學者。
在這篇長文裡,我補充了一些說法。但我希望下一輪的討論,不會又是從我這篇文章當中,抽幾個無關宏旨的細節來亂問一通了。要問之前,煩請先回到本源,好好處理上述兩個論點,或者三個問題吧。
然後,不用去查我三叔公的小阿姨了,他們真的沒念過這些書。
(原文載於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