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小說為何很難推向國際?——讓譯者面有難色的四個問題
2015/09/30 _時事雜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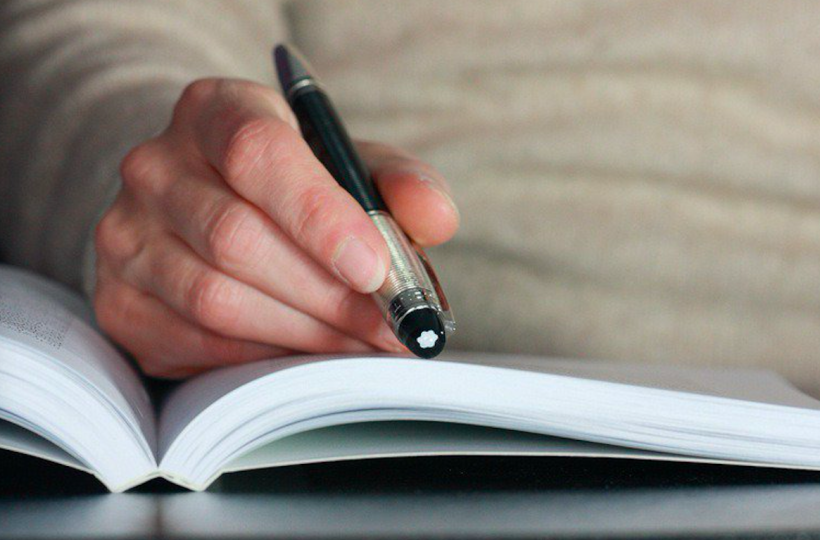
2015年的華文朗讀節剛剛落幕,而就在活動期間,我受到朗讀節其中一個團隊「譯動國際論壇」的邀請,參與了一場與國外譯者們的閉門會議,向他們介紹台灣近十年小說發展的概況。能夠向德、法、英、日四種語言的譯者推薦我心目中適合外譯的好小說,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我的推薦有多少說服力,不是我自己所能論定的;但在和這些對台灣文學有極高興趣的譯者討論的過程裡,我反而獲知了許多台灣的小說寫作者從來不知道的事,也許可以說是與會成員中收穫最豐的一人。
由於會議的形式自由,所以在我簡介了推薦的作品之後,有興趣的譯者就會對這本書的細節提問。從他們的提問和反應之中,我清楚地看到了譯者們在篩選「什麼樣的作品適合外譯」的細節考量,當我講到某些點的時候,可以很明確感受到譯者們是眼睛一亮,還是露出了為難的表情。除此之外,譯者們也提出一些他們對台灣小說的觀察,剛好也呈現了台灣小說和外國讀者的閱讀期待之間,有某種難以接軌的落差。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日文譯者天野健太郎體貼地指出:這些「落差」不應該成為一種指令,要求台灣的小說家必須往這個方向靠攏,這些問題只是他們長久閱讀台灣小說感受到的疑惑。但對我來說,我認為這些「讀者反應」是很珍貴的,無論小說家是否願意接受這些「國際標準」,多知道一些想法不是壞事;而對文化部、國藝會等政策部門來說,這些說法也比幻想追逐一個「同文同種」的,虛妄的「全球華文市場」要具體的多。
因此,底下的文章我將簡單整理譯者們提出來的一些問題,以及我對這些問題的回應。
問題一:為什麼你們要寫那麼長?
在我原來的簡報裡,每一本我推薦的小說,都會標明出版年份以及體裁,標明是「長篇小說」還是「短篇小說集」。而在與會之前,我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大概知道國外文學出版比較重視長篇小說,所以選擇的書籍以長篇小說為多。但有趣的是,每當我介紹完一部作品,譯者們問的第一個問題往往就是:「這本書多長?」連續幾本書之後,德文譯者唐悠翰終於像是忍不住了一樣問我:「為什麼台灣的小說都寫那麼長?」
我乍聽這個問題的時候,差點衝口而出:「欸?有很長嗎?」我所推薦的十本小說裡,除了明毓屏的《高雄故事:再見,東京》有四冊長,還有羅傳樵的《臺北城裡妖魔跋扈》會有續集以外,其他的小說對台灣讀者而言,大部份都是「標準」的長篇小說,厚度大約落在300到400頁之間。
但天野健太郎告訴我,當中文作品翻譯成日文的時候,篇幅很可能會膨脹到原來的一點五倍。他舉例說,中文常常會有一個句子裡面,透過頓號並列很多個名詞,比如說某人吃了五道菜,就寫上五道菜名。中文寫來容易,每道菜名都是三個字,但翻譯成日文之後,吃這五道菜可能就要寫成三行。
而除了譯文膨脹外,唐悠翰也提出了出版上的考量。以在德國,一般讀者比較習慣的小說篇幅來說,中文原作的長度在250頁上下是最剛好的,換算成中文大約是十萬字。厚度增加之後,成本和售價都會提高,也可能會讓讀者望而卻步。(看來不是只有台灣讀者不讀太厚的書⋯⋯)如果小說要超過這個篇幅,那乾脆拉到非常厚的尺度,做出市場區隔。而在這種情況下,台灣最常見的300到400頁篇幅就要長不長、要短不短,反而是最尷尬的。
而為什麼台灣的長篇小說為什麼這麼長?我猜測可能有幾個原因:首先從文學史來看,可能是因為早期本土派作家以「大河小說」為生涯標竿,所以戮力追求那種上下一百年、貫穿家族四代的長篇鉅製,比起嚴格控制篇幅、凝練結構,台灣的小說家更傾向「全力施為」。而在近年來,雖然還抱有這種興趣的小說家並不太多,但政府補助的因素卻也可能讓長篇小說篇幅居高不下。比如以近幾年長篇小說最重要的推手「國藝會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來說,它設定的最低申請門檻是十五萬字。——而這大概就等於我們前面所提到「台灣標準篇幅」。如果政策部門有心推動文學作品外譯,或許應該更細緻地考慮這些細節。而對於作家來說,書寫時的篇幅應該依照自己心中的創作藍圖,無需遷就翻譯的標準,但我想一個值得從中自問的問題是:我們真的有必要每次都寫到那麼長嗎?顯然並不是每一部作品都有很好的理由。
問題二:你要把讀者帶到哪裡去?
另外一個譯者們提出來的問題是,他們不知道為什麼,台灣的小說常常有一種「不知道要把讀者帶到哪裡去?」的感覺。唐悠翰指出,德國讀者閱讀一本書、一篇小說的時候,會希望看到作家明確地展示某個目標,所有的文字都一點一點在朝那個目標前進,不管是故事還是理念,都會有一個方向感。但在台灣和中國的小說裡,作家似乎不願意讓讀者知道手上這本書正在往哪裡走,會寫得比較晦澀。連帶的,許多書裡面的段落,就看不出來到底有什麼存在的必要。而這不只是整本書佈局層次的問題,法文譯者高滿德也提到,即使是在「單一句子」的層次上,台灣小說中也常會有不知道確切的意思是什麼的句子。即使詢問了作家本人,作家也可能回答「這是某種詩意的表現」,仍沒有給出明確的指向,讓譯者只能依照語法或句型來硬翻。
雖然我相信這些案例,可能有一些是基於文化差異、或不同語言運作邏輯不同,而有某些「不可譯」的壁障,不應該強求台灣的小說家修改成外國譯者能夠理解的樣式。但以我自己對台灣小說的觀察來說,我認為這些譯者所提出來的問題,其實正好暴露了台灣小說家基本功的薄弱。譯者們抱持的態度是謹慎、寬容的,他們認為自己沒能完全理解「作家要把我們帶去哪裡」,當中必有什麼小說家的特殊思考在內;但身為一個寫小說的人,我很清楚知道,在很多情況下,實情是「作家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
從故事形式上來說,台灣長久以來不重視敘事結構的基本功,總是以「藝術性」、「避免僵化」為遁詞,長久積弱不振而不願意承認。「文學不應該被紀律束縛。」這類信條,幾乎已成另外一種束縛文學創作的迷信。就算上面那句話是對的,也不應該反過來衍伸成為「沒有紀律就是文學」,因為很可能只是亂寫。而從小說表達的理念來說,戒嚴時期帶來的「逃避思想」傾向、以及瀰漫在台灣各個領域的「抒情傳統」,保護了思路不清的作家,甚至貶抑知性而過度推崇感性,長此以往,當然也就很難在小說裡面看到能成功調和藝術性與思想性的作品。
我觀察到,在會議裡比較容易引起譯者興趣的作品,往往是那種「一句話就能說清楚故事」的作品,比如我介紹何致和的《花街樹屋》時寫道:「這是一本台灣的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一群小孩因為同情心,決心拯救馬戲團裏的紅毛猩猩。但面對複雜的世界和環境,這項拯救任務最終失敗了,而這個失敗的經驗從此改變了他們的人生⋯⋯」第一句話是形式標籤,第二句話是故事梗概。而困難的是,即使我現在知道了這個訣竅,讓我重新介紹一次,有許多台灣的小說仍然無法「一句話說清楚」,因為它本來就不是一個首尾一貫的完整故事。
有趣的是,從我高中寫作以來,我也曾長期浸泡在上述的觀念之中,對其深信不疑。而當時所有這樣教導我們的前輩,所舉的模範都是外國文學作品——但此刻卻是關注台灣文學的國外譯者親口告訴我,台灣這樣的寫作方式讓他們很困惑。但從譯者的這項意見中,我也看到了可以樂觀的理由。整體而言,2000年以後台灣長篇小說的品質是一直在進步的,而且越來越強調完整的故事、明晰的理念、精確的議題,逐步揚棄過去的作法。這個自然演化的方向正與譯者們的期待不謀而合,只是我們才剛剛起步,很多事情還正要學。
問題三:小說家和編輯討論過嗎?
第三個是我已經忘記哪個譯者提出來,但一提出來就引起全場共鳴的問題:台灣的小說家出版作品前,會跟編輯討論嗎?
這個問題其實要反過來看,他們的意思是:許多台灣小說,看起來都沒有經過編輯就出版了。從小說中的科學細節是否真的可能發生,一直到寫作方向、小說整體的結構、目標讀者群、寫作技藝的打磨⋯⋯對譯者們來說,這都是編輯應該要做的工作。但是在翻譯台灣的小說時,譯者時常覺得自己同時把這部分編輯的工作再做一次,與作家討論:這個段落是否必要?那樣的表達能否讓讀者理解?是否該增刪或重寫某些章節?
我完全可以想像,當這種狀況一直發生的時候,翻譯台灣的小說,就會比翻譯其他國家的作品有更多的風險與門檻。(套句商管雜誌最愛說的,這就是競爭力比較弱啦。)而說來慚愧,他們確實一眼看出了台灣文學出版的一個重要弱點。但從小說寫作者的觀點來看,我必須說,台灣文學出版的這種情況,其實不能通通怪編輯不盡責,反而是我們這些寫作的人自己要檢討。或許是華人社會對作家這類「知識份子」過於崇高的尊敬,也或許是前述「文學不應被紀律束縛」的迷信,總之在台灣作家當中,能接受編輯直接告訴他「某某段落寫得不好,希望你修改」的人,我想寥寥可數。台灣的作家普遍姿態頗高,認為自己應該牢牢控制作品的所有細節,但忽略了「寫作」和「出版」其實是兩個領域的專業。
長久下來,編輯們自然也就養成習慣,「放作家自由。」於是,業界裡具有評估作品、協助作家修改的能力與經驗的編輯,自然會越來越少。這樣長期互動的結果是雙輸的,作家即使在出版產業裡最親密的專業夥伴身上也聽不到真話,無從知道自己每一本書到底是進步還是退步。我們一直都知道這種情況,使得一塌糊塗的書照樣可以出版,知道這種循環最後傷害的還是作家自己的信譽、讀者們對台灣文學出版的信心。現在還可以加上一條了——傷害到作品外譯的機會。
問題四:為什麼你們的小說角色不吃東西也不做愛?
最後是一個很小很小,但卻讓我心中瞿然一驚的問題。
在會議上,我介紹了黃崇凱的《黃色小說》,並且說明這是台灣小說中,很少見地討論「異性戀男性的情慾」的小說。因為在過往的小說中,女性小說書寫女性情慾、同志小說書寫同志的慾望,都是很常見的主題,但是卻很少異性戀男性作家反思自己的「性」,黃崇凱這本小說因此顯得很突出。在會後,天野健太郎說他贊同我對台灣小說中「很少討論異性戀男性的情慾」的說法,並且更加證明了他長久以來的疑惑:「我以前就覺得奇怪⋯⋯不知道為什麼?台灣小說如果不是以『性愛』為主題,就幾乎不寫性愛場景;飲食也是,只要不是以飲食為主題,小說家也不喜歡寫角色們吃了什麼。要寫就一點是主題,不然就完全不碰,為什麼呢?這些東西也都有它們的美感和功能啊!」
此話一出,在場的譯者們紛紛點頭稱是。(而我差點忍不住想說一聲:「幹,真的耶,你突破盲腸了!」的衝動......)
說真的,這個問題本身其實並不一定有多重要,也不會造成譯者和讀者的困擾。(「不寫」什麼通常不會成為評價作品的標準,人們比較在意的是「寫」什麼)但在思索幾天之後,我認為這兩個問題牽連的可能是更大的隱憂:一是我們的作家其實還是有很強烈的性別角色分工,二是我們的小說非常非常不習慣提供具體細節。
前者至今仍可見於創作與評論的套路上,無論女性作家寫的是什麼,一定會被認為表達了某種「女性意識」,而把「女性」代換成「同志」也會有一樣的結果;但如果是(異性戀)男性作家就不會有什麼人談論「男性意識」。某些主題,也彷彿就是特定的性別位置才能去寫,比如上文提到的情慾主題。——異性戀男性作家當然也偶爾會寫寫性,但沒有義務反思自己的性;那是女性作家和同志作家的「守備範圍」。這是畫地自限也是刻板印象。
後者則有比較久遠的歷史脈絡。1960年代的現代主義為台灣的純文學小說立下了諸多標竿,卻也留下了諸多不能算是太好的習慣,比如刻意地模糊人、事、時、地、物,形成「兩個面目模糊的人在一個空曠的地方對話」這樣的形式。連人名和環境都模糊了,更不可能花力氣去描寫明確的吃穿日用。這種寫法在戒嚴時期或許還有其必要性,畢竟「話不能說太明」是那個年代的必備技能,但解嚴已經這麼多年了,為什麼我們還不敢把小說寫清楚?我們在怕什麼、躲什麼?
他人的眼睛
當然,不是所有小說家都必須追求外譯,作家優先考慮本國的讀者是很正常的事。但同為小說創作者,我心知肚明,透過國外譯者們的眼睛折射出來的許多疑惑,並不是「文化差異」四個字可以帶過的。想用這四個字回應上述問題,其實就等於輕率地說「反正你們外國人不懂啦」,而不願意承認有很多問題是源於貨真價實的「缺點」。在場的譯者都是對台灣文學很有愛的外國讀者,即使許多作品的「規格」在翻譯上可能很有困難,他們還是想方設法要把這些作品帶回去自己的國家。無論是公開還是私下的交談,他們都不掩飾對台灣文學作品的熱愛,哪部作品讓他哭了好幾次,又有哪部作品讓他覺得是難以比擬的天才;也因此,我對他們願意誠實提出閱讀中的疑惑這一點,感到萬分的珍貴。特別是這幾雙眼睛真的利得很,每一個問號都能刺中一個我們真的必須面對的問題。台灣的小說寫作者無需妄自菲薄,但需要我們認真以赴的事情也並不在少數啊。
(刊載於「鳴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