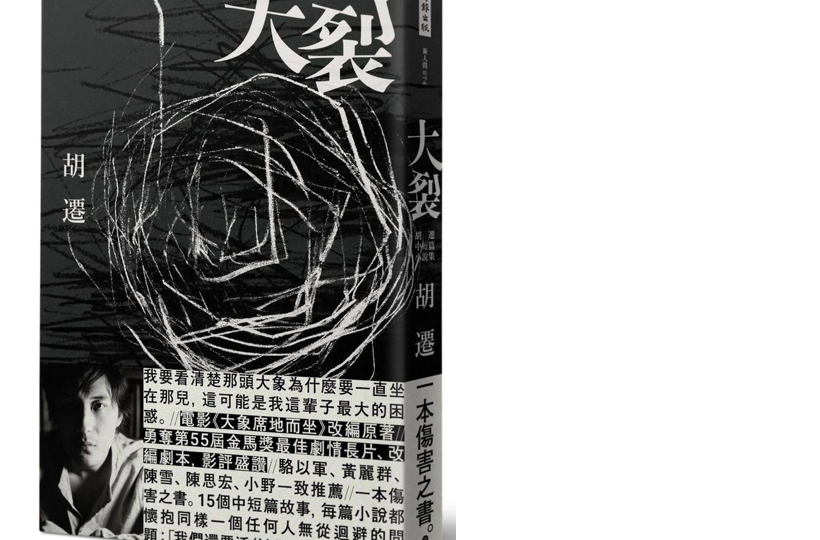白蟻的通道並非像懸了一個鉛墜子那般筆直朝下,而是有許多不必要的彎曲。⋯⋯『再下去一定會有水源了。⋯⋯就為了水。白蟻對失去水的耐受度很低,牠們一定要水,所以無論死掉多少白蟻、花費多少時間,牠們一定會不計代價地朝下挖,那是命定,那是本能。』⋯⋯那從地面朝下的取水主幹,以及許多挖到一半廢棄的、凌亂卻又有著目標的洞穴,是多麽像一個朝向地心的燭台。
(頁364-365)
這是小說結尾安置的象徵性意象之一,雖然沒有「被抬升到樹頂的單車」那麼有力量,但我認為它是最適合用以理解這篇小說的關鍵意象——這幾乎是後設地描寫出了《單車失竊記》的結構和思路。從創作的角度來看,這部小說最困難的部分,就是將各種龐雜的資料收集到位,經過消化後,重新組織為一個故事形式的有機體。關於「如何在文學作品當中處理知識」,在當代台灣的作家當中,吳明益絕對是難有人出其右者。早在《虎爺》的時代,小說家吳明益已經在小說中展現這方面的興趣,但他的「知性」仍主要是表現在散文當中。然而到了《複眼人》之後的小說家吳明益,就正式與散文家吳明益合流,形成一種沛然難禦的淵博風格。再加上吳明益獨特的關懷——大致環繞著「自然」與「懷舊」這兩個關鍵字——,形成了台灣小說家少能觸及的境地。經過了無論在情感、詩意還是知識都極為厚實的《複眼人》,以及結構精巧、揮灑如意的《天橋上的魔術師》後,我們迎來了這本眾所期待的《單車失竊記》。
而《單車失竊記》如何處理知識和敘事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得不說,它採取的是一種略微取巧的方式。小說以《睡眠的航線》那台失蹤的單車為引,形成了經典的「追尋」結構:敘事者追著一個目標,在追尋過程中遇到了許多線索和人物,然後一一帶出各自的故事。這種結構的方便之處在於,情節之間的關係不必非常緊密,什麼時候遭遇什麼人,完全可以由作者來安排。而吳明益的用心之處,在於這趟「尋找單車之旅」中,敘事者所遭遇的重要角色幾乎都織進了緬北森林的那場戰爭中。由於尋找單車,所以引出銀輪部隊;由於銀輪部隊,引出了參戰過的外省老兵和被徵召的原住民軍伕。讀者閱讀過程中會發現原本互不相干的故事線,漸漸以一種巧妙的方式聯繫起來。
這張故事網本身很完美,但比較大的問題是:敘事者跟這張網的連結是很薄弱的。「我」的目標是找到腳踏車,以及和腳踏車一起失蹤的父親(的意義),但相較於巴蘇亞、穆班長等人的錯綜交織,敘事者的父親和這些角色的關係其實並不大。因此,敘事者在這篇小說中,幾乎成了一種功能性的存在(用線上遊戲的術語就是:他是一名NPC),中前段有許多章節,他就是負責出場,告訴讀者他發現了甚麼新線索後(比如巴蘇亞的錄音帶,或者薩賓娜的小說片段),把敘事的主控權交給那段材料。分段來看,這些篇章無疑都是精彩的,但是對於敘事者發生的意義卻不清晰,在大部份時候,也看不出因為這些材料而讓敘事者有什麼情感上的、人格特質上的轉化,甚至也不見得都對尋找父親的腳踏車有幫助。如果是這樣,敘事者出現在這裡的意義是什麼呢?
這就形成了一個有點弔詭的,「朝小野大」的情形。每一段支線劇情都很亮眼,但主線劇情要到後三分之一才開始陸續經營,使得整本書的重心好像都在「別人」身上。而因為這樣,前三分之二的閱讀過程裡,敘事的推進動力是比較弱的,因為不是所有章節都是尋找腳踏車的「必經之路」。敘事者可以興味盎然地岔出去聽 / 說故事,但讀者卻缺乏一個「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如果單純將敘事者自己的行動抽出來,會發現整部小說實際推進的情節並不多,大多數時候,敘事者都是旁觀者,也因而讓人比較難感受到敘事者自己的情感轉折。
我們可以比較吳明益至今最受讚譽的長篇小說《複眼人》的敘事結構,就會發現差別。在《複眼人》當中,那個串起一切的敘事者並不存在,小說是讓每個角色輪流主持章節,各自行動來面對自己的困境,也就不需要像《單車失竊記》一樣,經過各種轉述(信件、錄音帶⋯⋯)來引出角色。只要情節之間的關係夠緊密,小說並不必然需要一個統率全局的單一敘事者。而「轉述」(如《單車失竊記》)和「演出」(如《複眼人》)的差別,或許就是前者為什麼讀起來較為散文化,時時恍有正在閱讀吳明益的臉書貼文;而後者雖然置入了更龐大的真假知識體系,卻能更有詩意、更有情感的渲染力的原因。
而在結尾之處,這位單一敘事者也帶來了一些麻煩。敘事既然是從他開始,也就必須從他結束,因而結尾那段並不能加分的「在病榻邊騎腳踏車」雖然顯得有些刻意,卻又免除不了。究其原因,恐怕還是小說中前段以前,並沒有足夠的戲份能建立起敘事者和父母之間的深刻關係(主要的篇幅給了故事更精彩的周邊角色),那段現代主義式的昇華,也就找不到支持的基礎。即使我們把《睡眠的航線》列入考慮,當作這部小說的前傳,也難以撐起這麼強的象徵,因為它的重心也不在敘事者和父母之間的相處。
相較之下,巴蘇亞發現的那台「被抬升到樹頂的單車」就是一個更漂亮的意象,可惜被這個敘事結構擠到了比較次要的位置。這也連結到另外一個略微可惜的部分。我認為,《單車失竊記》在思想上最大的成就,在於它透過「單車」這個意象,輕巧地連結了台灣所有族群的戰爭經驗、以及相關的歷史傷痕,包括外省人(如穆班長、老鄒)、本省人(敘事者的父親)、原住民(巴蘇亞),並且用一系列「轉贈單車」的曲折故事,舉重若輕地訴求了某種歷史的和解。敘事者的上一代們,分別因為戰爭困在歷史性的傷害裡,然而在單車的流轉中,他們治癒了彼此,或至少傳遞了希望能治癒對方的心意。對照現實的台灣,在統派紀念「八年抗戰」、獨派回首「大港起風湧」的「皇軍」歷史,各自以不同的戰爭記憶武裝自我認同、區分敵我時,吳明益找到了緬北森林這場戰爭,形成一個縫合歷史裂痕的漂亮接點,寫出了和解的可能性。這樣的視野和胸懷,在台灣文學史上是罕見的,即連李喬的《寒夜三部曲》和陳千武的《活著回來——日治時期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都未必能及,更別說吳明益的故事遠比他們更加精巧。如果說這部小說要重理敘事結構,這條線索應該會是最適合的,效果也會比現在的版本更佳吧。
將以上對這部小說敘事結構的討論,和開頭引用的白蟻穴並讀,我們就能看到一組微妙對應的圖像,幾乎就像這篇小說的自我寓言:白蟻(敘事者)往下挖掘水源,但並非鉛直地抵達目的地,而是形成了許多挖到一半就放棄的凹穴(支線情節)。那些凹穴的形狀都是美妙的,但那底下的水源到底是什麼呢?會是那些不斷在吳明益小說中重複出現的意象嗎?——中華商場的陽春麵(加烏梅酒)、廁所的夢魘、西裝店與皮鞋店、彈吉他然後殺死女友的阿猴、各式各樣的動物敘述⋯⋯在這些反覆出現的東西裡,是不是還有小說家覺得一直還沒寫到盡頭的神祕性在內?小說家再三致意的豐沛知識和「細節的聖殿」,也許是掘抵那「水源」的途徑之一,是反覆鑽探、嘗試而形成的凹穴,但並非真正的水源所在。《單車失竊記》找到了「那個濕潤的養菌圃」(頁365)了嗎?我想這是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
或許,某些讀者更期待的是像《複眼人》的結局那樣。小說家對這個世界的憤怒已瀕臨失控邊緣,遂不顧一切,翻覆天地,一舉炸沉整座島嶼、一整群的鯨魚擱淺、死亡、爆破⋯⋯那樣的失控,那樣的情感強度,是只有在吳式的扎實知識風格裡才能成就的。單憑抒情不能,單憑知性和考掘細節也未必能到達之處,必須有些什麼溢出了控制之外,衝入了小說一往無悔之境,捲動了讀者。乃至於,捲動了整個世界。
(刊載於「想想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