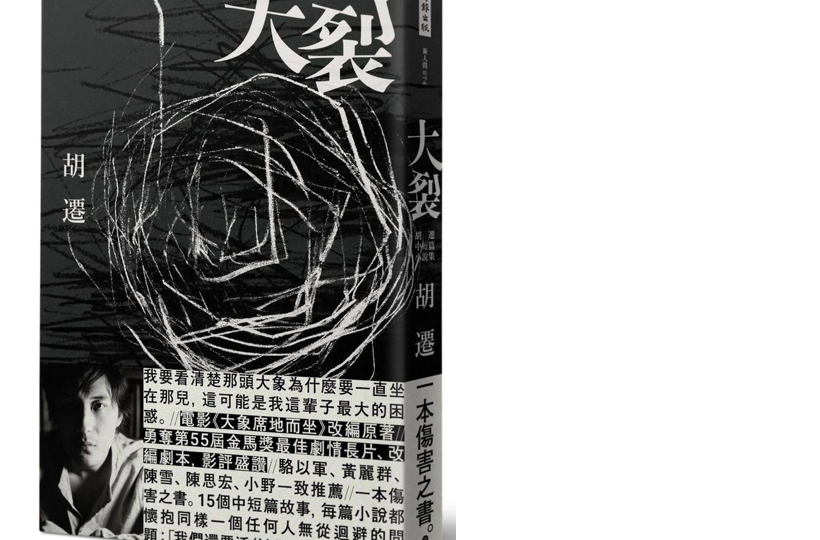略微歪斜,風格未滿:讀阮慶岳《神秘女子》
2018/03/01 _文學評論
阮慶岳的長篇小說新作《神秘女子》,是以一個俄羅斯娃娃式的三層結構組織起來的。結構的最外層,是一名收到兩本筆記本的女性敘事者,她認為這是離家多年、與她有著神秘連結的姑母寄回來的。次一層是兩本筆記本之一,寫著「日記」的那本,是一名男性小說家的日記。最內層則是寫著「小說」的筆記本,是另一位女性敘事者的獨白式小說。這三層敘事有些明顯的呼應,比如同樣都有不知身在何處的神秘女子、原因晦澀的單相思。
在情節的設定上,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褚威格的名篇〈一封陌生女子的來信〉。然而,相對於〈一封陌生女子的來信〉十分戲劇化的絕望與激情,《神秘女子》雖則篇幅更長、並且將類似結構運行了三次,但情節卻更簡單、調性也比較疏冷。
整本書最戲劇化的部分,當屬第二層次的小說家日記。在日記裡,除了記述了他寫作過程裡不斷收到的神秘女子來信,也塑造了另一名與小說家定期幽會的神秘女子。二女是否為同一人?如果是(或不是),她們又是為何要這樣接近小說家?這樣的懸疑性貫穿了整個章節,不但強化了閱讀的推進力,且直到最後一封信為止,力道都拿捏得宜,始終維持一種恍惚的曖昧狀態而不說破,從而撐出了豐盈的想像空間。也在這樣的背景下,「小說家」的煩憂與思索,以及他那並未在「日記」章節具體出現的寫作中的小說,才交織成為具有強大神秘氛圍的多重空間。
然而,比較可惜的是,雖然小說有三層結構,但並未發揮三層互相加乘的效果。如上段所言,我認為《神秘女子》最豐盈的部分,就是在「日記」一章了。最外層的「姑母-姪女線」內容較為單薄,雖然呈現了某些宗教性的線索,然而作用並不明確,更像是一層可有可無的外包裝。最內層的「小說」雖然透過敘事者竭力論述她的愛情觀點,然而並未有何出奇之處,深度並不超過一般文青的想像範圍。而以「論述」的筆法進行,更使平淡的論述失去了本來可以有的小說形式掩護。這兩層的少數亮點,或許都能收攏合併入第二層,成為更精練緊湊的中篇小說或短篇小說。
另外,《神秘女子》另一個令我困惑之處,在於它的文字。用非常一般性的觀點來讀,最直接的印象就是,這本書裡有大量的冗蕪字句。比如:「雖然各種疑慮依舊滿布雲集,我決定先接受這樣一切突如其來的發生事實,因為對於所有猶然等待被釐清的未明訊息,斷然就採取否定的態度,完全不是我一貫的人生態度。 」(p.10)不必是文字特別精簡的人,大約都能找到不少可刪減之處,比如「滿佈」與「雲集」僅需存一,「這樣」與「一切」能夠刪掉一個或者合併,「發生」與「事實」兩者都可以當作名詞用,也僅需存一。或者像這樣的句子:「這是到現在還很令我驚訝的事情,因為這個陌生的女人,絕對不可能會是我前妻在此地的突然再次出現,而且隨後再細想下去,也見不到兩人 容貌的任何真正相似處。 」(p.66)短句「絕對不可能會是我前妻在此地的突然再次出現」已經不只是冗蕪而已了,整句的文法完全不通。一般的句子,大約到「前妻」就可以終止了,後面的補充可以往前拉成修飾詞,也可以拆解成其他短句處理。
當然,文學作品未必要追求常人的「文從字順」。為了配合特殊的內容、節奏感或聲音需求,或者僅僅只是為了一種風格化的嘗試,都可能對文字進行破壞性的創造。在台灣文學史上,就至少有王文興、七等生這類著名的「破中文」(黃錦樹語)案例。《神秘女子》的文字問題,能不能用這樣解釋?我認為是很勉強的。如果是為了配合特殊的內容而進行形式變造的話,我們首先得區分出「這些特別的句子出現的段落,是否有值得深思的內容」,然而綜觀本書,這樣的句子散置在各處,並無具體脈絡可循。其次,如果說這是一種風格化的嘗試,則會令人疑惑:這樣的「風格化」,會不會太便宜了一點?比起王文興的詰屈用字、七等生的崎嶇文法,《神秘女子》的文字風格,歸納起來也不過就是「反覆堆疊意思相近的二字詞語」而已。無論就變造的方向還是力度來看,我們都很難明確的指出這樣的「風格」跟純粹的「冗贅」有何區別,遑論更深層的意義。
也因此,我完全無法理解附錄中宋澤萊關於此書文字的判斷。他說:「在文字藝術上,阮慶岳這篇小說真是不同凡響,叫人驚豔。他的散文文字非常細膩,不斷反覆的獨白有如山林中的溪水,潺潺不息,每個句子都彷彿一句詩,節奏性、音樂性十足。」(p.282)在我看來,這段判斷非常離譜。《神秘女子》的文字縱然不是問題最大的,但大概也稱不上細膩。更別說在後段還以此書為基礎批評「台灣的文學作品在網路時代裡已經受到隨便書寫的污染,文字技巧越來越薄弱」(p.283),這樣的美學標準,已經嚴重地與現世脫節了。
若要成其風格,或許我們該期待小說家更大膽一點,要歪斜就歪斜到底吧。僅僅像現在這樣略微地歪斜,是很難形成真正顯著的風格的。好小說的途徑本就不只一種,只要有足夠強的震撼或新意,讀者是能夠接受以醜為美、以粗糲取代工整的現代主義邏輯的。如果風格真能成形,前述的結構問題或許也就不成問題了;但在目前的狀況下,形式與內容兩端,顯然都還談不上誰掩護誰、何處亮點能夠逆轉何處缺點的問題吧。
(刊載於《聯合文學》2018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