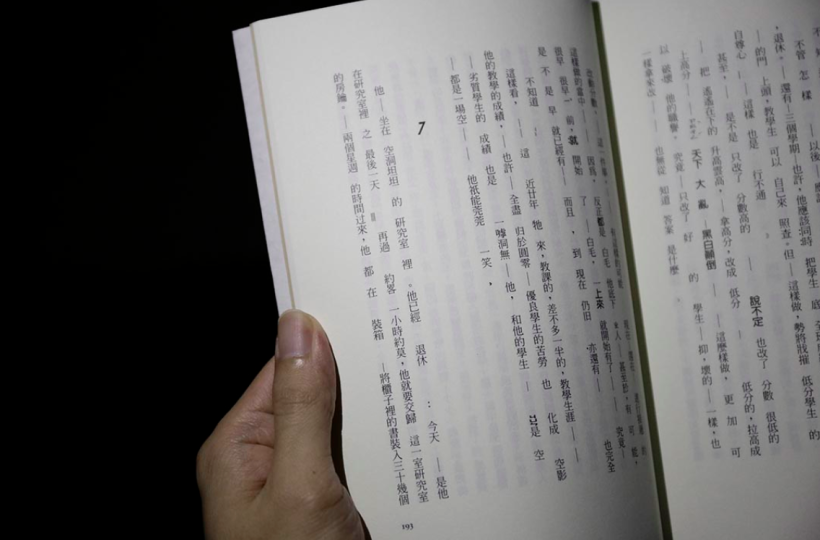反烏托邦小說一直是科幻小說的重要子類型。2015年,野人文化便出了一套「反烏托邦三部經典套書」,集合了薩米爾欽《我們》、赫胥黎《美麗新世界》、歐威爾《一九八四》三部重要作品。雖然側重點各有不同,但反烏托邦想像的大致是一種「科學專政」的未來——小說以某種科學技術與思想為核心,建構出一個完美運行的世界;然而「完美」本身就是反人性的,故此「烏托邦」註定將發展成戕害人類的恐怖專政。
以此脈絡來看,中國小說家王力雄的《大典》毫無疑問,正可放入此一譜系。從開篇第一章的「鞋聯網」構想出發,就能讓我們看到近未來完全可行的政治監控科技:透過秘密植入每一雙鞋子追蹤零件,國家可採集到每個人的身體資訊、移動軌跡、社交紀錄,從而解消所有叛亂的可能,真正成為深入每一秒鐘「生命治理」。其驚悚之處不在「科幻」,而在它幾乎就是「科(技事)實」,因為所採用的技術正是我們此刻琅琅上口的「物聯網」、「演算法」和「大數據」。而後續情節引入的新科技,除了「夢造儀」稍稍比較「不科學」一點,其餘如社會控制的「網格化」和機械科技的「電子蜂」,都並非遙不可及的技術。
然而,《大典》卻又不是傳統的反烏托邦小說,反倒富有強烈的中國特色,拓增了此一類型的視野。在小說開場,我們確實會看到若干反烏托邦小說的經典元素,比如「雙大典」(黨慶與世博會)的設定,令人聯想到《我們》裡的「整體號」,同樣都是極權政府的自我頌揚儀式;「夢造儀」的精神控制技術則致意了《美麗新世界》的意識形態培育科技;而工程師李博對「性」的焦慮、鄉愁與惦念,更是與反烏托邦小說以「原始的」性慾抗擊「文明的」科技之套路符合若節。
不過,當基本設定鋪陳完畢,小說中段開始發展情節時,我們就會發現《大典》的特異之處了。如果說傳統的反烏托小說描述的是「蛋殼再密也有縫」,《大典》的科技世界大概已經碎成一碗蛋花湯了。故事中的每一項技術看起來都鋪天蓋地,一旦在中國社會實作就左支右絀。「鞋聯網」看似無所不在,但小說開場就是李博藏了一雙手編草鞋,從而連動到結局的大逃亡。科技也不是百分之百地掌握在黨、國與資本家手上,中間多有上下其手的空間:老叔掌握了「性鞋距」、李博偷藏了「鞋麥」、鞋聯網裡找不到政要的SID參數......科技打造出了全控社會,但誰來全控這個全控社會?問號的反面就是系統性的漏洞。
不唯統治階層和技術精英能夠找到漏洞,底層人民也有自己的出路。透過一場防疫事件,王力雄建構了「網格化」這種社會技術,但旋即把視角轉向「綠妹哥」,讓我們看到千差萬別的中國農村環境如何讓系統失靈。
最有趣的系統失靈,當然就體現在獨裁統治的權力結構上。小說中後段,王力雄以上述科技為基礎,將故事帶進了他自《黃禍》以來,最得心應手的政治主題。連極權政府引以為豪的科技監控都碎成蛋花湯了,看似森嚴的權力結構自然也不堪一擊。小說中的「主席」為了自己的權位處處鋪路,創建各種能使他繞過憲法的法外機制,但在王力雄精巧的佈局下,所有增強其權力的設計,都成為了促進這個結構毀滅的助力。為了大權一把抓而有了「處突組」,結果當主席「不能視事」的時候,處突組就成了足以操弄軍政兩界的槓桿;為了制衡官僚而建構的「未必是你的錯,但你必須當責」的官場文化,反而促使最保守的官僚引爆了蘇聯垮台式的民主化宣言。
總的來說,《大典》的政治博奕非常精彩,搭配近未來的科幻設定更是威力強大。從一開始,王力雄的問題意識就不是證明烏托邦的強大,而是演示烏托邦的脆弱:越是龐大複雜的結構,越是可能因為一個小零件被敲掉,而導致勢不可止的崩毀。梳理整本書的結構,一切的起因都十分微小:工程師想要有性有愛、警察想要升職、商人想要卡位求官、老官僚想要自保......但微小的動機稍微推了推龐大的國家/科技複合機器,事情就這樣成了(或毀了)。
當然,《大典》並不是沒有缺點。某些設計稍嫌冗餘,比如「雙大典」的黨慶或世博會可以僅留其一,敘事結構會更漂亮些;九組在前段被寫得神通廣大,結局卻雷聲大雨點小。或在政治攻防的段落中,過度詳細地解釋每一個步驟背後的用意,雖然是滿滿的「乾貨」,但也不免失之直白,或可再多信任讀者一點。比如信息中心主任不想交資料給九組的段落,對白中點出「實驗項目」即可讓讀者領會了,無須那麼多解釋。但整體來說都是小疵,從主題、佈局到情節設計,《大典》絕對是今年台灣書市的小說前段班。
最後,我想來談談《大典》的結局。結局不是收在北京政權的政爭勝負,而是把焦點放回李博所在的福建窮鄉,讓各方人馬都爭先恐後湧來,此一設計自然饒富意義。不過我更注意到的,是王力雄用「鐵籠」來形容李博被居留的囚室,就在小說的最後一段:「鐵籠卻如同風暴中心紋絲無擾......」 (p.293)而我們知道,思想史上剛好有另外一個著名的「鐵籠」比喻,來自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這本探討資本主義源起的經典著作結尾,韋伯也用了同樣的比喻,來說明人類社會全面落入資本主義的掌控中,因而有了他寫作風格中,難得出現的激情段落:
這會是巧合嗎?綜觀《大典》的人物與情節,我想不是。社會學家韋伯在寫完這個段落之後,顯然也覺得自己失態了,馬上補了一句:「但是這就把我們引入了價值判斷與信仰判斷的領域,而這篇純粹討論歷史的文章無須承擔這一重任。」然而小說家與學者不同,他接下了價值判斷與信仰判斷的重任:讀畢《大典》的人都知道,關在這鐵籠裡的李博,剛剛才做出了一個悲壯動人的犧牲決定。没有人知道將來會是誰在這鐵籠裡生活;没有人知道在這驚人的大發展的終點會不會有全新的先知出現;没有人知道會不會有一個老觀念和舊理想的偉大再生。如果不會,那麼會不會在某種自發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飾下產生一种機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有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無道理地這樣評說這個文化的最後發展階段:「專家没有靈魂,縱慾者没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着它自己達到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唐山版,p.145)
無論小說裡或論述裡,小說家王力雄總表現得如此冷徹,連他筆下的民主化進程都毫無理想性可言,但在最後我們還是看到他真正相信的東西了——在經歷一切陰謀、鬥爭與殺伐後,最後的鏡頭不是停留在那些達官顯要身上,而是在這微不足道、自始至終都被擺佈的傻子身上。即便在最牢不可破的鐵籠裡,還是有那麼一人如此純真,如此甜美,還是令人願意相信:最終仍有人類能持守對其他人類的善意。
(刊載於《聯合文學》2018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