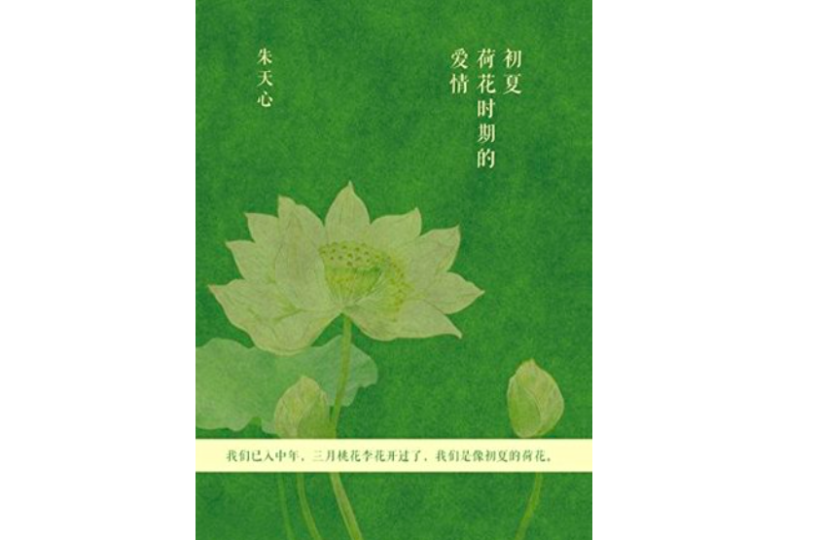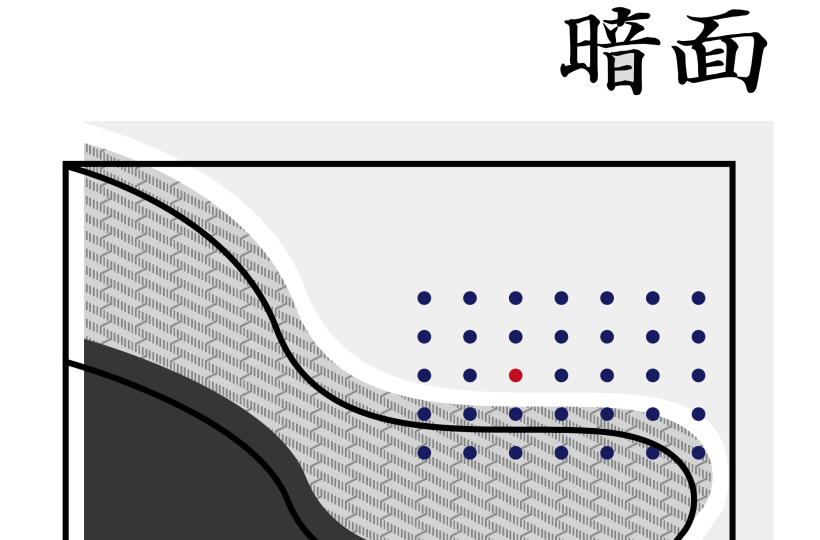2010年出版的朱天心《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是作家目前為止最新的作品。這篇由數個主題與人物大致統一、但篇幅長短不一的章節所組成的小說,大約是一個中篇的規模。朱天心招牌的第二人稱敘事者「你」,以及隨著「你」而來的絮叨長句、彷彿如下午茶碎嘴時光的腔調,都是能讓讀者能輕易辨認的風格標記。整體而言,《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是一篇輕盈、表現平穩的小說,並不算失敗;但比較可惜的是,如同風格上的熟悉,一路追索讀來的讀者,卻很難在這本新作當中讀出太多新意。
《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的主要軸線,是一位中年女子哀悼、追尋她在漫長婚姻當中流失掉的愛情。它的前一百頁採取後設小說般的結構,在多段章節的尾聲之處,作家的聲音突然浮現:「你和我一樣,不喜歡這個發展和結局?那,讓我們回到⋯⋯」下一章節,故事就會回到某一個分岔點,進行同樣主題但不同版本的變奏。而到了末六十頁,這種組織方式消失,改為在每章節最後點出下一章節的關鍵字(「男人與女人」、「別吵我」⋯⋯),轉接到下一個同樣主題、但處理角度不同的段落。這樣的結構使得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很容易感到一種分裂:本書前半段混合了卡爾維諾《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和朱西寗〈冶金者〉的寫法(特別是一再回到過去的某個時間點,歧生新的版本,與〈冶金者〉如出一轍);後半段則是比較單純、鬆散的「相似物轉場」——章節之間並無必然聯繫,於是在關聯不大的章節間安插一個類似的元素,利用人閱讀上的心理慣性來過渡。於是讀者會看到,在這麼短的篇幅當中,這本書就出現了兩種縫合章節的方式,並且所佔的篇幅都不夠大到被視為此篇的主導結構,顯然作家並沒有打算追求一個完整的敘事框架。問題是:為什麼要這樣處理?為什麼不選擇任何一種方式貫徹到底?當然,熟稔於各種「後」學術語的論者大可振振有詞:碎裂、拼貼、非線性本身就有其積極意義,我們對完整結構的追問,毋寧顯得陳腐了。但是,「不完整的結構可能有其意義」,不代表「所有不完整的結構都有意義」。在一定程度上,我們還是得考慮這是否可能出於疏漏,是一種寫作上的缺陷?到底此一敘事結構造成的效果是正面還是負面的,還是得搭配小說的情節來一起評估。
在「後設」的段落裡,小說主要由〈日記〉、〈偷情〉、〈神隱I〉三章組成;〈日記〉的敘事者偷看丈夫少年時狂愛自己的日記,對照此刻的淡漠,想找到「丈夫是何時被偷換的?」;〈偷情〉的敘事者出國赴一舊情人之約,但整場出軌激情實是一段與丈夫約定好的扮裝遊戲;〈神隱I〉則接續〈日記〉的旅行,情節較少起伏,更多是對衰老與時間流逝的自省。平心而論,這三個章節文字仍有風采,情緒的起伏錯落有致,確實是名家手筆。〈日記〉作為開篇,將壓抑欲狂的女子心事表現得十分精彩;但第二篇〈偷情〉的概念直接取自米蘭昆德拉〈搭便車遊戲〉,雖然細節、背景有所差異,但扣除掉借來的概念之後,這一段就要失色不少了。而在兩章的結尾處,〈日記〉與〈偷情〉都安排了殺機,前者敘事者推丈夫落橋、後者丈夫逼近敘事者的背後,雖然不是不能理解其中愛慾與死亡的關係,但這樣的概念連結似乎有點流於想當然耳了(愛慾的極致必然導向死亡,這是經典公式),處理上也稍微生硬了些。
相較之下,後半段的結構較鬆散,篇章數雖多,但越寫越短,到最後幾章甚至有寥寥數行者,使得某些可以深掘之處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有些可惜。在這些「男人與女人」、「女人與男人」的段落裡,作者引入了石器時代男女的想像,並將之一一對照於此時的夫妻生活。其他章節則更深入到日常生活,書寫夫妻生活之中與子女的關係,並且屢屢對照青春正盛的子女與肉身老去的自己,形成一系列「年輕vs年老」的二元對立概念,與上述「男女文明史」交錯進行,雖然構思簡單,但很有一種辯證轉喻的趣味。不過,在極少數以丈夫觀點敘述的章節〈男人與女人II〉,主要概念卻曾經在朱天心過去的名篇〈鶴妻〉當中出現過。閱讀至此,讀者恐怕無法不升起一種「偷工減料」的直覺:在這篇幅不過四、五萬字的小說當中,竟然就有這麼多與前作雷同之處!從〈冶金者〉借來的結構,從〈搭便車遊戲〉借來的「扮演偷情」,從〈鶴妻〉借來的「男人對家居的陌生」⋯⋯轉借概念予以重寫並不是不可以,但問題在於,這些轉借都沒有翻出原作的範圍之外,便頗有原地踏步的「重抄」(而非「重寫」)之議了。
由此而言,《初夏荷花的愛情》並不是一篇寫得不好的小說,而是一篇讓人惋惜「竟然沒能寫得更好」的小說。站在前作的基礎上,我們所寄望於小說家的,應是翻出更新一層的境界。如果以目前所表現出來的密度、深度來說,這篇已經不長的小說,或許還是讓人感到有點虛胖的。它的基本主題、情感和辯證,幾乎在〈日記〉一章當中就開展完畢,只要能夠找到從〈日記〉接續到〈彼岸世界〉之(仍有不甘的)優美頓悟的方法,這本書基本上可以只寫這一篇就好了。它凝煉、緊湊得多,其他的篇章也不能再有多少增益。而回到我們前面關於結構不完整的質疑,可以進一步反思的是:會不會這篇小說真正精彩之處,就在這個(前後分裂的)結構設計裡面?我個人覺得這是很難說得通的。姑且不去爭論這樣的敘事結構到底能不能算得上「設計」,我們並沒有辦法從這麼統一的主題裡面看到「分裂」的必要。而從小說的情節內容來看,我們也無法找到前一百頁非這樣不可、而後六十頁非那樣不可的理由。如果作者的企圖是用一系列的短篇小說穿刺同一個主題,那比較適用的或許是後六十頁的做法,各個短篇兵分多路,將思考的面向推展得更廣闊,只留下若干線索暗示彼此之間的聯繫。如果作者的企圖是將之視為一篇完整的作品,採用前一百頁不斷回溯的手法可能是更有可讀性的;至少這樣能夠表達一種強烈的執著,一種不斷原地踏步、回望過去、試著拒止時間卻又徒勞的努力。——但無論是哪一種寫法,作家都需要再找到更多至少足以撐起一篇短篇小說的「哏」,目前可見的「素材」是有些不夠的。王德威的序文指出:「〈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是朱天心進行中的小說創作一部分。」或許正是含蓄地點出了這本書帶給讀者的一種「未完成」之感。
原地踏步。拒止時間。無論就好的方面或不好的方面來說,或許都是理解《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的兩個關鍵詞。一方面,如上所述,小說其實在第一個完整章節就寫完了,後面已是原地踏步(更徹底的說法是:這個主題,其實在這篇小說寫出來之前,作家已經寫得很好了⋯⋯);但同時,原地踏步也是朱天心小說向來最動人的姿態,她總是拒絕與時俱進,到了一種總是用異樣眼光來看到新事物、新世代的地步。《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甚至將這樣的幻想加諸在「年輕人」身上:「要是能移除掉這一半人,便可以回到以你們為座標中心的那個時空⋯⋯」這樣的決絕幾乎是法西斯了,卻自有其迷人的堅定。論者往往以此,稱朱天心為「老靈魂」。但有趣的是,朱天心的小說腔調、視角和思考方式,反而與此字面上的「老」相反——她或許是台灣文學史上最正宗、真正永遠也不會老的「少女」系作家吧。在某些精神層面和情感態度上,《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距離《擊壤歌》並沒有太遠,除了當年「去情慾」的寫法轉為濃烈的愛慾這個轉變外,小說彌漫著的對愛情之忠貞、之狂熱的索求,其實仍是非常年輕的,林俊穎在書末引用「少年法西斯」的概念來談論朱天心是精準的。這篇小說表面上是一個初老、已老、與老抵抗的故事,但小說不時閃現的一種「發現新世界」的語調,卻泄露了這小說家其實還沒有老到世事洞明,她的太陽底下還有新鮮事;即使這新鮮事是老之將至的心態變化:「這才知道,戴耳環,以免他人目光滯留在不遠處魚尾紋的眼睛⋯⋯你發現,原來珠光寶氣不為吸引人,而是躲避人。」如此種種,或者能夠讓讀者放心一點,無論小說家如何寒著臉,「大慟」,如何給出一個仿佛成道出世、羽化飛仙的結尾,她仍然是我們認識的那個具有銳利好奇心,對人世(即使總是過去的)眷戀駐留、眼熱心細的小說家。小說表達的「拒止時間」主題或許不夠成功,但小說家的生命樣態卻成功地拒止了時間的侵襲。如此,讀者就還能期待讀到真正的新作——那顆心是還沒有真正僵硬掉的吧?
(刊載於《秘密讀者》2013年12月號)
站在原地,再一次拒止時間:朱天心《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
2013/12/20 _文學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