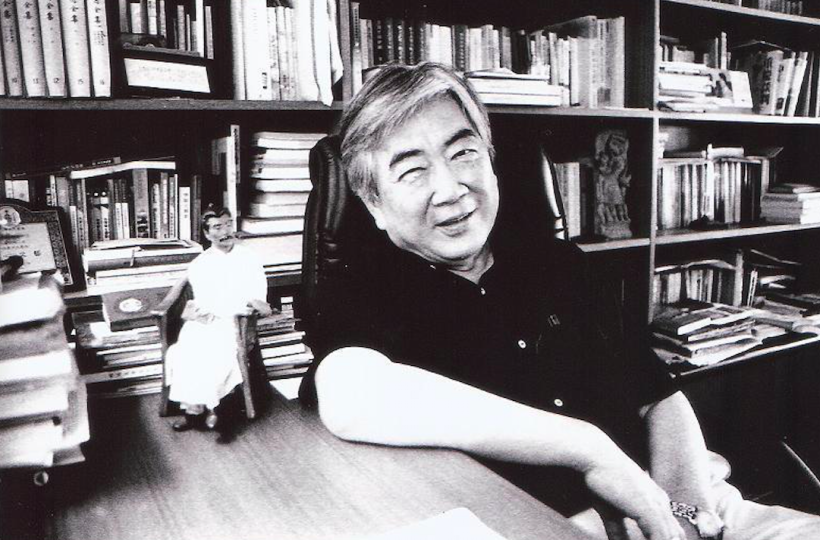整體而言,我同意他貼讀文本,試著從中勾連到作家整體思想,以及更大的歷史問題的處理方式,這樣的細膩閱讀是我們的文學評論,特別是學院當中的文學評論裡十分缺乏的。但同時,在趙剛的陳映真論述中,卻有若干嚴重的過度詮釋之處。以他的論述作為案例,我們可以看見幾個值得反思的問題:當我們試著從文本細節中詮釋出更深層意義的時候,我們推論的界限在哪裡?走到什麼地步,我們會開始認為「這是過度詮釋」了?什麼樣的詮釋我們可以確定是論證充分的?分辨「作者的意圖」和「角色的意圖」在分析上有什麼重要性?文本分析的任務是指出作家的思想,還是指出作品所表達的思想?——兩者之間若是出現落差,我們應當如何取捨?本文將與《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中提出的幾個詮釋進行對話,集中商榷「細節」和「角色」兩種解讀層次上的「極限」;這些討論或許在更大的思想脈絡來看只是枝微末節,但積沙才能成塔,再宏大的文學知識也是無數微細的詮釋交織起來。
1.「細節」詮釋的界限
文學,或至少在小說裡,是透過文本透露的有限資訊來與讀者互動,進而產生各種知覺之後的心理效果的。任何文本都是由有限的符號,透過特定的組織方式組成的。在上述的概括之下,我們或許可以這樣想像一個已經寫完、公諸於世的文學文本:它是由幾條被作者選定的絲線,用作者選定的編織法縫製而成的一塊彩布。既然符號組合是有限的,它所能提供的資訊必然也是有限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從一個文本裡面獲得大致上相同的閱讀經驗,能找到所謂的「主題」和「意義」。但弔詭的是,由於每一個符號並不是只對應一種意義,也不是只能提供一項資訊,其中有讀者可以各自解讀的歧義(當然,這個歧義也是有限的,比如我們不太可能把「牛」這個字讀成一種身體感覺;但至少不是一對一的簡單對應),所以我們也無法找出一個全然確定的「主題」和「意義」。這中間的落差,有時是本質上的差異(我認為這篇小說表達的是A,不是B⋯⋯),有時是程度上的差異(我認為沒有這麼A,只是a而已⋯⋯)。
綜上所述,除非我們決定採取一種虛無的立場,認為無論怎麼延伸文本的意義都不過分,否則我們就需要劃定界限,來認定什麼程度的詮釋差異是可以接受的,什麼是太超過的,以求框定一個可以作為普遍認識基礎的文學知識的範圍。在這個問題上,趙剛的陳映真論述是很好的討論材料。趙剛在自序當中,提到自己的「知人論世」的方法,從文本推及作者、推及世界;同時他也強調細節的讀解:「又一次次的翻來覆去地重讀,因為一個原先所沒注意到的重要細節會像個潛艇一樣突然浮現,而這個浮現又會震動,甚至打亂原先你『已知道』的小說秩序⋯⋯」(頁24)在這裡,我是完全同意他的想法的,但睽諸他的評論實踐,我們卻幾乎有著完全不同的閱讀結論——且不在我認為合理的差異範圍內,是一非此即彼,必有一方為誤的巨大的落差。
比如,對陳映真〈祖父與傘〉的詮釋。〈祖父與傘〉是敘事者「我」被情人的傘觸動了心思,想起了童年時同居山村的祖父在雨夜病歿,而敘事者抱著祖父不離身的傘出門求救不及,象徵性地毀了傘的故事。故事本身篇幅很短,梗概單純,有著陳映真一貫的憂愁氣質,但其實很難挖掘出太深的意涵。但是,趙剛在〈頡頏於星空與大地之間 : 左翼青年陳映真對理想主義與性/兩性問題的反思〉一文當中,認定老祖父是一個「老礦工,但也是日據時期反帝、反殖民、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老黨人。」(頁77)這是一個大膽的推論,如果能夠成功證明,確實就能夠將這篇小說提升到一個日治時代以降的左翼歷史的高度,從而使得整篇小說的一言一動都具有更大的象徵意義。然而,可惜的是,趙剛提出來的證明是非常薄弱的。他認為,證明祖父是一名老左翼的證據就是那把傘。首先,由於那支傘在小說被非常突出地描寫其高貴的外形,所以:「在環堵蕭然之中,這支離奇的長傘不得不脫略其物質性,而象徵了一種精神⋯⋯」(頁77-78)接下來,論文引用了一段陳映真的小說文本再進行討論,為了指出這中間的推論出了什麼問題,我將照抄陳映真的文本和趙剛的論述各一段,作為表格對應如下:
| 陳映真〈祖父與傘〉引文 | 趙剛的詮釋 |
|---|---|
| 它的模樣比現今一切的傘大些,而且裝潢以森黃發亮的絲綢。它的把柄像一隻雙嘴的鍬子,漆著鮮紅的顏色,因著歲月和人手的把持,它是光亮得像一顆紅色的瑪瑙了。[⋯⋯]它有著一種尊貴魅人的亮光。晚飯的時候,傘就掛在左首的牆上,在一顆豆似的油燈光之中,它像一個神秘的巨靈,君臨著這家窮苦命乖的祖孫兩代了。 | 如果說,這把傘象徵的是全世界或至少是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算是穿鑿附會嗎?應該不是。無論是蘇聯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都是紅黃二色,鮮紅象徵革命的熱情,而黃代表革命開展的發亮的光芒。更何況,傘還掛在『左首的牆上』,占據一種精神的、信仰的中心位置。如果說,祖父象徵著在這個冷戰時代中已經消失或隱匿的台灣的左翼黨人,那麼這把經過『歲月和人手的把持』的傘,就象徵了左翼革命信念的雖敗不死,且仍將一代一代傳下去。 |
在這裡,支持祖父是左翼黨人的理由只有兩個:一是顏色(紅、黃兩色),一是位置(左首的牆上),就算我們認同傘應該是某種象徵,也很難在這麼薄弱的理由下相信它是象徵這樣的東西。這個詮釋並非絕對不可能,只是證據不足,難以服人。象徵的原理是以此指彼,在同一文本內,它的詮釋邏輯必須一致,而且通常要出現不只一次(因為只出現一次,是為孤證,甚至無法形成詮釋邏輯)。紅、黃二色(的傘)在這個文本裡面,就是這樣的孤證,我們找不到作者在其他地方繼續暗示這兩個顏色有什麼意義,因此這最多只是一個可能的揣測。更何況,我們如果順著這個邏輯往下走,大可以追問:如果紅色是社會主義最主要的代表色,何以在文本中,黃色會首先出場,並且佔據了比較大的視線面積?(黃色是傘面外包覆的顏色,紅色僅是把柄)如果這真的象徵了祖父「老黨人」的身世,無論如何都該以主要代表色優先吧?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就算連結了顏色與左翼的關係,也未必能代表「中共」和「蘇共」——台灣日治時期的左翼,或者與「日共」、「台共」的關係更密切,光憑顏色,是看不出民族光譜的。
其次是位置的問題。放在「左首的牆上」是否就代表了左翼?用同樣的標準解釋,「左首」也只出現了一次。更嚴重的是,小說後段甚至出現了完全相反的描述,那是在祖父垂死的段落,孫子:「我看著他那垂死的臉色,又看見那一支右牆上的大雨傘,傾刻之間,我得到無比的啓示和助力了。」這一次變成右牆了。然而,趙剛對這句話的詮釋暴露了前後不一之處:
明明一向是「掛在左首的牆上」的傘,怎麼這回掛在右牆上了呢?但重點不是「右牆」,小孩不是受到「右牆」的啓示,而是受到了不管掛在哪裡的同樣的那把「大雨傘」的啓示;「右牆」比喻的是祖父的絕望。當然,傘似乎該是隨意地棄在地上或任一角落,才更是絕望的適切表達,但必須瞭解,這裡沒有刻意指出「右牆」,又如何能讓先前所指的「左」不是一個無意義的修辭呢?「右牆」因此有可能是作者刻意的「此地無銀三百兩」。因此,這裡的從左到右,不是說一個不合理的「變節」,而是曲折地說明「左」的隕落。(頁79-80)
這段反反覆覆、強詞奪理的論述,完全摧毀了此一論點的可信度。如果第一次出現「左首」是重要的,第二次出現的「右牆」就不可能「不是重點」。好的詮釋框架,應該要能夠完整解釋文本內的細節,起碼不可以有完全矛盾之處。我們可以想像,如果陳映真在文本之中兩次都把傘放在左首,就不需要這麼多「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解釋,它的象徵意義自然顯明得多。而這一左一右的布置,顯然作者就意不在此,很可能只是一個寫實性的描述而已:左右方位是與視角相對的,上一次的視角是「晚飯時」,這一次的視角卻是從祖父床邊往外望,相反是正常的。文學意義的構造,必須建立在對尋常規則的破壞上,沒有破壞任何規則就不會有「深意」,因為我們無法知道作者是著意如此還是必須如此,也就無從探知作者的意志。我們可以假設一個情況,如果我們接受「右」也可以是一種欲蓋彌彰的「左」,那要是陳映真兩次都把傘安放在右牆上呢?——那或者也可以被解釋成一種左翼理想的衰弱、死滅吧,畢竟祖父最後也死了?這樣一來,如果所有的細節都可以指向同一個意義,那就意味著這些細節本身並無任何特殊意義了。
為什麼趙剛會作出這樣的推論?我認為是某種思考方法上的疏忽有以致之。我們都同意微小的細節可能有很深的象徵意義,但趙剛處理這些細節的方式是純粹演繹的,抓出一個字詞就當做是一條線,在沒有其它旁證的支持下就一路推進;我們的分歧在於,我覺得這個方法必須是演繹與歸納並濟的,要在至少有一個以上的細節,形成相同的象徵指向邏輯(也就可以用同一個詮釋邏輯反推)時,我們才可以就這(些)個細節進行更深的挖掘。文本分析的任務不在於幻想每一個符號都必然有其意義——這是不現實的,雖然我們總是錯誤地期待作家有如此精密的腦袋——,而是先指出某一些符號組合比另外一些更有意義,然後再去解釋它們。畢竟在一個敘事文類裡面,有很多符號可能只是純粹功能性的,幫助情節推進、幫助人物建立、幫助讀者瞭解背景⋯⋯人類的想像力是沒有極限的,所以作為一門知識,文本分析的使用需要極限,需要自我節制。若我們同意評論家可以在沒有這些自我節制的基礎上,就進行無止盡的解讀工程,那基本上任何文本都可以推出任何結論。(就像我們剛才在左右之辯當中看到的,有就是有,沒有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地「有」)所有文本的特殊性,彼此之間的差別也就蕩然無存了。這就宣告了文學的虛無,文學知識的全然無效。
2.「角色」理解的極限
另外一個趙剛的陳映真論述中出現的問題,就更切題地與他所謂「知人論世」的閱讀方法有關,即我們該如何理解小說裡的角色。趙剛對陳映真所有小說的分析,都是為了從中看見陳映真的思想狀態,這個目標設定既使趙剛得到很多敏銳的見解(比如在〈「老六篇」論:在歷史、思想語文學交會處的書寫〉中,透過角色的年齡分析,證明了〈故鄉〉、〈鄉村的教師〉二篇與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關係);但也由於這樣有點先畫靶再射箭的思考方式,使得小說解讀時會出現若干偏誤。在這裡,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是:分析文學作品之時,把目標完全放在「知人」(理解作者)之上會有什麼問題?作者在文本以外的,別處的言論所展現出來的思想,是否能毫無疑問地拿回來解釋文本?更尖銳的是:有沒有可能,作者本人清晰表達過的思想,在他的小說作品中卻得不到夠好的表達、甚至讀者從小說作品能讀出的意義與他的思想竟然背道而馳?
這些問題,具體落實到文本的詮釋上,就很大程度地關乎「我們怎麼理解角色」的問題。若要透過小說「知人」,那就必然要理解小說裡面角色的言行所代表的意念,再從作者對這個角色的安排、處理當中,探知作者對這個角色所代表的意念有什麼感想。因此,讀者要透過小說去「知人」,實際上是一段非常危險、處處可能出現誤讀的旅程。如果我們讀錯了「角色所代表的意念」,讀錯了「作者對這個角色的感想」,那就不可能正確地理解「作者對這個意念的想法」,這是一組處處罅隙的三段論。如同前節所述,其實我們也可以把角色視為一連串符號的特殊組合,附屬在一個人格化的名詞底下。一個角色可能擁有一系列的名詞、形容詞和動詞,來表現它的外觀、狀態和行為。對我們正在討論的議題而言,動詞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是最重要的,因為行動(以及不行動)就意味著選擇,肯認某種立場或排拒某種立場,也就可以從中看到這名角色所代表的意念。
從趙剛對陳映真〈我的弟弟康雄〉中的第一人稱敘事者「姊姊」的分析當中,我們便可以看見這樣的分析是多麼困難、容易造成誤讀。〈我的弟弟康雄〉透過姊姊的第一人稱視角,敘述她的弟弟康雄,一名無政府主義者,如何在理想不能伸張的蒼白絕望中自殺。趙剛對康雄的分析和常見的說法沒有太大的扞格,但對姊姊的評論就很難得到足夠的文本證據了,特別是底下這段談論姊姊在弟弟死後,決意為了家道嫁入豪門的論點。我們再次將論述與文本並置:
| 陳映真〈我的弟弟康雄〉引文 | 趙剛的詮釋 |
|---|---|
| 我答應這樁婚事,也許真想給我可憐的父親以一絲安慰,叫他看見他畢生憑著奮勉和智識所沒有擺脫的貧苦,終於在他的第二代只憑著幾分秀麗的姿色便擺脫掉了。從此流著一部分他自己的血液的子孫,該永遠種植在一塊肥美的土地上了。而事實上,我是存著一分最後的反叛意識,擲下我一切處女時代的夢的。在我的弟弟康雄死後才四個月,我舉行了婚禮;一個非虔信者站在神壇和神父的祝福之前⋯⋯這些都使我感到一種反叛的快感。固然這些快感仍是伴著一種死滅的沉沉的悲哀——向處女時代、向我所沒有好好弄清楚過的那些社會思想和現代藝術的流派告別的悲哀。然而這最後的反叛,卻使我嚐到一絲絲革命的、破壞的、屠殺的和殉道者的亢奮。這對我這樣一個簡單的女子已經夠偉大的了。 | 康雄姊曾經藉著他們的異類的、否定性的精神資源,來支撐她的冷傲姿態,以保護那因貧困家世而易受傷的自尊⋯⋯那麼,她如何把自己出賣呢?如何在出賣自己時保證自尊不受到傷害呢?不用擔心康雄姊吧!她可謂善用她的心理詭計把她因「變節」而生的種種心理疙瘩,給燙得平平的呢。她想,與其慢慢地、被動地被調整成體面世界的一分子,不如主動出擊。她於是以一種潛伏的特工才可能有的「行動的快感」,在弟弟死後四個月,就和一個她其實並沒有感覺的體面之家的男子結婚了。在那個莊嚴的宗教儀式上,她進行了雙重任務:一方面,她悲哀地向「沒有好好弄清楚過的那些社會思想和現代藝術的流派告別」,另一方面,以一個「非虔信者」做虔誠與感動之偽裝,同時冷眼地睥睨地旁觀這些體面的信者。這個雙重任務,使她取得了一種烈士的悲壯,在同志皆亡之下,獨闖敵營。⋯⋯如果康雄的自殺代表的是拒絕沈淪的意志,那麼康雄姊的「烈士行為」所代表的則是接受沈淪的詭計。(頁53-54) |
在這裡,我所欲批判的並不是那種輕挑的語氣,而是造成評論者如此強烈感情的那個論點,似乎缺乏了極為關鍵的論證。在小說的敘述當中,讀者直接讀到的是,姊姊的婚嫁「同時」是一種對世俗價值的墮落和反叛;但在趙剛的詮釋裡,作家真正對姊姊的想法是,她的行為其實只有墮落,即便那種反抗的姿態,也是墮落之後的托辭而已,更顯得其德行之低落。問題是:趙剛怎麼知道那是托辭?這個論點仍然是可能的,只是在整篇小說沒有任何一處可以支持這個論點,趙剛也沒有提出其他證明。在近兩頁的篇幅中,我們看到的不是對這個角色的分析,而是評論者先決定了「這是托辭」,然後用這個視角去理解每一個有關康雄姊的細節。
評論者在此,其實踏入了一個很危險、很難證成其論點的狀況而不自知:他不僅僅是在詮釋一個普通的角色而已,他詮釋的姊姊同時是一個第一人稱敘事者。也就是說,不管我們在小說裡面讀到什麼,我們都要切記,那是從敘事者的眼光當中觀察到的事物。敘事者可能有侷限,可能有私心,我們不能全盤相信它,也不能把它的觀點直接等同於作者的觀點。(因為作者也是有可能不同意自己的敘事者的,就像不同意其他角色那樣)而在〈我的弟弟康雄〉這個討論案例裡,趙剛必須證明的是「姊姊在結婚的反抗意念僅是一種托辭」——這非常非常困難,等於是要證明姊姊是一個「不可靠的敘事者」,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在她的自述當中找到破綻。而這樣的破綻在小說之中有沒有呢?我認為是沒有的,因為敘事者提到自己婚嫁以後之事只有三段,一是上引段落,二是敘事者回想婚禮之中的耶穌形象,與弟弟瘦弱的身體疊合;三是結尾,敘事者發願要為弟弟修一座豪華的墓園,三個段落都抓不到任何一丁點她樂意進入這段婚姻,因而需要捏造托辭的「墮落」的證據。甚至在最後一段裡,有這樣的文字:「這使我感到歉然——富足果真『殘殺了一些』我的『細緻的人性』嗎?貧苦果真使我『卑鄙』,使我『齷齪』嗎?我一點也不想抗辯,但我盡力企圖補償過⋯⋯」一個徹底墮落的人,且善於狡猾地隱藏的人,就算能不露出任何一點說謊的痕跡,起碼也不用進行這麼一段「一點也不想抗辯」,直接認定自己有錯的懺悔吧?最後一個短句中連續兩個曖昧的詞:「盡力」、「企圖」,在在顯示了說這句話的敘事者一點也不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能夠補償這一切。如果論者認為,即便連這樣的懺悔姿態都是狡猾的托辭,那我們又回到了老問題——如果姊姊沒有懺悔自然是墮落,有懺悔也是狡猾的墮落,那不管文本怎麼寫,康雄姊早就被評論者定性了,永遠沒有別的可能性。
在這樣對角色的錯解的基礎上,趙剛犯下了最大的推論錯誤,他寫道:「『為他重修一座豪華的墓園』。陳映真寫到最後大概是真的有點恨康雄姊吧,因為這個永遠只有自己的康雄姊,竟然是以一種幾乎是鞭屍的殘忍對待她所深愛的『我的弟弟康雄』,只為了要安息她自己的死掉的過去。」(頁54)而因著這樣的概念,所以他認為陳映真透過這種姊弟,表現了「某個時代的左翼男性青年的內在水火」(頁55),而有了自我懺悔、自我掙扎的意義。「知人」的目標於焉完成,這篇小說再一次證明了趙剛眼中的陳映真。但是,如前所述,我們無法證明姊姊是那樣墮落到底的角色。更有甚者,即使我們退一萬步,相信這個版本的姊姊為真,我們也不能推出作家「恨」姊姊這麼強烈的情感——從文本來看,作家「不同意」姊姊大概是確實的,但如果要從「不同意」抵達「恨」,作家還需要增加很多否定姊姊的細節(無論明的暗的、實質的象徵的),評論者也還需要非常多的論證去補足,這是一個程度拿捏的問題。如此斬釘截鐵,也就抹煞了很多詮釋可能。比如說,陳映真很可能也同時是同情姊姊的(雖然不如同情康雄那麼多),他真正「恨」、真正批判的最大目標,還是那一整個時代的結構性壓抑。值得玩味的是,在前述〈祖父與傘〉的案例裡,趙剛用很薄弱的證據,試圖把陳映真的小說放在更深遠的脈絡裡觀察;但在這裡,同一位評論家卻反而要用不存在的證據,試圖把陳映真的小說縮限進一個較狹窄的詮釋裡面。
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評論者混淆了「作家的意圖」和「角色的意圖」兩個層次,將它們做了太深的連結。我們可以想像,如果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一位姊姊一樣的人,陳映真或許真的是會「恨」她的吧,這個我們不能確知。但即便我們確知如此,面對已經寫成的〈我的弟弟康雄〉這樣的文本,仍不能說作家一定是帶著恨意在處理這個角色的。文本應該有更寬廣的可能性,和更嚴謹的解讀步驟。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頡頏於星空與大地之間 : 左翼青年陳映真對理想主義與性/兩性問題的反思〉後面評論〈哦!蘇珊娜〉:「對於一個自詡天才,有著為世人所不理解、當局所要獵捕的一腦子叛道思想的青年,能做的充其量只是幾個人相濡以沫地鼓著腮亂扯,這在聰慧如『我』的眼睛中難道看不出來⋯⋯」(頁72)這個「難道看不出來」的判斷沒有任何證據。〈「老六篇」論:在歷史、思想語文學交會處的書寫〉中討論〈鄉村的教師〉,將「為什麼吳錦翔沒有受到二二八事件的衝擊?」(頁242)作為解釋角色人格的重要關鍵。但這很可能是個假問題,論者是先預設了角色應該受到衝擊才開展整套解釋的,但如果在作家的故事藍圖裡,這個歷史背景根本不重要呢?畢竟在小說之中幾乎沒有提及此事。而發表於期刊的〈階級與人性狀態:試論陳映真〈兀自照耀著的太陽〉中的現實主義〉裡,趙剛將故事裡小女孩的死描述為:「小淳是在進行一種『死諫』。」「死諫」的意思是以死亡作為最終的行動,但我們找不到文本當中有任何小淳「主動求死」的痕跡(如同〈山路〉裡面出現過的那樣),怎麼談得上「死諫」?也許陳映真確實有以這場死亡事件來「諫」讀者的意圖,但「作者以角色之死勸諫讀者」不等於「小淳以死亡勸諫他的父母」,那是作家的意圖,不是角色的意圖。理解角色不等於理解作家,理解作家也不能硬套到角色身上,這或者才是一種更尊重小說文本的「物質性基礎」的觀點吧。
3.熱愛作家的危險
在這篇文章裡,我採取了一種以文本證據為最優先的立場,或許在閱讀的預設上就和趙剛有很大的差異了。但同時,趙剛的陳映真論述卻又是現有的文學論述中,很少數進行文本細讀的——也正是如此,本文才能在其基礎上,對「文本詮釋」進行這麼具體的討論,這是必須大大致謝的。但是對我而言,一項關於文本的詮釋,必須盡量地具有普遍性,能夠讓小說自己對讀者說話,而不應過度依賴對作家本人的理解。如果我們希望一位作家的作品能夠經典化,更應該相信作家的作品本身就具有足夠的力量,不應為了使之「更偉大」而勉強用薄弱的證據連結宏大的詮釋;這樣的誤讀,應該不是表達對一位作家的尊敬最好的方式,容易將作品本身工具化、從屬化,也會在方法上抹平了這位作家真正的特殊之處。試想,我們若用同樣的標準去閱讀一些二、三流的文本,是否也能得到這麼多「分析」和「思想」?若能接受這樣的方法,我們反而是在解消陳映真小說超越他人的真正的深度。從趙剛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見對作家陳映真無可置疑的熱愛,這是令人動容的,但在分析上卻是危險的,無法保持某種批判的距離。然而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屏棄文學閱讀中的「個人體驗」或情感衝擊,相反的是,這種情感往往是觸發敏銳詮釋的關鍵,只是它需要一些限縮,不能放任自己的想像永無止境地奔馳。本文從「細節」和「角色」兩個切入點來談,僅是略窺一斑,尚有非常多的「界限」需要我們去探索,希望在這樣的持續辨證當中,能夠發展出更完善、更有說服力的文本詮釋方法。
(刊載於《秘密讀者》2014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