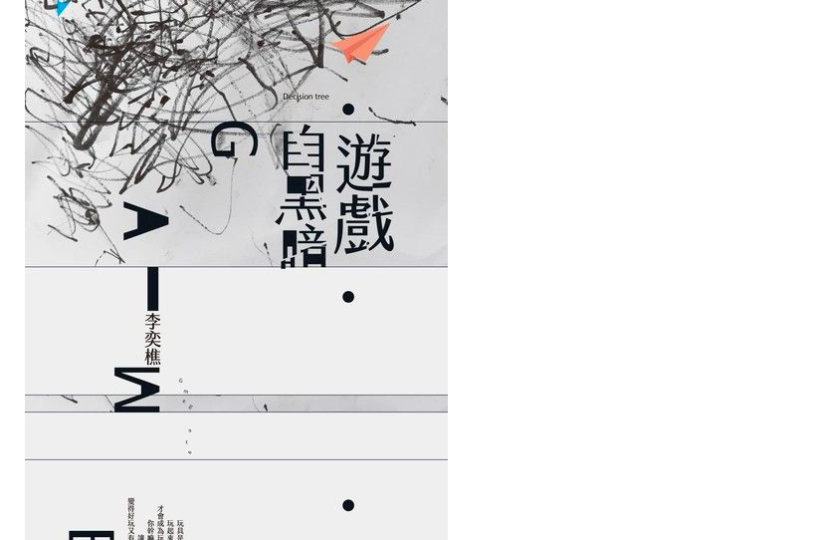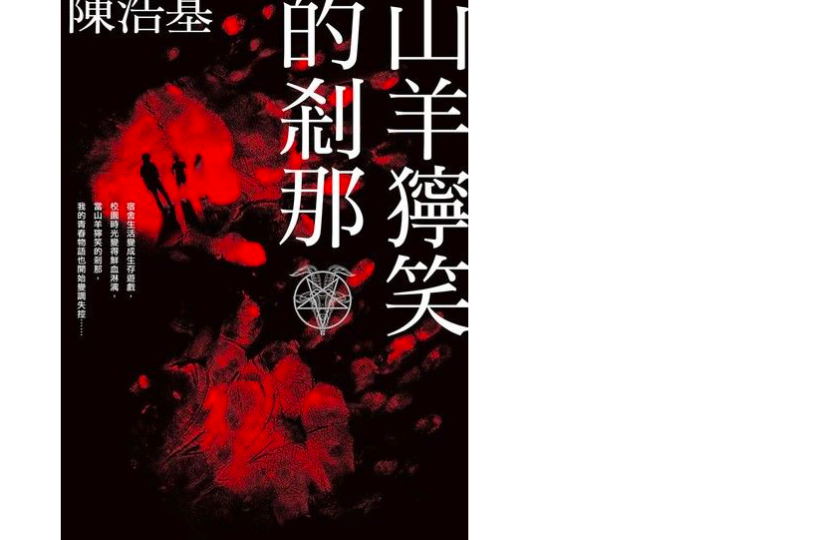然而,睽諸小說實際的表現,不得不說是很令人驚訝甚至是失望的。雖然巴代向來直言自己不善文字經營,但小說敘事表現的粗疏,還是超乎了筆者的預期之外。當然,這樣的判斷可能有欠文化上的反省,也許是筆者身為漢人,對「故事」之結構的想像與卑南族的想像有所落差;也許這樣的粗疏,反映的是原住民文化被迫進入以西方價值、以漢人觀點主導的「文學場域」時,某種翻譯上的艱難。因此,筆者以下的批評,希望能以較為具體的文本細節,來討論此作在小說技術上的失手,以為切磋之意。
筆者認為,《最後的女王》所述的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題材。在眾多部落爭雄、動盪不安的卑南平原上,兼之以外部帝國勢力的威脅、內部氏族的興衰榮辱,這絕對可以寫成好小說,而且可以是不只一本好小說的豐富題材。但巴代的《最後的女王》,有兩個小說技術上的重大問題,使得這篇小說更像是比較鬆散的「史」,而缺乏集中的戲劇力道:一是它的敘事觀點調度不夠準確,二是它的角色塑造和對白都是非常失敗的。
1.敘事觀點的距離
敘事觀點可以想像為電影中「攝影機」的調度,除了一般人都能琅琅上口的「第一人稱」、「第三人稱」這種關於「攝影機放在誰身上」的問題外,更細膩也更關鍵的是「距離」的問題。小說是圍繞著小說人物展開的,所以小說家除了決定第幾人稱,還得決定每一個章節、段落甚至每一句話,要從距離小說人物多遠的地方發聲。從最遠到最近,我們可以簡單分成三種距離:最遠的距離是「綜觀全局的寫法」,它讓攝影機置身於上帝一樣的視角,不限於故事當下的時空,使讀者能從比較外部(也就比較疏遠)的角度看到故事所在的時空脈絡;次遠的距離是「關注人物外部動作的寫法」,它把攝影機放在故事發生當下的時空平面,讓讀者貼近故事的外形,具體看到事件的進展;最近的距離是「關注人物內在動機的寫法」,它的攝影機是放在人物內心當中,讓我們看到特定人物最幽微的心理轉折,因此能夠引起讀者比較大的情感共鳴。
雖然不是鐵律,但在一般狀況下,現代小說通常會將大部份的篇幅放在「次遠」和「最近」兩個層次。因為「最遠」的層次太過疏遠,很容易變成冰冷的歷史敘述,通常只在說明背景的時候少量運用,一旦多了,就會讓讀者像是在讀歷史課本一樣,很難入戲。而後面兩個層次,則很容易讓讀者身歷其境,追隨事件和情感的變化,也才會讓讀者感覺「像」小說。舉例而言,《最後的女王》的楔子就包含了三個層次:
(最遠)
十九世紀下半葉,東台灣傳統的區域霸權「八社番」(註:今日的卑南族)的「彪馬社」,相隔十年發生兩次天花瘟疫肆虐,使得力量由鼎盛榮耀而後極速衰敗;另一個同是「八社番」成員的「呂家望」社,卻掌握機運極速與悄悄的趁勢崛起,與平原北方的花東縱谷內,十數個由西部「西拉雅」、「馬卡道」等平埔族移民的聚落,建立了相當的同盟情誼,勢力早已凌駕於彪馬社之上;而聚集在「寶桑庄」(註:今卑南溪出海口南岸的台東市寶桑里北側)的漢人移民,在彪馬社為了農業發展,而由西部引進當時的「番產」交易商鄭尚之後,日漸成型為一個近百戶的農、商聚落。
(次遠)
那煙雲隨著轎子輕微的搖擺,而呈現出了鋸齒狀,向上揚升變淡,而後消逝。她吸了吸滑出鼻孔的一點鼻液,又不自主的搔了搔纏髮黑巾邊緣的銀質髮箍。舉手間,緞面黑色布料裁剪的寬大衣袖,搔拂著右臉頰,她忽然沒來由的傷感了起來。
這黑色袍掛,是仿照她曾祖母所珍藏的清朝王妃服飾所裁製而來的!她嫁作人婦之後,十幾年來,她一直是以這樣的穿著為底,視居家或出巡的狀況增減裝飾,但曾祖母那個年代早已經離去久遠。
(最近)
是這樣的!的確是這樣的!
一個婦人吸吐著長柄煙斗,坐在由八名漢子扛起的轎子,穿著鑲縫上金色線條與福壽圖紋的黑色漢滿融和式袍掛,頸上幾個銀質項圈攤垂在前襟,黑絨中沉浮著幾分銀亮。她吸了口煙,堅定的這麼想著。
還是得想辦法讓彪馬社重新站立起來。那婦人呼了口煙心裡又說。
我們可以看到,在第一個層次裡完全沒有具體角色的出現,是一種鳥瞰的視野。在二個層次裡,角色出現了,但描述的基本上都是感官可及之物,即讀者如果身在現場,可以看到、聽到、知道的事物。第三個層次則是小說的特權,是唯有透過小說敘述,才能夠自由穿梭的內心情感。
而《最後的女王》的寫法,是三種層次交互應用,並且比一般小說更加偏重第一層次。或許是因為作者的田野資料豐沛,所以自然而然就在小說行文中把歷史的全貌說出來,但比較「像小說」的寫法,應該是設法將這些資料融化、分散在不同的事件與角色身上,轉化成第二與第三層次。而在某些情節緊要之處,更是應該極力避免使用第一層次的疏遠觀點,以免讀者感受不到故事的精彩所在。
比如在第七章的「呂家望事件」,整個故事最緊要的地方應該是呂家望參戰,攻進漢人街道,最後被清軍反攻擊破的整場戰爭。但由於作者堅持將敘事觀點放在彪馬社的達達身上,因此所有關於戰事的經過,都是從轉述得來的。像是呂家望攻打卑南廳的段落:
以及呂家望最終淪陷的段落:翌日,七月十日清晨,彪馬社周邊顯得清淨,南北兩邊都沒有任何關於集結的客家群往南移動與造成騷擾的情形,但才過中午,一早前往卑南廳的張新才慌亂的回到住家向達達說明,呂家望以及縱谷區昨夜南下的客家庄民,已經一舉攻破卑南廳府,並殺進了寶桑街附近街道,沿途燒毀民宅、殺了百餘名男女,現正圍攻張兆連的軍營。
上述兩段都是第一層次的寫法,因此場面雖然浩大,但寫出來卻沒有撼動人心的效果。而這個層次的寫法,如果轉寫成第二層次或第三層次——比如說,安排一名彪馬社的斥侯,用他的敘事觀點轉述;或者把敘事觀點轉到參戰的呂家望青年(布昂?)或漢人身上——,這兩段想必都是能寫成八千字、甚至上萬字的曲折情節。但在第一層次的「摘要」下,寥寥數百字就帶過了,殊為可惜。一直到了八月四日,澎湖鎮總兵吳宏洛率領二千四百人,在卑南溪口登陸,與萬國本、李定明、張兆連會合,總兵力達到了四千多人。這是卑南覓平原第一次出現這麼龐大的漢人武裝部隊,也是大清帝國第一次在東台灣展演現代化建軍,執行陸海聯合作戰的成果。但在呂家望堅強抵抗下,加上大巴六九社、邦邦社不時由側方襲擊,即便丁如昌令人拆了六磅炮四尊,配合洋槍隊強攻呂家望,也沒得到預期的效果。到了八月十四日,丁汝昌又以海上兵輪致遠、靖遠船上艦炮轟炸呂家望社,仍無法使得呂家望等社屈服。於是,八月十五傍晚,萬國本從各隊兵勇之間懸賞徵求敢死隊三百人,個個攜帶五連發步槍,狠狠的吸食完一輪兩輪的鴉片煙後,配合拆下的四尊快砲發動奇襲,終於攻下了位在呂家望西側半山腰的邦邦社。更在十六日乘勝發動總攻擊,大破西門,攻克呂家望,大巴六九社見大勢已去,便宣布放棄抵抗。而北方的客家庄在清軍動用快砲與艦炮時轟擊呂家望時,便遠離卑南覓平原,向北攻擊花蓮地區,遭擊破弭平。
而這種寫法並不只限於這章,而是大部份的章節都有這種問題。《最後的女王》基本的行文邏輯,就是一段最遠層次的大敘述,帶出彪馬社這方的反應,如此交錯前進。作家或許是想要呈現史實與小說情節並進的效果,但這樣的結構設計,帶來的問題可能比帶來的好處要多上不少,值得再三考慮。另外一個延伸出來的問題是,綜觀整篇小說,除了小說中段的部落聯盟巡視、小說末尾的雷公火之役,大部份的情節其實都不是彪馬社主導的,但當這篇小說以「最後的女王」命題時,就彷彿被困守在大部份故事之外了。達達面對大多數的事件,都只能聽轉述、做出消極應對,而不真正涉入事件的進展,也不免讓讀者覺得故事的重心很奇怪,明明主角是女王,但女王大部份時間卻都對故事毫無影響力。
2.角色塑造與對白
上節談論的是比較整體結構的問題,但我認為《最後的女王》更嚴重的問題,在於角色塑造的細部處理和對白有太多失手。如果暫時先不看配角,至少在主要角色上,小說家必須賦予它明確的動機和鮮明的性格。「動機」是角色所追求或避免的東西,「性格」是角色面對事情的一套價值體系。有了動機,故事就能隨著主角的追求或逃避來展開;有了性格,就能讓故事向著特定的方向前進,而形成悲劇或喜劇的必然結果。
從這個觀點來看,《最後的女王》在角色的塑造上非常失敗,幾乎讓人難以相信這是出版過好幾本書的作者所寫的。主角達達的主要動機是復興彪馬社,特別是彪馬社中拉赫拉氏族的榮光,小說中段也安排了部分的愛情戲,所以她另外一條支線的動機是年輕時的愛人布昂。但不管是哪一個動機,達達在全書的三分之二都沒有具體的作為,只在突發狀況發生之後才消極應對。而更扁平的是周圍的重要角色:達達的母親西露姑,兩代漢人通事陳安生、張新才,兩代彪馬社領導人林貴、葛拉勞⋯⋯他們要不就是沒有動機,要不就是動機微弱,而獨特的性格更是完全沒有。所以這篇小說雖然有著驚心動魄的背景,但在雷公火之役之前,完全沒有辦法引起讀者任何的緊張感或懸疑感——因為這些角色之間根本不可能有衝突的,因為小說家並沒有賦予他們動機,當然就沒有什麼好爭的。即使在衝突一觸即發的場合裡,作者往往也讓某個角色說一陣很長的話,彼此就被說服了。這在現代小說而言是很不可思議的,如果人類是一種講道理就能說服的生物,而無自己的執念、情感和利益的話,文學基本上可以不需要存在,小說也可以不必寫。
而在文字細部的問題上,巴代的「敘述」和「對白」也有極大的落差。小說的「敘述」很平穩,並沒有什麼大問題,但「對白」幾乎都不行,邏輯混亂、散漫的毛病無所不在,而且每一句對白若是把說話者的名字遮住,根本認不出是誰說的,顯然這些對白並沒有很好地搭配不同的人物性格。試舉以下兩例討論。首先是小說前中段,卡地步和呂家望兩個部落交戰的消息傳到了彪馬社:
「這兩個番社終於打起來啦?怎麼不多死幾個人啊?」西露姑忽然感到厭惡,聲音微弱,但飽含怒意。「這兩個,從不把我們放在眼裡,想打就打,想怎樣就怎樣,本來還想著有機會大家坐下來談一談,將來怎麼一起攜手合作,看現在的狀況,想也別想了,呸!」
才說完,西露姑掙扎著望向陳安生說:「我們換抽鴉片吧!這麼氣人的事!」
林貴想著事,眼睛空洞著看著幾個仕女忙進忙出,準備鴉片煙具,自己嚥了嚥口水,忍著不附和跟著吸鴉片。近期,他感覺到鴉片毒癮已經要超過他的意志力了。葛拉勞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沉思:
「阿瑪,卡地步與呂家望之間的紛爭也很多年了,這一次交戰,有這麼嚴重嗎?我的意思是,雖然這兩個是與我們相同種族的兄弟番社,他們打起來,對彪馬社的影響在哪裡?他們勢力稍稍減弱不是對我們更有利?」
「他們實力大減,的確對我們繼續掌控卑南覓是有直接的影響,但是作為領導人,我擔心的不是這個,我想陳老爺應該也有同樣的看法吧!」林貴說著,眼神卻飄向陳安生,只見陳安生微笑著只點點頭不語,乾癟的臉上皺紋攪成了一團。
「我不懂了,阿瑪,你們的憂心在哪裡?姊姊,妳懂嗎?」
「葛拉勞啊,你不懂的事,我也不會懂。」達達注視著葛拉勞一會兒,然後說。
顯然易見,這些小說人物大多用一種很幼稚的、不像成人的語調說話,特別是西露姑,這種急躁的語調完全看不到她多年擔任聯盟女王的經驗和霸氣。接下來葛拉勞的第一句話也很有問題,事實上在這段發生之前,彪馬社這邊的人早就因為此二部落不合,而開了很長的會議來討論如何因應,葛拉勞更是親自到呂家望交涉的人,這句「有這麼嚴重嗎?」好像剛才讀者看到的都不算數了一樣。這種寫法,其實是初學者常常出現的一種失誤,因為沒有想清楚如何帶出下面作者想說的話,所以隨便安排一個角色來問問題,好讓其他人順理成章的回答。因此,這句話的功能不是「葛拉勞在問其他角色」,而是「作者幫讀者問其他角色」,反而尷尬地破壞了故事獨立的氛圍,再次導致讀者的「出戲」。
而林貴接下來的「陳老爺應該也有同樣的看法吧!」這句話,則似乎是巴代特殊的書寫習慣。在整篇小說中,常常出現A角色講到一半,突然丟出這句話,讓B角色接著說的詭異結構,完全看不出有什麼好處,反而因此抹滅了角色的獨特性:如果AB角色遇到事情要講的話都一樣,那又何必寫成兩個角色?而在這個段落裡,更詭異的是,當林貴這樣說完後,下一段接著的還是林貴⋯⋯自己丟出去的球自己接,為什麼不把球拿好就好了?比較可能的解釋是,作者希望透過這句話賣一個關子,好讓葛拉勞可以順理成章再問一個問題,然後透過『「葛拉勞啊,你不懂的事,我也不會懂。」達達注視著葛拉勞一會兒,然後說。』這句話,來表明達達比葛拉勞高明——因為她「注視」的那一會兒,暗示讀者她其實知道長輩的擔憂何在,但為了自身氏族的繁榮,她不願意洩漏自己的底牌、也不願意指點繼承權上的對手葛拉勞。最後這兩行的寫法雖然有些刻意,但還算是有想法的,問題是為了置入這兩行,而把林貴的對白硬生生打斷、並且讓林貴從一個老謀深算的阿雅萬變成一個賣無聊關子的笨蛋,值得嗎?
第二個例子,則發生在呂家望正式向官廳宣戰,攻打卑南廳的消息傳來時。在這個段落發生前,彪馬社已經得到了相關的消息,長老們開了一次會,決定這次兩不相助,保持中立。彪馬社的策略是讓他們最大的對手呂家望去招惹官廳,這樣他們自然會被清軍攻擊而削弱實力。接下來,呂家望果然採取了軍事行動,彪馬社的領袖們再次開會:
「新才,你說說看吧,我們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林貴說。
「這個……」張新才張了嘴,看了一眼達達,又環視眾人,「這個問題我不好多說,畢竟番社裡的事,還是要由各位領導人協商處理。不過還是要按照女王以及陳安生老爺的想法與過去這事的習慣,我認為還是應該還是比照上一回薙髮事件,保持關心,避免介入。」
「那這個樣子,還談什麼聯盟情誼?這一段時間的經營不就白忙了嘛?」達達忽然感到有些憤怒,冷冷的說。
「這個……」張新才欲言又止。達達的憤怒他理解,又似乎有些不明白。
「這一點,大家要冷靜冷靜,找出最好的辦法啊。」林貴企圖緩和氣氛。
「算了,這個話我來說好了。」達達丟了一顆處理過的檳榔入口,接著說。
「伊娜跟陳老爺說過了很多次,我們現在的實力已大不如前,跟呂家望結盟也只會淪為配角,跟官府鬥,即使贏了眼前,最後也會輸,而且未來如果官府報復,有可能造成我們自己番社的解體。所以,如果非要找誰合作結盟就該找官府,否則就應該保持中立。老實說,我並不喜歡這樣,但是這是現實,而且,如果能……」達達忽然住嘴。
這裏有非常明顯的矛盾,特別是發生在達達的反應上。達達的第一句話是:「那這個樣子,還談什麼聯盟情誼?這一段時間的經營不就白忙了嘛?」這句話完全莫名其妙——這本書從呂家望出現開始到現在,彪馬社的立場一直都是不干涉、冷眼旁觀他們引火自焚、並且趁此機會壯大自己。達達怎麼會在第六章才突然顧及起「聯盟情誼」了起來?更別說就在這話前面沒幾頁的地方,達達是親自和所有長老討論自保措施,並且還聲明了以後由她代行女王職務的,自己的策略怎麼會自己立刻忘記?於是這句話果然引起了其他角色的困惑(別說是角色了,讀者也很困惑⋯⋯),達達竟又接了一句:「算了,這個話我來說好了。」於是我們才發現,這有是一個A角色拋球給A角色自己接的遊戲,而且接球的姿勢還很生硬。——「算了」的語氣,好像是大家陷入僵局、所以只好由達達來打開局面,但問題是僵局是反復無常的達達自己產生的呀。而從小說的功能來看,這裏的轉折也看不出任何意義。如果作者意圖呈現達達的內心掙扎,比較「常規」的做法應該是同時去寫「對白」和「內心獨白」,形成「嘴巴上講要削弱呂家望,心裡卻很猶豫,不知道該不該破壞部落情誼」的情況,而不是像連續劇一樣,把所有內心獨白都寫成對白說出來。
以上兩點,是筆者希望和小說家商榷的一些技術問題。這些東西都無關乎思想、題材和風格,可以純粹在技術上校訂得更加精準,而不傷害到小說原本打算表達的東西。希望這樣的談論不會讓作者覺得過於冒犯。畢竟作者宏大的寫作計畫和特殊的視角,絕對有機會成為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如果作者不僅以「紀錄」為滿足,而希望真的抵達「創作」之境的話,他其實已經站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再補上一些基本動作就可以超越其他創作者了。
(刊載於《秘密讀者》2015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