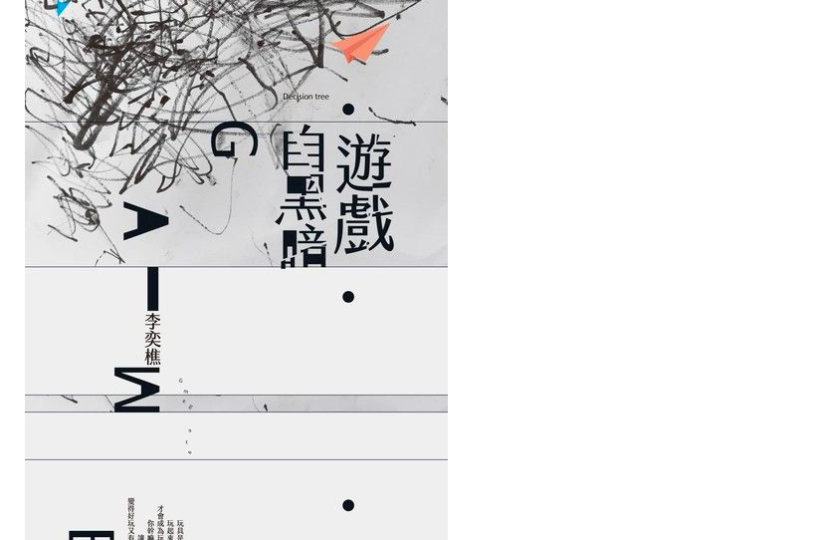《房間》是楊婕的第一本散文集。全書分為五輯,共收錄六十餘篇散文,最長者近萬字,但大部分均是兩千字以下的短篇散文。除了第五輯〈地契-霧中書〉的大部分篇章,是描述一段逝去的遠距離戀情之外,其餘四輯確實都是圍繞著一個個「房間」去書寫的,耐心的讀者幾乎可以按圖索驥,建構出作者十八歲離家之後的「房間史」,乃至於房中的細小物件。由此來看,這本書的推薦者、並且也是新書座談講者當中,出現寫了《物裡學》的李明璁,倒也是有脈絡可循之事,特別是輯二〈回收物〉的詞條形式。但兩者相像的幾乎只有書的形式結構,寫法基本上完全不同。楊婕的房間—小物基本上缺乏(或刻意避免?)李明璁隨手拈入的文化史、理論反思,而是走純然抒情一路。這是本書最明確的風格,或也是最危險之所在:也許是太純、太抒情了。
作為參照對象,我們或可將楊婕的《房間》和同世代的三位女性散文家對比:吳妮民的《暮至台北停車未》、神小風的《百分之九十八的平庸少女》、言叔夏的《白馬走過天亮》。吳妮民《暮至台北停車未》以家族故事為軸,敘事成分頗高,有時甚至敘事重於抒情;神小風《百分之九十八的平庸少女》則是比較「中庸」的案例,中規中矩,情必緣於事而發。與此二書相較,《房間》的抒情非常濃烈,但敘事的部分卻被壓到極低,除了第五輯、和〈作親〉等少數篇章稍微讓讀者窺得較多人物關係外,大部份時候都無「本事」可言。但純走抒情一路,而不靠具體情事來引動讀者的共鳴,那恐怕就得仰仗文字上的「內力」,就此而言,《房間》在語言的詩意上卻又不如言叔夏《白馬走過天亮》走得那麼遠。
簡言之,這是一本「沒什麼事」的散文集。並不是真的無話可說,而是作家的書寫策略,幾乎就像是刻意將所有情節刪除,僅留那些際遇生發出來的感懷而已。創作年代最早的一篇,也是全書點題篇章的〈房間〉就有這樣的段落:「有時我在房間裡失神,過往如水流激越,崩解、碎裂。思緒湧動的狀態多在夜晚,冬日深夜滿是透明的冷,我獨自承受睡眠的輪迴,失眠時倒一杯酒,小口地喝。」(頁25-26,底線為筆者所加)在這裡,應當是情感來源的「過往」到底是什麼?那些失眠的夜裡,敘事我又「承受」了什麼?這是終其篇章也找不到線索的。或如〈鬼屋〉,描述的是一段奇妙的時光,敘事我違規寄居在某一「女博士生」的宿舍裡,終至被「樓主」發現趕出。從若干用詞(如女博士生答應說:「行。」)和細節來看(裝水要刷水卡,按時間計費),讀者可以模糊感覺到那場景有點奇怪,不太像是台灣。但整篇文章都沒有提及具體的時空脈絡,要在往後其他篇章的交叉比對當中,我們才會發現,那應當是作者在北京旅行的遭遇——同樣的旅行空間,還包含了四川(〈作親〉結語提到的)和雲南(〈青年旅舍〉等篇提及的)。而令筆者疑惑的是:為什麼要隱藏這些並不關鍵的細節呢?
受過長期文學獎規訓、以及內化了各種台灣文學場域規範的我輩文青,大概都得練出一身「藏」的好本事。文章忌直白、意念忌淺近,已是台灣純文學寫作者和讀者之間樂此不疲的語言遊戲,或至少也是默契。但即使是在這樣已經有些僵化的文學傳統裡,「藏」強調的也是「最重要的話不能說」,對於支撐行文邏輯的細節,還是多以不肥腫為前提去寫它。但楊婕的散文似乎著意進行一種純化工程,一意埋藏細節,只願意透露「結論」。即便在情節相對較多的〈作親〉裡,我們還是感覺到,在房東叔叔阿姨的熱情背後,真正情感的核心事件並未顯露:「當時未曾提及的願望和困擾,在時間磨洗下,終於揭開面貌,還給生活本身,變得不再重要。」(頁39)不只是當時未曾提及啊,基本上整本書都沒有提及,或者因為剪接的隱匿,就算提了讀者也無法辨識。而全書情感最濃烈的第五輯,也時有這樣的句子:「我怕我的到來讓你更了解毀棄。」(頁237)「我們說好去看海,一起逛賣場、夜市,以及所有能紓解慾望的形式。不向任何人掩飾關係,儘管關係剛剛開始。」(243頁)從行文的「過去式」腔調來看,我們大概只能知道這些文章談的是一段逝去的愛情,所以這類哀傷的感懷可以理解。但能理解不見得能共感,不斷壓抑埋藏的書寫策略,結果反而是使讀者很難進入作者投射的情感狀態裡。
在一定程度上,這會不會是被規訓過頭的結果?太會「藏」,以至於「藏」作為一種展示手段,竟爾篡成為目的本身,而遺落了本當展示給讀者的東西?
當然,這不是在說作家所表達的感情是虛假的、空無的。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底下濃烈流動的情感是假不了的。但楊婕的書寫方式,卻在在讓筆者想起了BBS個人版(比如ptt2或各大學自己的站點)時代的抒情模式。在那還沒有「時間軸」的年代,讀者在個人版之間游移,閱讀每一個性格強烈的板塊。那些「個版文」形成了很奇特的抒情狀態,某種程度上它是私密的——因為在「隱版」等手段之下,能夠閱讀到某個個人的版塊,本身就是一種版主和讀者之間的特許默契——,但很多時候卻也是疏離的。因為個版文往往成為一種投射、宣示,特別涉及到情感事件時,我輩文青的文章往往寫成濃烈的抒情文字,外人看來毫無細節,但在最微小的「字」調動中,都夾藏了大量的暗碼。
你看不出暗碼,就知道那些話不是對你說的,你不是那個「某人」,那個C、O或「你」。
而對於看得出暗碼的人,則能從中讀出無限的記憶細節。
那是一種既展示又隱藏的文字,一種精準投擲的技術。
但這是適合一本散文集的寫法嗎?筆者對此是遲疑的。「出版」的公共性質,與「個版」的半公開狀態,畢竟不是同一性質的。在出版之後,或許作家更需要多想一點的問題是,為什麼讀者必須翻開、必須讀下去?讓這些作品進入公眾視閾的理由是什麼?抒情但也疏離,這樣的寫法,會不會使得抒情成為一種「表演」性質的文字展示,讀者無法進入作家設置的情感狀態裡,看到的不是誰的心思流轉,而是「我在抒情」這件事?能否再有事一點,讓我們真的看到房間裡外,人們來去的痕跡?這或者是作家接下來可以再思考的問題。
(刊載於《秘密讀者》2015年10月號)
如果再有事一點:讀楊婕《房間》
2015/10/20 _文學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