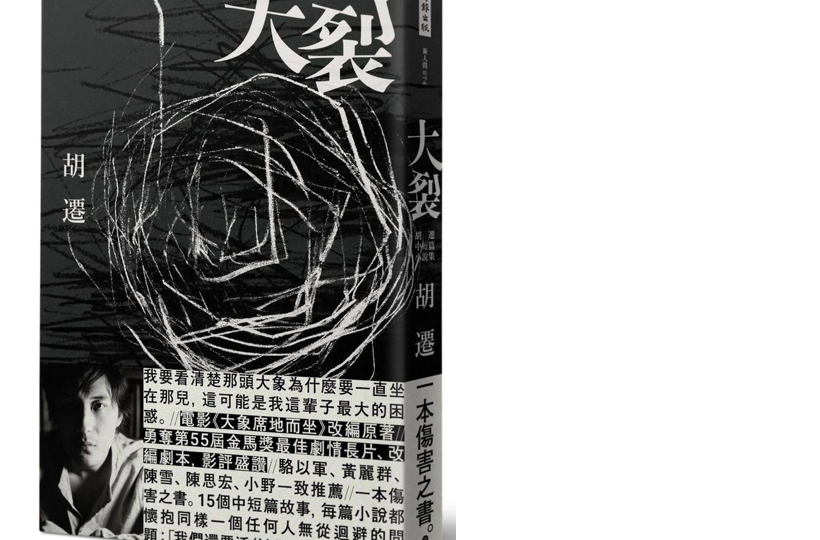小說家張亦絢在2015年年底才出版的《永別書》甫上市未久,旋即在文學讀者圈內引起了一陣驚嘆。這在文學書嚴重下挫、長篇小說又飽和攻擊般連環出版的去年來說,是頗為罕見的現象。這本以「記憶」為線索,串起族群與性別兩大主題的小說,寫法其實有點「非典型」:在第一人稱敘事者賀殷殷強勢的帶動下,它的故事線其實是條虛線,推進的邏輯(如果有推進的話)依靠的是賀殷殷對自身記憶的整理,是名副其實的「人生整理術」,整理到哪就寫到哪。
而從行文風格上來看,《永別書》更像一部由虛構角色寫下的超長篇散文,而且是比台灣尋常定義下的(抒情)「散文」更具有思辨性、論述性的。在戰後的台灣文學史上,能以此寫法寫出成績者並不多,很容易讓讀者聯想到施明正、邱妙津兩位「壞掉」的小說家。有趣的是,《永別書》的內文明白地提到了邱妙津,並且都是以小說家賀殷殷對小說家邱妙津的評價說出來的。比如提到《鱷魚手記》中的段落,賀殷殷批評:「我不記得我曾滿意過邱妙津的書寫⋯⋯我讀到的是廉價的賣弄。」(p.89)或者在後段,含蓄地提及了《蒙馬特遺書》中的場景:「邱妙津筆下的主角,在得不到愛時,會猛撞電話亭;在我這一生中,偶爾我會想起這個畫面——帶著一點輕蔑地想:如果為此要撞電話亭,即使有一百個電話亭,也是不夠撞的。」(p.133)這樣的批評,其實並不能視為小說家對邱妙津「路線」的拒斥,反而正好說明,兩位小說家在某個層次上,是走在類似的道路上的,那種以思想的深美、情緒的刻描為標誌,而不著意於戲劇性的寫法。而且,觀諸《永別書》的表現,賀殷殷顯然很有對前輩皺眉的理由,邱妙津書寫中的生命刻痕或者難以抹滅,但在思想或技藝上,這本書很明顯是後出轉精了。
另外,這種雄辯的風格也令人想到舊俄小說的傳統——那或者是六年級以上的文學青年所必備,但當代文青多半不太熟悉的文學教養了。這點也可以從貫串全書的托爾斯泰追索回去。
當然,以上試圖安放《永別書》之譜系的討論,對於解讀文本來說,不見得是最重要的。但由此可以延伸出來的一個問題是:小說家採取了這套寫法,造成了什麼樣的效果?
這種寫法很容易造成的危機,是敘事動力的無以為繼。因為沒有夠強的故事「位能」,讀者隨時可能在某一頁產生了「為什麼我要往下一頁翻呢?」的念頭,只要一秒,就能讓這本書土崩瓦解。在《永別書》的前半,張亦絢幾乎是仗著自身渾厚的內力在「推」著小說走的。前述提到的「思想的深美」,在這本書裡面,不但是最重要的「內容」成份,也是最重要的「技藝」成份,那些關於族群的、性別的、文學的、人性的辯證,必須每一段都有足夠的亮點,才能讓讀者自然而然想聽作家「多說一點」。故事的一千零一夜,靠的是懸疑;《永別書》的一千零一夜,靠的是:「天啊,你還有多少關於人類的奧秘可以跟我說?」所以小說的外型雖然看似渾重,在我讀來卻幾乎是段段走在一根極細的絲線上:這段超有梗,但如果下一段⋯⋯啊,這也超有梗,那下一段⋯⋯?
於是,《永別書》成為一本奢華的小說。這不是在說它的文字風格,而是它蠻不在乎拋出「新梗」的頻率。幾乎每一個章節中,我們都可以找到五六七八個段落,其中的靈思是至少足以捶打成一個短篇小說的;但它就這樣幾百字寫過去,用掉了,然後從另一邊口袋再掏一個差不多好的出來。
不過,人的內力畢竟有時盡,這樣的寫法要撐到將近四百頁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第七章左右,張亦絢開始伏下了小說當中唯一的敘事動力機關,那就是「兩次爆炸」。從第七章開始,每一個章節的最後,都暗示了「爆炸」的性質和重要性。第七章的最後一句話是從小惠的性雜交陷阱,引伸到:「被詛咒的家族⋯⋯這並不是,我們這個家族,第一件,性雜交事件。」(p.159)在此,埋下了「第一起是什麼呢?」的懸疑佈置。第八章的最後一句則是:「那個『真正的客家人』,那個母親的父親,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因為他,他可是闖了大禍。」(p.183)敏銳的讀者大致已能猜到,「大禍」大概就是那「第一起」事件了吧?終卷後,我們會知道這個想法並不完全正確,但確實也是故事的部分事實。第九章的最後一句話是:「因為當不能浪費時,就是真實迎面——而真實,真實非常要命。」(p.203)要命的「真實」,如果不是跟家族中的性雜交有關的爆炸,還能是什麼呢?第十到十一章更進一步梳理家族和情慾的主題,最終逼近了第十一章最後的關鍵字:「亂倫」。在這麼長的鋪陳之後,第十二章,也就是小說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地方,我們迎來了第一次的「爆炸」。
也就是說,如果要分析這本書的結構,我大概會分為「前六章」、「七到十二章」、「十三到二十章」來區分。第一個區塊定調了所有基本思路,第二個區塊讓「爆炸」浮現,第三個區塊就是爆後餘生了。在這樣的區分下,只有第二個區塊塑造了比較強的敘事動力,第一區塊與第三區塊則更是思辨性的。
這樣的區分,其實只是一種後設分析,並不帶有任何價值判斷。在別的小說裡,失去敘事動力的章節,幾乎都會像是螺旋槳停止運轉的飛機一樣墜毀,但《永別書》的渾厚內力是個例外。對於一個在意「故事」的小說讀者如我而言,我很驚訝地發現,我竟然反而對有敘事動力的第二區塊感到淡淡的遺憾。那不是說它寫不好,而比較像是嘆了一口氣:「唉,人力終是有其極限的啊。」——飛過大洋的途中,螺旋槳畢竟還是轉了一陣子,沒能一路滑翔越過整座海洋啊。這當然是過於任性的期待了。
我們幾乎可以這樣說:《永別書》最好的地方,就是它永遠能找到最漂亮的姿勢,「迎面」處理各種真實,無需依賴象徵、隱喻或敘事技巧的閃躲。它幾乎不需要曖昧的美感,線條清晰,強悍而美麗。但這只是表面,當我們讚歎於那些自我辨析外省身份與性別認同的精彩拉扯時(同樣去年出版,卻扁平得不忍卒睹的朱天心《三十三年夢》,剛好就是最好的對照組),我們或該特別注意小說家的結構設計:在那些思考後面,真正深埋的傷痛是兩次「爆炸」。
為什麼可以這麼「誠實」(在小說的意義上)地寫外省人和台獨的糾葛?為什麼可以這麼「誠實」地寫小朱、萱暄所帶來的傷害?為什麼敘事者總不害怕暴露自己的軟弱和自我矛盾?
因為比起「爆炸」,這些東西都只是表面。
所以弔詭的是,賀殷殷之所以能夠在很多地方誠實無諱,那是因為她另有難以啟齒之事。看似「迎面」書寫一切,什麼都沒在怕的《永別書》,其實是一個欲言又止的故事——為了第十二章的「爆炸」,它可是有(第二區塊的)整整五個章節都在拖延。那是幾次漫長的深呼吸。甚至我們幾乎也可以這樣說,前六章或許也是另類的「顧左右而言他」,開頭宣告了這場遺忘之旅之後,敘事者其實是先從外圍的枝蔓開始修剪起的,並沒有一刀就切入核心。
毫無疑問,賀殷殷的遺忘方法學是別出心裁的:將記憶說出,然後辨析成另外一個樣子,從此使得那個記憶不再是本來面目。但最難的是第一個部分,因此我們會看到,真正「爆炸」的本體描述是非常非常少的。第一次爆炸的亂倫事件,我們大概只能很間接地猜測到模糊的畫面(在關於「不吃老虎」的段落),在行文上不斷地「一沾即走」,稍一碰觸到這傷痛的核心,賀殷殷就會引用更多聽說的故事來引申它。說得越多,事件的本體越是凐杳難現,越是埋在大量的事例與分析當中。到最後,連分析都被中斷了,在第十九章:「我最終將一萬多字的亂倫分析,在此刪去了。還是過於殘暴了,這種記憶。」(p.384)那或許太靠近核心了,三百八十頁的深呼吸還是不夠讓人鼓起勇氣去碰觸它。相較之下,第二次爆炸雖然啟動了這趟遺忘之旅,卻更顯得「稍微沒那麼嚴重」——它就像是第一次爆炸的餘震一樣。沒那麼巨大,沒那麼痛,於是更容易說出來。
這部充滿雄辯風格,直來直往的小說,最終告訴我們的,或許竟還是「迎面」的困難。
而在小說的結尾,張亦絢安排了一道諷刺的機關。小說拉到當代的,318運動的時空(——題外話,不是說「太陽花」而是「318」,真是太好了。),並且說出了一句非常溫柔的建議:「給她時間,而非時代。」(p.385)那是針對「運動」的建議,看起來也像是賀殷殷送給自己的一句話。畢竟我們才剛剛看到她在第十八章,被一對維也納的情侶救贖了。這趟遺忘之旅、記憶清理之旅、人生整理術大展,或能有一個好結果吧?結果到了第二十章,敘事者的生命嘎然而斷,在「3的玩笑」之後死去了。
那終究是無可描述,無可救贖的吧——賀殷殷留給我們的最後一句話,如果我略知法語的朋友沒有錯譯的話,應該是:「我丟下你們了。」
真是倔將的一部《(_____)遺書》啊。無法迎面,卻要留給人們飄然而去的背影。
(刊載於《秘密讀者》2016年1月號)
迎面的困難——讀張亦絢《永別書》
2016/01/20 _文學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