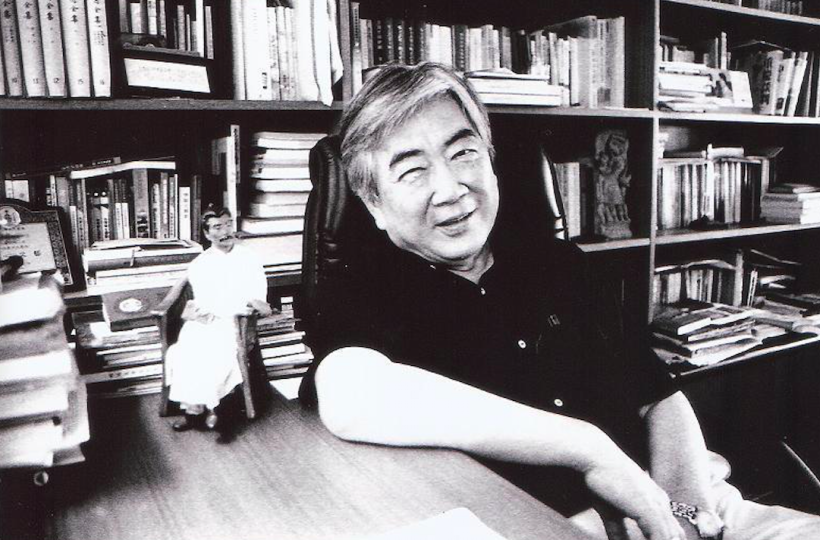在當代的台灣,小說家陳映真或許是一個有點微妙的存在,這種微妙感源於他最主要的兩個政治位置:左派以及中國民族主義者。如果以「左右」、「統獨」這兩道台灣最主要的政治光譜來安置,應該可毫無疑義地歸入「左統」一系,作家也以加入中國作協的行動「明志」,顯示了他異於常人的堅定立場——他似乎是極少數從來不曾對中國感到失望、幻滅(或是有也不影響他的立場)的知識份子之一。因此,趙剛、陳光興等當代台灣左派知識份子,之所以在近年極力回頭「挖掘」陳映真這顆「橙紅的早星」,也是出於某種為了「左統」建立思想傳承譜系的建構工程。
然而,人之為人,就在於任何建構出來的模型,總是很難真正處理人的複雜性。陳明成的《陳映真現象》正好提出了幾個破口,可與左派眼中的陳映真、甚至是陳映真自述的陳映真相質。《陳映真現象》長達五百多頁,但其實主要發現可以簡單概括為兩點:一、從史料考證,發覺陳映真筆下的生父與養父,都被隱藏了日治時期的真正行止,以符應作家的中國民族主義認同。二、從一批書信文獻的交叉比對中,找到早年陳映真的認同並非一開始就如此「堅貞」,而是有著階段性的改變。(陳明成,《陳映真現象》(台北:前衛出版社,2013年))
而提出這兩點顯然是危險的,這完全踩到了奉陳映真為教主的當代左派知識份子的紅線。因而這本書大多數的篇幅,都是在以數量極巨的史料反覆申說上述論點,唯恐論述稍有不嚴,便將授人以柄。《陳映真現象》書出至今,幾乎令所有此一立場的知識份子咬牙切齒,刻意漠視與叫囂威脅均有,但仍未有任何論述能夠駁倒此書,足證此書用功之深。
事實上,如果撇除這些政治觀點,回到文學本身的立場,陳明成的《陳映真現象》其實是為如何解讀陳映真的作品,立下了巨大的功勞,幾乎可以說是「板塊運動」等級的認識基礎巨變。在這本書當中,最驚人的發現當屬第一章〈在「台灣行進曲」的年代〉和第二章〈在「大刀進行曲」的晚會〉當中的論證,前者主要討論陳映真的生父陳炎興、後者則討論養父陳根旺。眾所週知,陳映真在〈父親〉、〈後街〉、〈鞭子與提燈〉等文當中,所述之父親形象均是堅定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在日治時代當中不改氣節,在子孫心中「守住了一個祖國」,「一個實在的祖國」(陳映真〈父親〉,《父親》(台北:洪範,2004年),p.149)。
這些資料,都是過去陳映真的研究者賴以為推論基礎的傳記資料。但是,根據陳明成的考證,這些以散文形式撰寫出來的作品,其實並不完全是真實的。若是比對日治時期的史料,會發現內中隱匿了大量關鍵資料,以至於和陳映真的自述極難咬合。〈在「台灣行進曲」的年代〉花了極大的篇幅證明了兩件事:陳映真的生父陳炎興其實是日治時期皇民歌曲比賽的獲獎者,他創作的「台灣行進曲」傳唱一時,在廣播節目當中一再重播,並且至少有九個版本的唱片發行。(陳明成,p.44)該比賽是兩階段的,首先徵求歌詞,然後以得獎歌詞徵求作曲。這首得獎的「台灣進行曲」歌詞當然是呼應時局,滿溢著皇民化宣傳的詞句:「當陽光照耀在亞洲的早晨 / 觸目所及 / 都將是大和島國統治紮根的領土⋯⋯啊,萬世一系的天皇呀 / 即便是水窪旁的小草都會為您 / 殉死盡忠、如此赤膽忠誠 / 這就是神州日本、咱們台灣。」(陳明成,p.35)這個比賽過程,代表陳炎興並非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參加比賽的,而且這樣一個高獎金、自由徵稿的比賽,也並非時人的「義務」,是有參加與否的選擇空間的。就此而論,陳炎興其實在歷史上應該更接近一個在日治時期適應良好的皇民化運動協力者,而非一個未曾動搖的中國民族主義者。
而在〈在「大刀進行曲」的晚會〉裡,陳明成透過1926年的一則「警務新聞」,考證出了陳映真的繼父陳根旺在日治時期真正的工作——那是陳映真所有的記敘當中都未曾提及的——,他其實是日本時期的一名警察,並且在這一年升任了「巡查部長」:「海山郡鶯歌庄鶯歌派出所勤務巡查陳根旺氏,自奉斯職以來,頗具熱心研究,者番應巡查部長之試驗遂及第云。」(陳明成,p.84-85)而在這一年之前,全台灣的日本警官,從最高階往下,總共只有警視15人、警部220人、警部補270人、巡查部長652人。警部補以上沒有台灣人,而巡查部長當中,僅有兩名台灣人,直到1926年台北州的陳根旺、台南州的楊克紹及新竹州的鍾日紅加入為止。陳根旺不但是警察,還是殖民體系下,台灣人當中位階最高的警官。
《陳映真現象》之所以引起左派知識份子的憤怒,主因就是這兩章的考證,不少人主張這是「鞭屍老子、糟蹋兒子」的做法。但這種想法,本身就暴露了論者的意識形態底蘊——他們從一開始就認為日治時期是骯髒的,無意去同理台灣人在日治時期求生存的困難和抉擇。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忠誠度如此精純,以致近於法西斯。但暫時擱置這些爭議不看,真正重要的文學議題是:陳映真顯然花了極大的力氣去虛構了自己的兩個父親,將「皇民的」通通消音、隱藏,然後代之以「守住祖國」的父親敘事。為什麼?或者說,如果陳映真是這樣看待他的父親,我們如何將之納入考慮,來詮釋陳映真的小說?
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用這條脈絡來解釋陳映真小說中的「罪咎」意識。「罪咎」是陳映真小說中最明確的特徵,從第一篇小說〈麵攤〉裡,夾在丈夫、警察、病兒三人之間依違難定的妻子開始,一貫穿早期名作〈我的弟弟康雄〉等,直到小說成就最高峰的〈山路〉,一股不見得找得到明確原因的「罪咎意識」總是彌漫其中。他的角色如果不是已經犯錯,就是將要犯錯,而且基本上沒有贖罪的結構可能。在陳明成的《陳映真現象》出版以前,最常見的兩種解釋,是將之歸因於基督教信仰的原罪意識,是一種宗教式的自苦;或者,將之視為某種左派憂鬱,有理想而難伸、有良知而不能行、只能坐視他人苦難的罪惡感。
這兩種解釋都是可能的,但陳明成《陳映真現象》考證出來的「虛構的父親」,或許能帶來第三種可能的解釋。如果青年時期的陳映真,就漸漸由於各種經歷而成為一個堅貞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堅決拒斥「台灣」所代表的分離主義和地方主義的話,那他的意識形態自然也很容易和官方意識形態當中的反日論述共構。畢竟那是八年抗戰的「國仇家恨」。然而,這就和陳映真的本省人出身——包括生父陳炎興和養父陳根旺——的歷史位置有了嚴重的衝突。經歷過日治時代的本省人家庭,已被「玷污」,更何況兩個父親都還是某種意義上的「皇民協力者」,這該如何面對?更尷尬的是,這些「玷污」的痕跡,都是在那個陳映真還不在的時代發生的,他出生面對已是既成的歷史,無法改變當初那些選擇了。某種意義上,如果父親們是叛國者、漢奸,那陳映真註定就是叛國者之子與漢奸之子。
那是帶在血裡面的罪。這樣的精神刻痕,閃現在小說當中的,就是小說角色時常出現的「無理由的罪咎」。你有罪,不是因為你做錯了什麼,是因為你生而為你;或者說,錯誤早在你不經意的時候就種下了——〈我的弟弟康雄〉、〈鄉村的教師〉、〈祖父與傘〉⋯⋯。陳映真的人物反映的是他對歷史處境的焦慮,這與他「覆寫」家族歷史的敘述是共構的。一方面他的「父親」敘事遮掩日治時代的紀錄,一方面他也試著以「師法魯迅」的說法,來掩蓋自己濃厚的日本風格,如陳明成第四章〈「失落」的台灣文學史〉所述,1960年代早期的陳映真曾經對鍾肇政說過,他對如何在中文當中融入日文風格有著濃厚的興趣,而在私信當中也屢屢有日語的單詞和語法夾雜其中(比如以「姿」來代換「形象」的用法)。但這些痕跡,在1960年代中期,他從淺井基文處開始接觸左派思想、乃至入獄認識了真正的地下黨人團體,鞏固了他左的與中國的政治之後,就煙消雲散了。
但一處掩蓋的,往往就在另一處露出了縫隙。如果我們回頭去整理陳映真的小說,會發現他小說中的「父親」敘事與「罪咎」的結合,是非常可觀的。比如〈那麼衰老的眼淚〉,裡面因為與女僕亂倫而失去兒子敬重的康先生,最終連女僕的愛都失去了,因為他「不能擁有一個孩子」;而〈蘋果樹〉當中的飄浪少年林武治,之所以離家,正是因為他無法阻止父親的不義,「但是我出來了又有什麼用呢?每天每天我的用度仍舊是那些不義的銅錢。」(陳映真《我的弟弟康雄》(台北:洪範,2001年),p.152)疊上陳映真「比較接近真實的父親」脈絡,此句的情緒指向昭然若揭。〈兀自照耀的太陽〉是一群父母輩的成人,看著真正有人道精神的小女孩死去,除了說話以外未曾伸出援手,這些父母們說的也都是「洗心革面」之類的話;換句話說,他們本來就過著罪惡的生活。〈某一個日午〉寫的是一名高官的兒子因不明的原因自殺,當高官終於盼來兒子的遺書時,才知道兒子的自愧,是因為發現父親背叛了自己少年時的理想,腐敗至此。又是帶在血裡的罪惡,兒子除了一死,無可解消這些罪惡:「您使我開眼,但也使我明白我們一切所恃以生活的,莫非巨大的組織性的欺罔。更其不幸的是:您使我明白了,我自己便是那欺罔的本身。欺罔者受到欺罔。」(陳映真《上班族的一日》(台北:人間出版社,1995年),p.44)
最值得用這條線索挖掘的,或許正是長期被忽略的〈永恆的大地〉。這篇稱不上優秀的作品,在凌亂晦澀的文字風格之下,其實埋藏著非常咬合的象徵設定,垂老的父親象徵國民黨法統,無主見的兒子象徵台灣人,「伊」則是「大地之母」。這幾乎可說是呆板的一組對應,或許沒有太深的寓意可說,但考慮到陳映真執意隱藏的這些「父的暗面」,這一集中火力去寫父親之顢頇邪惡的小說,或許可以從中找出陳映真「過不去」的精神關口。最有趣的是,這令人痛苦的「父」,所承載的不再是抽象的「罪」,反而是國民黨持守的法統,那套中國民族主義論述:在那一邊,我們曾經有很美好的家園⋯⋯。這會不會是小說家生涯中的一個破口,一個未曾成功壓抑的念想——他的中國民族主義其實並不如此「天然」,而是充滿著與他自身歷史處境的內在緊張?小說中父親的每次呼喚,總是同時引起兒子厭惡、懦弱、憤怒和莫可奈何的諸種情緒,這可不是什麼良好的認同經驗。
限於本文的篇幅和筆者的學力,本文只能暫時先以指出方向為念,淺論至此。但由上述簡單的討論,我們已能看出陳明成《陳映真現象》的研究當中,對詮釋陳映真的小說有如何巨大的潛力。如果我們真的在乎文學,而不只是想要塑造一個為己所用的「教主」的話,這樣的研究絕對應該得到重視。
(刊載於《秘密讀者》2016年1月號)
生養的暗面,罪咎的根源:重讀陳映真
2016/01/20 _文學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