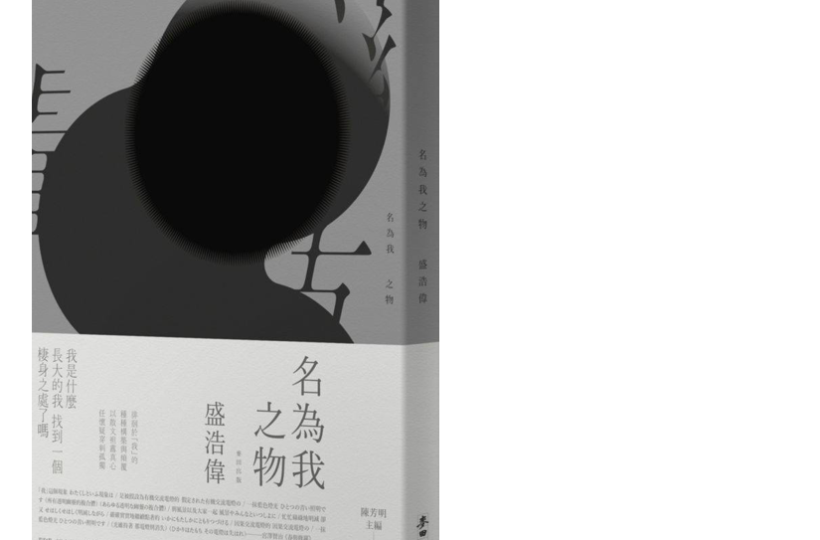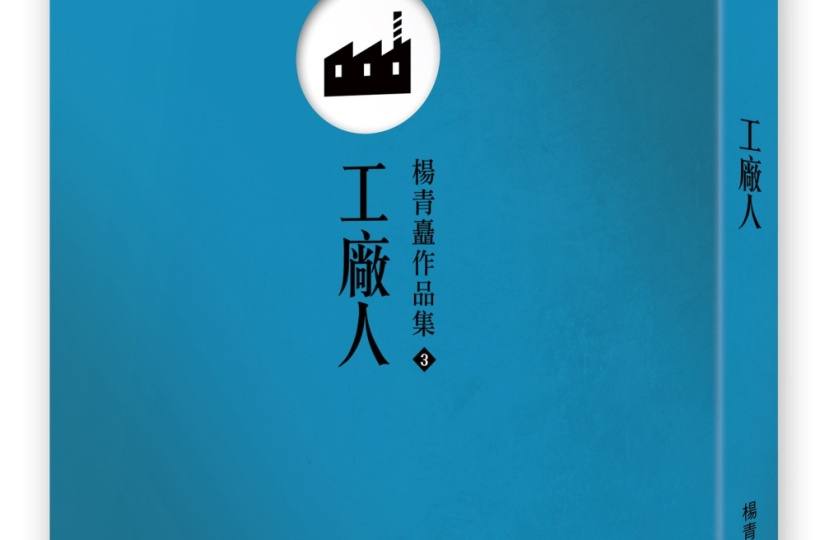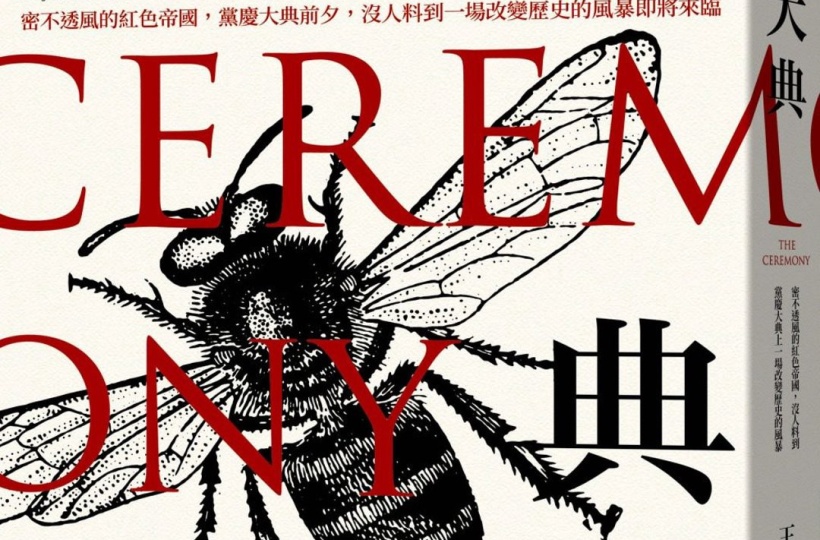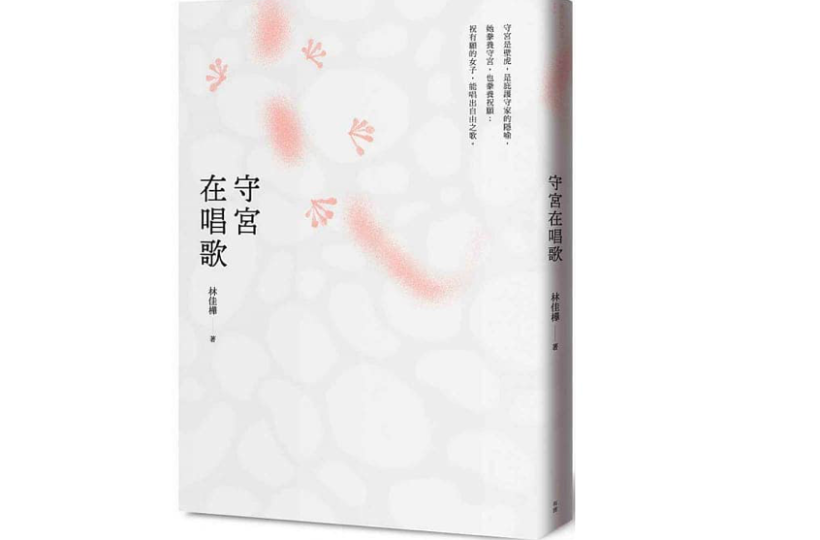然而即便風格不同,《向光植物》基本上仍然是通俗的純愛故事。小說從情感的啟蒙開始(「學姊」牽著「迷路」的「學妹」找到「教室」,無一不是情感啟蒙的隱喻),然後以基本上去性化的純愛模式推進,強調情感之中的曖昧氛圍、而非肉體的碰觸(唯一具體出現在小說中的性愛,是在中後段小旻的背叛),在歷經分離與死亡之後,最終「修成正果」,而且還是與初戀修成正果。支撐這個故事的,是非常清晰的浪漫愛模式。
但說它是「通俗的純愛故事」並無貶義,至少我沒有這個意思。絕大多數的文學作品都踩在固定的公式之上,差別只在作者是否自覺、是否能夠完好執行公式、或者是否能夠以公式為基礎開出新局。就此而言,《向光植物》的好處在於細節的處理非常細膩。它的抒情文字恰到好處,既保有一種清新的流暢感,又不會顯得淺陋;而在維持文字美感的同時,也能得當地控制力道,不至於讓「節制」變成「壓抑」、讓「修飾」變成「扭曲」。如果讀者讀來覺得此書一切順暢,那正是這篇小說的功力所在,因為作者已經事先修掉了大部份會破壞閱讀體驗的毛邊。
而另外一個值得稱道之處,在於小說的對白。《向光植物》的對白非常乾淨,沒有什麼多餘的說明文字,關鍵時刻也都能用簡單的字句勾出角色的情感。比如在小莫剛出場,敘事者和學姊陷入尷尬之後,有一段發生在游泳池邊的情節。敘事者穿著全套的運動服跳入泳池,把散落水中的球和呼啦圈撈回來,最終學姊也用呼拉圈拉敘事者上岸,並且說:
「我圈中了欸,這個我要。」學姊把我拉上岸邊,指著我說。
「妳才不要。」忙著把滴水的衣服擰得乾一點,我賭氣回答。(p.46)
這裡一方面承接了前段「夜市套圈圈」的意象,一方面用很輕巧的方式表達了學姊修補關係的努力。因此接著,敘事者就理所當然地軟化,問學姊:「可不可以重新開始?」(p.47)在這段鋪墊之後,作者立刻用細膩的慢筆描出了前期最重要的情感轉折:
她蹲下來,以一個非常靠近的姿態,拿下我瀏海邊緣、還有馬尾裡夾帶的葉子,她看著我的眼睛,看向某種類似靈魂深處的地方,接著緩緩地伸出右手。
「妳好,我姓游。」
「游小姐妳好,我不諳水性。」我握住她的手。(p.47-48)
這顯然是深諳如何調動情感的老手,才能寫出的段落。先以一個極近、極親密的特寫調慢節奏,同時醞釀了足夠的情感強度,然後在對白中帶入淺淺的幽默感(而這種幽默感是「學姊」這個角色一直以來的特質)。真正緊張等待答案的「我」也還了一個以姓氏為哏的俏皮話(而不是真的傻傻地寫出她有多緊張;簡斷的語句就夠緊張了),往上是銜接衝動跳入泳池的情節,往下是埋下了暗示,不諳水性的人愛上了「游」小姐,這段感情之後還有得拖磨了吧。(宋冬野的歌詞寫著:愛上一匹野馬 / 可我的家裡沒有草原)
類似的橋段,在全書當中俯拾皆是,小說家寫來顯然得心應手。比如在大學之後尷尬度破表的double date,小莫的每一句話幾乎都有弦外之音。(「啊,蛋糕垮掉了!」(p.137),垮掉的真的是蛋糕嗎?「還有好多東西想玩呢。」(p.138)指的是「還有修補敘事者和學姊關係的任務沒完成呢」吧,再考慮小莫夾在兩人當中、卻又努力調解兩人的資處境,這些清淺的對白底下其實都有沈澱的雜質。)小說的後段,敘事者打開很少用的臉書,收到小莫不知送出多久的交友邀情,也是類似的隱喻。
這類「輕隱喻」是《向光植物》最好看的地方,但大概也標定了這篇小說的極限。小說家所設定的隱喻都並不難讀出,能夠吸引讀者停留三秒、會心一笑,然而最多就是三秒了。這些輕靈的場景彌補了略嫌單薄的故事線,但真要往下探究,其實也並沒有太多的東西能挖掘出來。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小說都是寫來讓讀者東敲西打、追摹形式或挖掘出思想上的意義的,這本小說看起來完全沒有想要往這些地方發展的意思,它就是提出一個普通的架構,然後在裡面灌注了所有對青春的感嘆、緬懷和竊竊私語,而且漂亮地完成了這個架構。對讀者來說,它所能達到的滌淨功能是與《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或《我的少女時代》類似的,而且恰恰正是沒辦法被這兩部電影滌淨的文青們,需要的是《向光植物》這樣更高段(但又不過分高段)的文本,來回想自己的十六歲。人們的品味或者不同,但情感的需要卻是類似的。
除了「輕隱喻」的重複,《向光植物》的大部份章節,開篇的方式也是非常雷同的。或許是因為這篇小說係出自連載,作者並非在一個連續的狀況之下寫完,因此每次都有一定的「暖機」時間。小說家似乎很習慣以一到兩段的說理——當然並非學校作文那種等級的說理——來帶出下一段情節,而不是讓每一章節形成緊湊的情節因果鍊。比如第7節:「妳是什麼時候發現自己喜歡上女生的呢」(p.27);第11節:「有一種門只進不出」(p.54);第27節:「懷疑愛,懷疑愛人的能力」(p.129);第32節:「遊戲規則是這樣的」(p.150)⋯⋯。這問題不大,但過多的重複,對於創作者來說或許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警訊。
而在這篇文章的最後,我覺得還可以注意的是另外一組對照,即曹麗娟〈童女之舞〉和李屏瑤《向光植物》的對照。兩篇女同志小說相隔數十年,其所描述的社會氛圍已有部份變動(當然不能保證是完全不同了;那太樂觀了)。這或者也可以部分解釋兩作的氛圍為什麼會差這麼多。曹麗娟〈童女之舞〉一樣充滿了機巧的對白,但相較之下是更沈重、更無喘息空間的,她們的全付心力都用在避免碰觸對方的傷口之上了;而李屏瑤《向光植物》少了一點社會壓力,多了一些社會支持系統(社團、宿舍、「家」的空間、相對友善的家人),因此角色們在「談感情」的時候真的就是在談感情。〈童女之舞〉的爆炸點是:「我的天!童素心你比我還慘。」《向光植物》則是一句有淡然、有哀傷、但也不無堅強的:「我跟對方說,女同志現在不自殺了。」(p.190)
我們不應該率意將這句話解讀為同志運動取得成果的「社會事實」,而應該理解到,這句話裡有部分的真實、但也有部分是祈願。同理,《向光植物》總是再三重複「受傷>療癒」的情節,並且透過敘事者的陳述和實踐,不斷重提「所有的傷口終會痊癒」的說法,不見得是全然寫實的。那是小說家一再合十祝禱的手勢,「你要好好的」。
(刊載於《秘密讀者》2016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