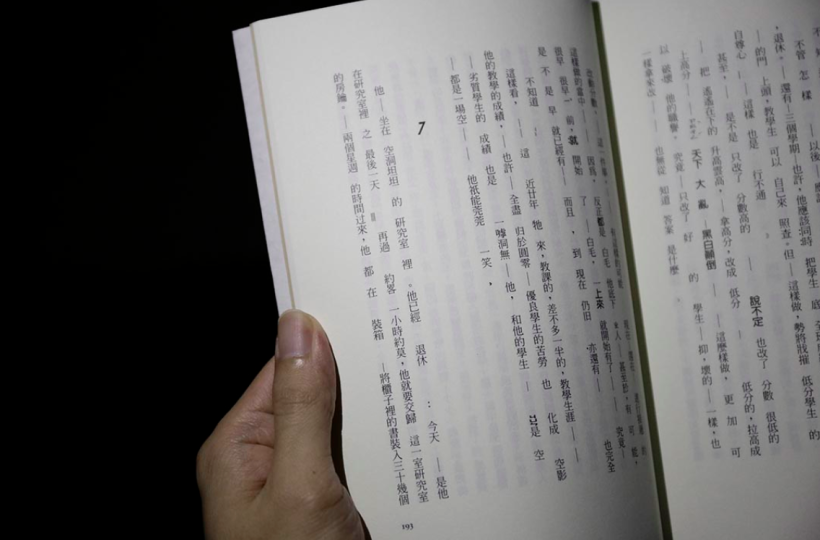另外一個論者時常提及的點,是小說的「清淡」風格,這或許更有多挖掘的餘地。關於這一點,李金蓮顯然是十分自覺的,這在本書的新書發表會上,已有作家本人的證言可稽。但值得追問的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一、在技術層次上,它是如何「清淡」的?寫作的技藝與類似風格的作家相比,有何異同高下?二、對小說家而言,為何要淡?她想要回應的問題、關懷的核心是什麼?
在第一個層次上,我們或許可以把它放置在台灣一系列同樣「清淡」的小說家中來比較。筆者認為,「清淡」這個形容詞應是來自「三個減法」:情節上減低戲劇性、敘事上減低形式感、文字上減去不必要的修飾。依此定義,其中一條線索也許可以拉到日治時期張文環的自然主義,然後沿著戰後的鄭清文以下,乃至於1990年代的袁哲生。而在這條線索發展的中途,也或許匯入了張大春在談論中國傳統筆記小說時,所提倡的「沒事兒」的小說,那依然也是「減法」的思路,強調無形的「意趣」而非具有「小說感」的文字營為。當然,這樣的脈絡,還很難說是形成了某種譜系,因為畢竟上述作家背後的美學與政治預設都有很大的差異,但至少可以想像成諸多細小支流,每隔幾年就出現新作,匯入同一條清淺的大河裡。
由此觀之,李金蓮的「清淡」,主要來自後兩個減法(文字、形式)。她的文字不但少修飾,而且也盡可能不突出任何明顯的聲腔;其次,《浮水錄》的形式安排放在當代小說中比較,幾乎就是素顏面世。除了第一節有「楔子」的功能,略微調動了時空以外,整篇小說基本上就是沿著角色的生活順敘過去,就像是從每個角色的日記本上面剪裁幾個段落編織而成的。但相對來說,第一個減法(戲劇性)就不是李金蓮特別著意的部分了,這並不是一篇「沒事兒」的小說。全書分作上下兩篇,上篇「母與女」主要的戲劇強度來自茉莉與韓敬學的感情;下篇「父與女」主要的戲劇強度來自秀代和唐進榮的感情。
為什麼減了三分之二,留下最後的三分之一?
具體的思路,當然可能要對作家進行進一步的訪談、或者觀察更多的作品後再下定論。不過這裡筆者希望能提出一個猜想:這或者是對於1990年代以來,文學獎所主導的純文學習尚的疏遠——如果不是批判的話。如果以剛剛的「三個減法」框架來看,在文學獎裡日益爛熟的作品套路,正是「情節薄弱,但文字與形式的高度操作」。因此,《浮水錄》剛好就與之成為一組對照。考慮到李金蓮在「開卷」長年任職的背景,對於這個時期純文學小說的主要風格應該是熟悉的,因此這或許可以理解為李金蓮援引一種老派的寫法,辯證地回應當前的主流風格。而作為對照的是,雖然如伊格言、甘耀明、吳明益等後起之秀也在近年來與「情節薄弱」這一點「對作」,但他們在策略上多是援引類型文學、地方文史或田野調查的資源,對話的對象或許相同,解決的路徑卻是不一樣的。
回到小說本身,《浮水錄》的表現並不惡,但卻也沒有太突出之處。比起袁哲生、童偉格能從生活的碎片中精煉出礦物結晶,李金蓮的感性還是顯得較為單純的。小說的上下兩篇中,最精彩的段落都是在靠近結尾的地方:茉莉與韓敬學攤牌、秀代前往尋找唐進榮,而筆者認為前者又比後者表現更佳,貫穿在這兩個場景內的韓敬學,更是全書最豐厚的角色。韓敬學與茉莉之間萌生情愫的第一個段落就寫得很細緻,在第六節末尾,韓敬學抱著秀代和秀瑾玩「坐飛機」的遊戲,輪流拋高兩人。先是秀瑾被拋起時:
然後是秀代:韓敬學把秀瑾蹬得高高的,像飛上了天際,秀瑾的臉映照在他前方,右邊缺了一顆牙的牙縫,竟露出了淡淡的一抹微笑,韓敬學下了一跳,那是茉莉。(p.89)
這兩個段落,放在小說行文的脈絡中,非常輕巧地把韓敬學心內的慾望具現化了,並且也同時挑動了茉莉,因此開啟了後續兩人所有的掙扎。這些讀來頗有味道的段落,是使《浮水錄》免於成為流水帳的關鍵。因為它所採取的形式雖然能帶來強烈的生活感,但作為小說,生活的雜亂本質與敘事的集中要求是互斥的,沒有足夠的情感或動機去撐持的段落,很容易讓讀者感到多餘、無趣。《浮水錄》在情節上雖有戲劇性但不夠強烈,本身是沒有足夠的內在動力的,如無這些段落的「續命」,恐怕難以為繼。突然,秀代皺起眉頭,一臉認真,對著韓敬學說:「韓伯伯,你做我們的爸爸,好不好?」(p.89)
因此,作家接下來的挑戰,或許是得面對一個更尖銳的問題:《浮水錄》的「清淡」,是有自覺的手藝,還是「不得不淡」的手段匱乏?如是前者,我們期待看到的是作家在之後的作品中,展現出更強的「內在結構」,讓讀者看見真正的「靜水流深」,處理更深邃的人性問題。能否讓問題不要停留在「因為她終究守住了」(p.238)這條線為止,多談一些生活中左支右絀、守禦不住之事?這或許是我們之後繼續觀察作家新作時,可以抱持的一點期待。
(刊載於《秘密讀者》2016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