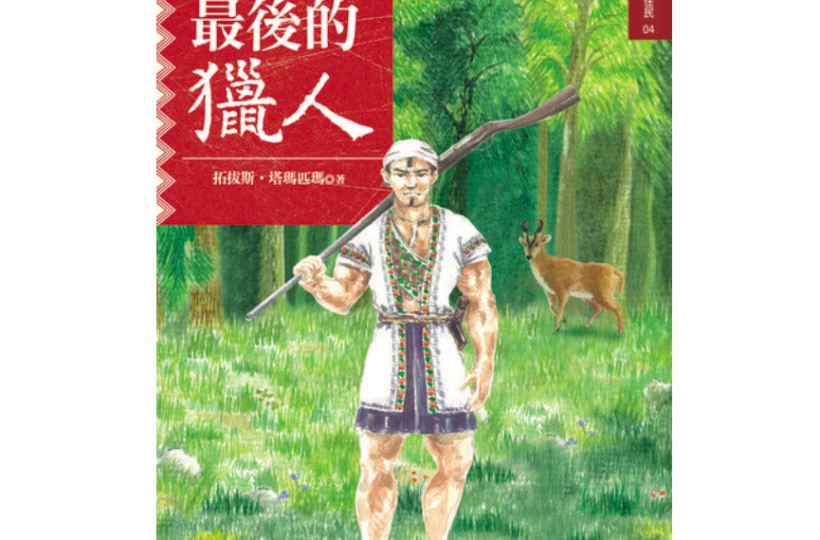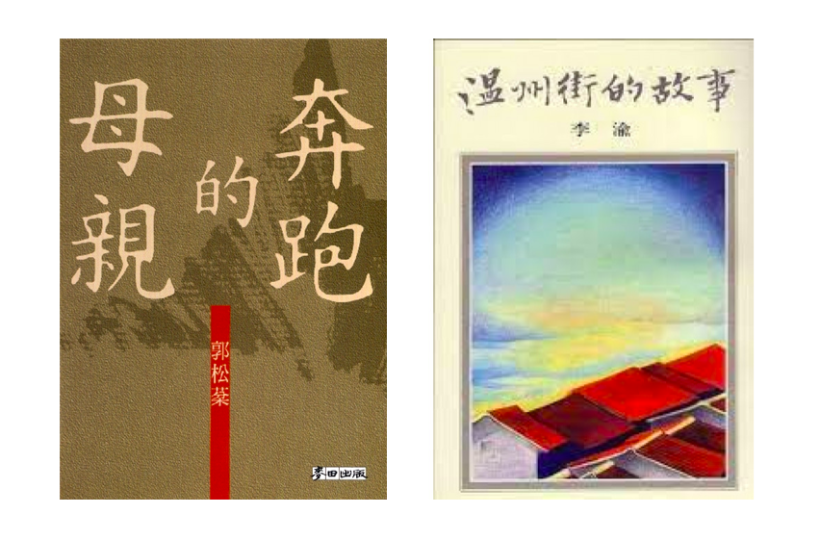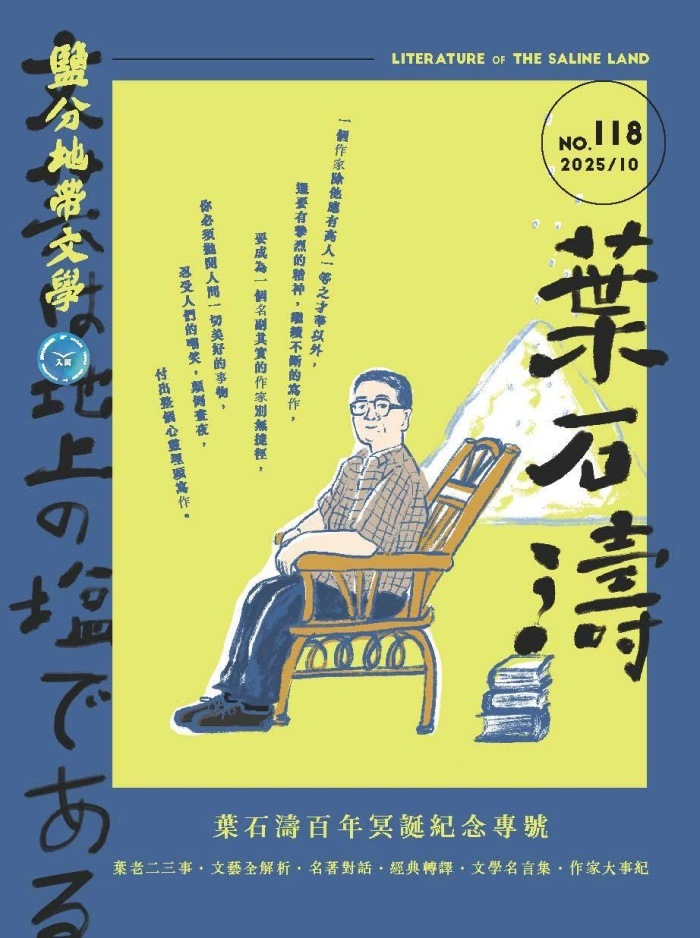在《斯卡羅》上映後,有一種稱讚的說法,是「它讓我們看到了原住民的故事」。這是眾多「稱讚」裡,最糟糕的一種。
事實上,原住民的故事早就在那裡了,並不需要等待一群漢人的「發現」。
剛好前幾天,我也在「與點堂」的課程裡談到了1980年到2000年之間的原住民文學,於是順手把一些書單和「看點」整理如下。如果你在看過了《斯卡羅》之後,有被「推廣」到,想要進一步了解原住民小說,我非常建議你可以直接去讀原住民作家自己寫的作品。這不但有實質的支持意味,而且很多細節和精神,真的跟他族人士的作品比起來,是天差地別的。
當然,詳細的文本分析就留給課堂學生了,這篇文章只是很簡略的概述。
・
台灣的「原住民小說」,大致可以追溯到1971年出版的,谷灣・打鹿勒的《域外夢痕》。這是第一本「原住民作家、以漢語書寫原住民經驗」的小說。這本書絕版多年,現在非常難找了。谷灣・打鹿勒是排灣族出身的警察,他在花蓮工作時,剛好認識一位作家盧克彰,於是在盧克彰的鼓勵下,以排灣族部落經驗為主題寫作投稿。
這本《域外夢痕》裡的小說,陸陸續續發表在1960年代,在當時不算特別受到矚目。不過,谷灣・打鹿勒特殊的經驗與題材,卻引起了當時本省籍作家領袖鍾肇政的注意。鍾肇政跟谷灣・打鹿勒通信,鼓勵他繼續寫作。然而,這份溫暖終究敵不過現實,鍾肇政當時能夠動用的文壇資源也很有限——他當時手上,只有一個發不出稿費的《台灣文藝》版面可以運用——谷灣・打鹿勒最終還是慢慢淡出文壇了。而這開天闢地的第一本原住民小說,也就默默沉寂下去了。
不過,這份遺憾一直留在鍾肇政心裡。鍾肇政雖然是漢人,但卻對原住民的歷史與文化很感興趣,發願要寫關於原住民的歷史小說。1979年,他先以「霧社事件」為主題,出版了《馬赫坡風雲》;到了1980年代,他更陸續發表了《川中島》與《戰火》兩部描寫「霧社事件以後,族人被遷移、被徵召去打二次世界大戰」的長篇小說。從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寫「霧社事件」好像沒什麼創意——歷史課本都有講了嘛!但別忘了,那是戒嚴時代,當時的歷史課本連台灣史都沒有,更不要說原住民了,整個社會根本沒有幾個人知道「霧社事件」。鍾肇政在出版了《川中島》與《戰火》之後,認識了一批在跑原住民運動的大學生,其中就有住在「馬赫坡」的後裔,連他們都不知道日治時期曾經有過這樣的故事。
平心而論,鍾肇政這系列的作品並不算是他的代表作(當然是要比《傀儡花》好非常多,畢竟鍾肇政是真的會寫小說的人,還是很值得一讀)。而以漢人的觀點來寫,更是在細節上有難以周全之處。比如鍾肇政曾在某篇小說寫原住民獵人帶水壺上山打獵,作家拓拔斯・塔瑪匹瑪就半開玩笑地評說:「我們在山裡頭長大,怎麼可能不知道哪裡有水,即使帶水壺,裡頭也是裝米酒或是小米酒。」
這一點,鍾肇政非常有感,他始終覺得自己寫起來有「隔牆觀望」的感覺。因此,他非常期待能有原住民作家出來寫自己的故事。
・
就在這種期待的氛圍下,1980年代的拓拔斯・塔瑪匹瑪躍上了文壇。他從1981年發表第一篇小說〈拓拔斯・塔瑪匹瑪〉後,陸續寫了一系列作品,終於在1987年出版了短篇小說集《最後的獵人》。
《最後的獵人》不是第一本原住民作家所寫的漢語小說集,卻是開啟我們現在所知的原住民小說浪潮的第一波,影響力巨大。在《最後的獵人》裡,我們幾乎可以看到往後原住民小說的好幾種重要類型。比如〈拓拔斯・塔瑪匹瑪〉,描寫的是年老的布農族人無法理解平地的法律,他們依照自己的習俗做事,卻被控告盜罰國有林,遭到法律懲罰。而年輕的布農族人在都市裡讀過書,卻陷入兩難:他一方面同情老人的遭遇,一方面又希望老人們可以放下成見,試著理解「部落以外的智慧」。這種「讀了書的原住民青年,卡在現代文明與部落傳統之間」的兩難,將成為往後原住民小說一再出現的主題。
除此之外,〈最後的獵人〉也是頗受文壇矚目的一篇。這篇小說同樣觸及幾個重要議題:布農族人到底要用傳統的農耕、狩獵的方式生活,還是要下山出賣勞力,去當資本主義底層的螺絲釘?當獵人堅持自己驕傲的傳統時,他的家人又要如何面對較差的生活條件?這篇小說鉅細靡遺地描寫了獵人上山打獵的細節,文字又比〈拓拔斯・塔瑪匹瑪〉更加絢爛優美。主角比雅日在山中時而焦慮,時而自卑,時而寂寞,時而又感覺到充滿力量與光榮,心理描寫非常動人。而到了故事結尾,獵人雖然成功狩獵到山羌,卻要面臨平地警察的威脅與索賄,最終竟然像是海明威《老人與海》那樣落入了虛無的境地。
而我個人最驚豔的,是〈夕陽蟬〉和〈侏儒族〉兩篇。〈夕陽蟬〉寫久居城市的布農老人,終於受不了平地的生活,請調回到自己的部落。乍看之下,我們會以為這也是另一篇描寫文化鄉愁的作品,但仔細一看,這篇小說竟是科幻小說!以科幻架構處理原住民題材,充分顯示拓拔斯・塔瑪匹瑪的創意。
而〈侏儒族〉更是非常巧妙的諷刺小說。布農青年帶著自己的外祖父,到城市裡看美國馬戲團表演。不料表演到一半,外祖父指著舞台上的黑人侏儒大吼大叫,害他們被警衛趕出去。在回家路上,外祖父才說明自己激動的原因:在古老的布農傳說裡,族人住在山谷,而山頂上住著更加聰慧的「侏儒族」。他們一開始約好互不侵犯,侏儒族甚至還會教布農族人農耕和打獵的技術。然而,當族人人口越來越多時,長老和勇士決定侵犯侏儒族的領地,進攻他們的部落。幾經戰鬥之後,侏儒族乘船遠颺,從此消失在這塊土地上。而布農人這時才感到後悔與抱歉,希望有朝一日能遇到這些「真正的山地人」,向他們道歉。外祖父之所以激動,就是因為馬戲團裡的黑人侏儒,長得和傳說中的侏儒族一模一樣,他很想要立刻去道歉⋯⋯
這篇小說指桑罵槐之意非常明顯。布農族侵犯侏儒族的故事,幾乎就是漢人侵犯原住民的翻版。差別是,外祖父看到一點幻影就急著想道歉,而漢人呢?
・
說到這裡,我想先岔題出去,講一個閱讀原住民文學時,必須放在心上的觀念。
有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最後的獵人》一系列小說發表時,與本土派的作家關係非常密切。像鍾肇政一樣期待「原住民作家寫原住民故事」的作家還有很多,比如熱切提攜拓拔斯・塔瑪匹瑪的吳錦發。幾乎可以這麼說,第一批原住民小說之所以能漸漸在文壇有知名度,與本土派作家的大力支援很有關係。而這種關聯性,也留下了一個尷尬難解的問題。
1980年代中後期的本土派已非吳下阿蒙。在本土化浪潮逐漸升高的情況下,他們能夠掌握的文壇資源越來越多,足以培養他們有興趣的新秀了。而本土派為什麼對原住民小說特別有興趣?從吳錦發第一次讀到拓拔斯・塔瑪匹瑪的反應可以看出來,吳錦發說:「這才是真正的台灣文學吧!」
這句話聽起來是一百分的讚嘆,但仔細一想,卻有點危險。為什麼原住民小說是「真正的台灣文學」呢?這裡面,其實隱藏了本土派的一種文化焦慮——我們在政治上,希望與中國切割,訴求獨立;但在文化上,我們能否創造足夠的區隔,闡明「台灣文化」的獨特性?畢竟,台灣的漢族與中國的漢族,縱有種種歷史帶來的文化差異,相像的部分還是太多了。
這時候,原住民文化就變成最有力的「鐵證」——這些文化,這些文學,怎麼看都是台灣獨有的吧?至少,不可能跟中國混淆了吧?也因此,對本土派來說,熱切擁抱原住民小說,其背後的心理動機是「我們獲得了一支足以區隔中國文學的援軍」,所謂「真正的台灣文學」,是在這樣的心理下成立的。
聽起來很美好。但有個問題:原住民有答應讓你挪用他們的文化,拿來當作切割中國的次元刀嗎?
甚至更尖銳一點問,如果漢人只在需要切割中國的時候,才把原住民推到前線,而在平常的政治安排、社會制度、文化意識裡,卻沒有任何實質改善原住民處境的行為,這樣的「挪用」真的合理嗎?
人家有答應要當你的援軍嗎?
當然,吳錦發在喊出「這才是真正的台灣文學」時,很可能沒有惡意。但是,當漢人輕率地把原住民文化當作「我們共同的文化」時,往往沒有意識到,那些是人家的東西,我們漢人充其量只是來借用的。如果人家不借,那是他們的自由;如果人家願意借,那我們有義務好好珍惜,用完了還得物歸原主,不能隨便認為「這就是我們全體台灣人的」。誰跟你全體台灣人?原住民被歧視、文化被破壞、生存領域被侵犯的時候,我們漢人可沒有在部落裡同甘共苦。
——如果你明白這個觀念,你就能明白為何當地人對《斯卡羅》有這麼多不滿了。作家或劇組,恐怕完全沒有「我是來借東西的」之自覺。
・
岔題結束,我想再接著推薦1990年代的兩本原住民小說。第一本,是游霸士.撓給赫的《天狗部落之歌》。
對於我們這些不懂原住民文化的漢人麻瓜來說,《天狗部落之歌》或許是最能「無痛讀懂」的一本原住民小說。游霸士.撓給赫是泰雅族人,但他當了幾十年的國文老師,漢化程度很深,因此在文字風格上,是漢人最容易習慣的——當然,代價就是他的文字風格就不像其他原住民作家那麼強烈。
除此之外,《天狗部落之歌》也非常「通俗」,他的小說故事性強烈,在敘述原住民文化的境遇時,雖然也有失落的哀感,但也時時閃現令人哭笑不得的幽默感。比如〈媽媽臉上的圖騰〉,先從一名族人不願意跟臉上紋面的母親一起行走講起,看似要啟動一個沉痛的故事,不料敘事者話鋒一轉,開始轉述自己的母親當年紋面的點滴。游霸士.撓給赫用了非常長的篇幅,講述少女如何害怕紋面,把陪同的家人整得七葷八素;接著,又細描了紋面之後,整張臉感染腫脹的慘狀,感官十分鮮明濃烈。而當少女成為母親,和敘事者一起到台北逛街時,那張佈滿圖騰的臉反而成為她的驕傲,路上遇到的日本、非洲觀光客紛紛要求合照。
而就我個人來說,游霸士.撓給赫最厲害的地方,是對戰鬥的描寫,特別是描寫「出草」。〈出草〉、〈斷層山〉和〈丸田炮台進出〉都非常有意思。〈出草〉延續游霸士.撓給赫一貫的幽默感,從三個死者的聊天開場,原來這是一名泰雅族獵人和兩名日本警察的骸骨。日本警察質問獵人,為何要出草殺害我們一位溫和無辜的同伴?獵人於是娓娓道來,將不為人知的、有點滑稽的戰鬥經過敘述出來。最終,獵人因為出草而被逮補,卻拖著兩名押送他的日本警察跳下山崖,於是有了這場「一笑泯恩仇」的死者群聊。〈斷層山〉則是一部適合直接拍成動作片的小說。獵人洗雅特和日本的二十名突擊隊員對峙,故事開場,洗雅特全家都被殺盡,只剩下他一人,化身為復仇之鬼。於是他在山中利用各種技能,埋伏、分割、暗殺,殺得整支部隊左支右絀,幾乎是泰雅版的藍波。最終,這支突擊隊拋下了半數隊員的屍體,倉皇撤離,洗雅特坐在亂石堆中,望著逃回日本人地盤的敵人,放聲大哭⋯⋯
而〈丸田炮台進出〉,更可以說是游霸士.撓給赫在情節上最具巧思的短篇。日本人在山頂上建立砲台,轟擊主角所在的泰雅部落。整篇小說就描述部落如何突破通電鐵絲網,撤退到山上的預備陣地,但因為沒有逃出砲台的射程範圍,所以主角等六名族人決定突襲砲台的故事。這篇小說的戰術規劃極為精巧,絕非《斯卡羅》裡面亂砍亂射一氣的寫法可以比擬。比如當族人的子彈不夠時,如何用「草船借箭」的方式,從日本人身上取得彈藥補給?在進攻前,獵人又是如何掩蔽自身、如何安排射界?(然後游霸士.撓給赫又在此展現幽默感:因為族人隱蔽得太好,日本士兵竟然在族人頭上尿尿,還渾然不覺)更別說戰鬥的過程、結果乃至於撤退路上的氣氛,都非常精彩。這麼一篇驚喜層出不窮的作品,我不想講太多,就請有興趣的人自己去找來讀吧。
・
最後一本我想推薦的作品,是霍斯陸曼・伐伐的《那年我們祭拜祖靈》,特別是〈布妮依的婚禮〉和〈失手的戰士〉兩篇。
〈布妮依的婚禮〉講述部落裡一位能幹的女孩。她天生聰穎,能夠代替族人跟平地人打交道,爭取應有的權利。布妮依是跟前面我們講過的拓拔斯・塔瑪匹瑪不太一樣的類型。拓拔斯・塔瑪匹瑪自己適應了現代文明,卻無法改變族人的生活;布妮依則天生就是「有社工關懷的領袖」,不但自己有一流手腕,還能洞察族人的需要,巧妙解決問題。光是這種現代與傳統融合的形象,就足夠令人驚艷,但更驚人的是:如果你夠細心,還可以在這篇文章裡讀到白色恐怖的蹤跡。由於布妮依太過能幹,被平地人指控她通匪,天真而困惑的族人詢問平地官員:你們所說的,海那一邊的邪惡的敵人長什麼樣子呢?如果我們知道敵人的長相,一定幫你們消滅他。這時候,平地的官員尷尬了,想半天,只答得出:「長得跟我一樣。」這句對白真的絕妙,一句話就表達了原住民的立場:你們海峽兩邊的漢人自己殺來殺去,為什麼要扯上我們?
而〈失手的戰士〉,則是我最喜歡的一篇原住民小說,沒有之一。事實上,也不必限定在原住民小說的領域,就算你把〈失手的戰士〉跟台灣文學史上所有作品並列,它也毫無疑問要入選國家隊——下次如果再有什麼文創國家隊計畫,真的不要再去選不會寫小說的漢人寫的原住民小說了,霍斯陸曼・伐伐1996年就已經寫了這麼強大的作品。當然,我並不是原住民文學的專家,所以也許還有更好的作品也不一定,但這篇對我來說已經是超一流水準。
〈失手的戰士〉從主角督布斯小時候寫起。因為督布斯的疏忽,害自己的妹妹塔妮芙陷入火場,小腿肌肉全部燒焦,一輩子不良於行。然而,部落的人並沒有怪罪督布斯,反而認為這是惡靈的詛咒,褫奪了督布斯的父親在族中的社會地位。督布斯的第一個困惑開始浮現:明明錯的是我,為什麼一切會歸諸於惡靈?為什麼是父親承擔連帶責任?父親同樣困惑,但因為深愛女兒,所以他拒絕了長老殺害女兒、曝屍荒野的建議(諷刺的是,長老之所以如此建議,是因為看到漢人這麼做),一夕之間從族裡的英雄變成邊緣人。
多年後,督布斯成年了,部落與日本人發生衝突,長老決定出草。父親立刻自告奮勇,想靠出草來洗刷詛咒之名。結果在出草前的會議上,長老認為父親的夢境不吉利,拒絕讓父親參與。父親只好哀求長老,至少讓督布斯參與。於是有了這樣的段落:
長老問坐在圓圈外圍的督布斯說:
「年青的後輩(Wvad)!把你所夢到的說出來?」
督布斯看著爸爸期盼的眼神,又想到妹妹被詛咒的小腳,他很想編出和前面族人一樣的夢,但是欺騙(Silaluwn)是觸犯先祖所傳下來的禁忌,本身和家人將會遭到一生一世無法解除的詛咒,他吸了一口氣,很誠實的說:
「祖靈有在我的夢中暗示我,但是我醒來的時候忘記了。」
督布斯立即把頭低下來,準備接受被拒絕的事實。
「如果你有男人的生殖器(Hadas),明天早上到這裡來。」長老用低沈的聲音對年輕人說。
督布斯不相信的張著嘴巴,他萬萬想不到「遺忘」也可以得到機會;「遺忘」不是族人所認為的愚笨、白痴(Mataula)的現象嗎?
這段文字非常值得玩味。首先,督布斯陷入了「要不要說謊」的兩難。如果誠實說出無夢,那就不能出草,家族的詛咒必將延續;但如果說謊,又觸犯了新的禁忌,會遭到永遠無法解除的詛咒。這段兩難非常精彩,也深化了「出草」這件事的意義——這可不是外人眼中,隨意殺人斬首的野蠻行動,而是有著賭上家族聲譽的深沉動機。
其次,督布斯選擇誠實,正證明了他作為獵人的良好品行;意外的是,長老竟然答應讓他出草。這也顯示了「傳統」並非僵化凝固,而有人性化的一面——長老豈不知道,督布斯一家人等待多年,不能放掉這個機會?長老又豈會不知道,昨夜無夢的督布斯是面對了怎樣的兩難,才決定誠實?此中的細膩與深度,毫無疑問是一流文學作品的構思。
而背負這樣重量出草的督布斯,最終卻「失手」了。他不是沒有機會斬首,而是他遭遇了不忍斬首的情境。為何如此?督布斯又要如何掩飾自己的失敗?而他放過的人,最終又會如何回到他的命運裡?關於這篇小說,我已說得太多,就此打住吧。有些體驗,就是要在一無所知的時候翻開書頁,才能有最大的衝擊力。我只能說,如果你想像中的原住民小說,都是描寫「傳統文化」,並且故事裡的每個人都全心全意相信、歌頌傳統文化,那你一定要讀讀看霍斯陸曼・伐伐〈失手的戰士〉,他會讓你看到部落戰士粗獷勇悍的表面下,隱藏了多少細膩而無法言說的心思,他們又是如何擺盪在傳統文化與個體經驗之間,持續思索,調和,乃至於陷入無奈⋯⋯
・
以上三位作家,主要是1980-2000年之間,幾本我自己特別喜歡的原住民小說。最後要強調的是,我的推薦純粹是從我自己的立場出發,我並不了解原住民文化,也不是研究原住民文學的專家,所以我的推薦未必有絕對的公信力。但這些小說都以其非常堅強的質地撼動了我,這是無庸置疑的。我不敢輕易說出「這是真正的台灣文學」這樣的話,我只能說,在我閱讀到這些作品時,我一方面覺得萬分歉疚,一方面卻也覺得榮幸——我們竟能與這樣的靈魂同住在一座島嶼上。
如果我們的理解只停在《斯卡羅》,就太可惜了。
---
以下為書籍連結:
拓拔斯・塔瑪匹瑪《最後的獵人》
游霸士.撓給赫《天狗部落之歌》(已絕版)
霍斯陸曼・伐伐《那年我們祭拜祖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