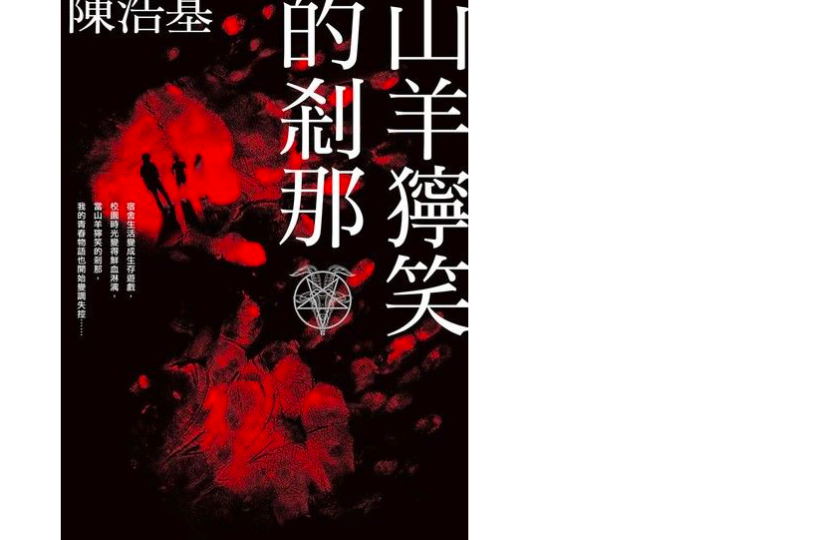青山千鶴子・楊双子的《臺灣漫遊錄》之前引起了一些爭論。有人認為它「託名虛構」,並且認為它的「行銷手段」欺騙了讀者。老實說,我從一開始就覺得莫名其妙:難道真的有人覺得,把一本「小說」講成一本非虛構性質的「史料」,會增加行銷賣點嗎?如果真要行銷效果,已經以《花開時節》而大受矚目的「楊双子」之名,難道會比一個從來沒有人聽過的日本名字「青山千鶴子」難賣?
因此,我沒興趣去談什麼「行銷手段背後的倫理」。我覺得這本書有趣之處,就在於它層層疊疊的「託名」;如果沒有辦法理解此中妙處、此中深沉的情意,那無異是買櫝還珠了。
.
「如果」真有青山千鶴子這位作家,真的寫了《臺灣漫遊錄》這部小說,那它會是一本很不錯的小說,也具有豐富的研究價值。它的主軸扣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難以消解的權力關係——那是一種即使善良、溫柔甚至是愛情都無法跨越的鴻溝。故事中的日本人越善待台灣人,就越顯得日本人與台灣人注定有著不同的人生。《臺灣漫遊錄》全程吃喝旅行,情意柔美溫婉,然而作者從未放鬆對權力關係的注意,就算在最甜美、最朦朧的瞬間,殖民地的陰影都不曾稍淡。
然而,如果這本書僅只於此,那它的主題、思想,卻沒有超出日治時期、描寫台灣的日本作家太多。在前幾年出版的《華麗島的冒險》的諸篇章中,就有好幾篇以不同角度探討這個問題,比如日影丈吉〈消失的房子〉就反省了「日本人根本未曾真正理解台灣」這個問題。
.
唯有在理解了《臺灣漫遊錄》設下之「託名虛構」有何文學意義,才能抓到這本書最深美的地方。而要理解這套設計,首先要從「楊双子」這個筆名開始談起。
「楊双子」並不是一個人的筆名,而是一對姊妹的筆名。「双子」指的是姊姊楊若慈、妹妹楊若暉這兩個人。於是,當我們說「某本書是楊双子寫的」,它到底是楊若慈寫的,還是楊若暉寫的?或者說,這對姊妹到底負責了作品的哪些部分呢?
這個問題,你翻開《臺灣漫遊錄》折頁的作者簡介就會看到了:
雙胞胎姊妹楊若慈、楊若暉的共用筆名。姊姊楊若慈主力創作,妹妹楊若暉主力歷史考據與日文翻譯,共同創作台灣歷史百合小說。
在「楊双子」的筆名之下,分工是很清楚的。楊若慈負責寫小說,楊若暉負責考據與翻譯。要注意的是,雖然這段資訊毫無虛構成分,但從這裡開始,就已經是《臺灣漫遊錄》小說的一部分了,這是理解小說的關鍵線索。
.
所以,當我們問:「《花開時節》是誰寫的?」答案是「楊双子」,但更精確的答案是「楊若暉負責考據與翻譯、楊若慈執筆寫成」。
而當我們問:「《臺灣漫遊錄》是誰寫的?」這個答案就更複雜了:它是「楊双子」寫的——但這一次,「真實作者」只剩下楊若慈一人了,沒有楊若暉了。或者保守點說,楊若慈可能還是引用了部分楊若暉之前整理的資料;但楊若暉參與《臺灣漫遊錄》的程度,一定是低於《花開時節》的。
為什麼?因為楊若暉已於2015年去世了。
這才是《臺灣漫遊錄》的解讀鑰匙:這是姊姊楊若慈寫給妹妹楊若暉的悼亡之書。日本殖民時代的台灣,是她們共同關懷的主題,她們的文學夢想和學術志業;所以這本悼亡之書,才會以「一名日本作家的台灣遊記」為主題。
.
大部分的人,都注意到這本書最明顯的「託名虛構」:
1.楊若慈虛構了「青山千鶴子」這名作家,以及「青山千鶴子」的作品。
但事實上,更關鍵的是第二重「託名虛構」,這是有讀到書中內文的人才會發現的:
2.楊若慈虛構了「楊若暉翻譯了青山千鶴子的《臺灣漫遊錄》」這件事。
這本書的封面寫著「青山千鶴子.楊双子著」。再一次,我們要問,這裡的「楊双子」是誰?現實上來說,我們知道是楊若慈,但你如果去讀書中收錄的文章,包括一篇推薦序、四篇後記,很快就會發現,每當大家提到譯者時,都會非常精確地指出,這本書的譯者是「楊若暉」。全書最後一篇的〈新版譯者代跋 琥珀〉(這也是小說的一部分),更是以「楊若暉」的第一人稱寫成。該文的倒數第二段,「楊若暉」寫道:
特別需要感謝的是我的孿生姊妹・『双子』當中的若慈。本書譯稿雖然由我・『双子』當中的若暉執筆,實際上卻是我倆的共同作品。
這段令人迷惑的話,如何證明它是虛構的呢?很簡單,看這篇文章落筆的時間。在文章的最後一行,就註明了此文寫於「二O二O年春彼岸於永和住處」。
楊若暉逝世於2015年,是不可能寫下這篇文章的。因此,這是「楊若慈虛構的楊若暉,翻譯了楊若慈虛構的青山千鶴子之作品」。
.
這麼層層疊疊的虛構,有什麼意義嗎?
搭著小說內文看,就有了。
《臺灣漫遊錄》的故事線條很單純,描寫日本作家青山千鶴子受邀來台演講,趁此機會遊歷台灣一年。青山千鶴子結識了台灣通譯王千鶴,在精通語言、美食文化、風土民情的王千鶴帶領下,進行了一場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之旅。當然,楊双子致力於百合小說的創作,這兩人之間的牽絆日漸濃烈,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這裡有個好玩的線索,是兩人的身分。
青山千鶴子>>>小說家
王千鶴>>>翻譯
(而且隨著故事的進行,我們還發現王千鶴的志向是「小說翻譯家」。)
不覺得很眼熟嗎?根本就是「楊双子」的功能配置:
楊若慈>>>創作
楊若暉>>>翻譯
理解這一層之後,《臺灣漫遊錄》藉由青山千鶴子的視角,對王千鶴生發的種種情意,也就有了別樣的意義——很多時候,我會恍惚覺得,當青山千鶴子對王千鶴說心事的時候,似乎也正是楊若慈對著楊若暉說心事的時候。當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這樣粗暴地畫上等號,但這組結構本身就有某種內在的幽微聯繫,這大概是不能否認的。
舉例來說,在新日嵯峨子(咳咳)的推薦序中,提到小說末尾有一股「道歉」的情緒,這解讀我非常同意。但我想有點僭越地詮釋,這裡的「道歉」,或許不只是日本人青山千鶴子對台灣人王千鶴的道歉,而是否能讀作某種對亡者的歉然?亡者已逝,生者則帶著兩人共同的夢想,背負著同一個名字繼續寫下去。無論生者怎麼努力,或許多少都會有一種「如果你在就好了」、「我這樣做夠了嗎」的歉然之感吧。
在小說裡,最終分隔兩人的是歷史變動、人事變遷;在現實世界裡,最終分隔「双子」的是生死之岸。這也是為什麼,即便故事裡面有其他日本人與台灣人友愛相處的組合,即便其他組合都有可能和解,但青山千鶴子和王千鶴之間就是不可能跨越彼此的身分界線。《臺灣漫遊錄》的殖民鴻溝,不只是這本書的主題,更是這本書的隱喻——如果我們把「悼亡」當作本體的話,這麼大的一個殖民故事,其實只是外殼,真正的核心、真正要說的,是「双子」的故事。
附錄的〈麵線〉一文,作者藉著(虛構的)王千鶴之筆,不就明明白白寫了嗎?
來不及的餘生共酌,來日若有機緣天堂重逢,我再向青山小姐舉杯吧。
.
「翻譯」是跨越文化阻隔的活動,而如果我們之間的阻隔,是語言也沒辦法贖回的呢?
那就要靠「創作」了。
當楊双子中的楊若慈,創作了一部真正由她自己一人創作出來的小說《臺灣漫遊錄》時,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楊双子中的楊若暉,也織進層層虛構之網中。
妹妹怎麼能不在呢?双子必須姊妹都在,才成其双子啊。
所以,楊若慈不只是「創作」了一個日本女作家的台灣暴食之旅,她還「創作」了楊若暉「可能的存在」。如果真有那麼一本小說,那確實可能會由楊若暉來翻譯的吧?如果楊若慈真的寫了一部小說,也完全有可能由楊若暉翻譯成別的語言吧?
對亡者的思念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是可以把自己作為作者的位置也讓出去,也沒關係的程度。
作為小說創作者,我很難想像還有什麼比這更貴重的禮物了。
回到爭議的起點,《臺灣漫遊錄》非得這樣「託名虛構」嗎?
楊双子不可以純粹就寫一個「青山千鶴子」的虛構故事,然後作者欄只放上自己的名字嗎?
當然可以。只是這樣的話,意義就完全不同了。
讓我再次僭越地詮釋吧:《花開時節》,是姊妹兩人共同構思、合作完成的作品。而現在,《花開時節》已經完成了,也已經以其高度的水準,證明了兩人的文學夢想有其價值。而接下來,只剩下姊姊楊若慈的楊双子,下一步該寫什麼、該往哪裡寫呢?《臺灣漫遊錄》或可讀作楊双子的文學宣言——「我不會拋下你的,我們一起往前走吧。」
〈新版譯者代跋 琥珀〉有段話,我很喜歡,也彷彿冥冥預言了此書出版之後的「真 / 假」爭議:
至於為什麼青山千鶴子不是集結當年的臺灣遊記,而是以小說形式重寫?再者,遊記 / 歷史是否更加『真實』?而小說 / 文學是否相對『虛構』?我無意以論文回答這個問題,姑且容許我抒情地這樣說吧:小說是一塊琥珀,凝結真實的往事與虛構的理想。它耐人尋味,美麗無匹。
所有答案,已經在這本書裡面寫好了啊。
——
青山千鶴子.楊双子 《臺灣漫遊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