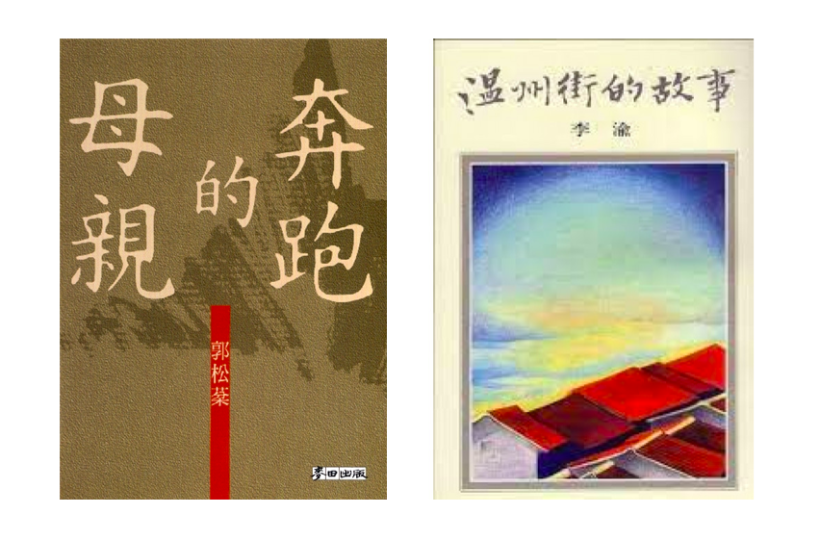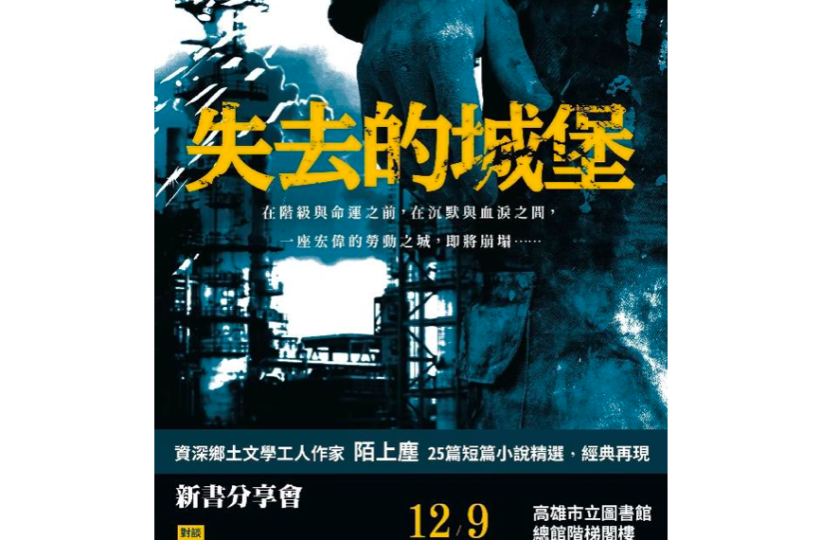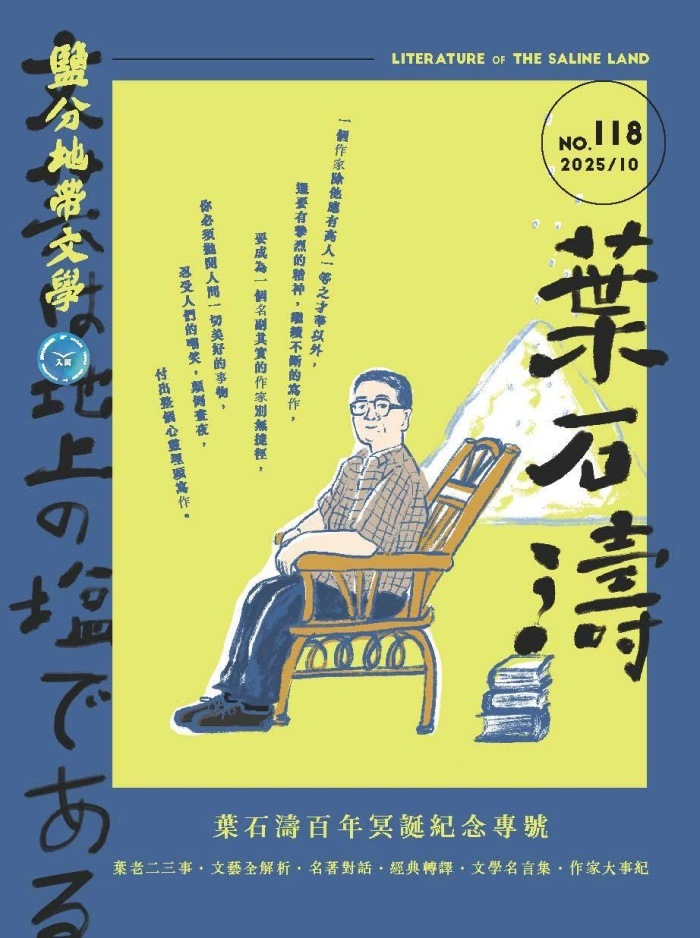2021年11月2日,出現了一幅文化界未必會注意到,但對台灣本土語言創作來說有重大意義的「奇景」。台灣最熱門的遊戲實況主魯蛋,在網路上直播他遊玩《廖添丁:稀代兇賊の最期》這款遊戲的過程,長達七個小時。這款《廖添丁:稀代兇賊の最期》早在十七年前,就以《神影無蹤廖添丁》為名,推出過Flash遊戲的版本,並且轟動一時。此次推出的新版,則是大幅度優化、劇情也更加趨近於完整的作品,自然引起許多新舊玩家的關注。
也因此,魯蛋在遊戲上市後立刻就開了直播。一進到遊戲內,魯蛋就發現可選擇的語言介面包含「台文」,很快按了下去。接下來,魯蛋和他的數千名觀眾便進入了一趟奇幻旅程——《廖添丁:稀代兇賊の最期》的台語旁白由吳國禎主講,他是以講述廖添丁傳奇聞名的講古名家吳樂天的弟子;遊戲裡所有對白、說明、旁述,凡是有文字的地方,也通通都以台語正字撰寫。在年輕世代當中,魯蛋的台語是非常不錯的,但他並未接受過正統的台文閱讀訓練。因此,他會試著用自己的理解,去識讀遊戲裡出現的台文詞彙,比如「鬥相共」或「跤數」;而在他無法辨識出來的時候,八千名觀眾所組成的熱鬧留言板裡,也會開始出意見,甚至一起查教育部閩南語字典。
在直播的中段,魯蛋感嘆地說了一句:「我們一瞬間回到20年前耶,一邊對日文辭典一邊玩遊戲。……現在不一樣,現在是一邊對台語辭典、一邊對遊戲的發音到底怎麼唸。」
究其數量或意義,這恐怕都是整個台語創作史上少有的奇景。魯蛋雖然未經台文訓練,但他並沒有落入常見的「我會講台語,怎麼可能不認識台文,所以你們台文通通都有問題」的謬誤之中(事實上,一個學齡前的小孩大多都會講流利的母語了,卻也往往無法閱讀該母語的文字;「會講」跟「會讀」本來就是兩回事)。他的立場友善,反覆提醒在留言區裡謾罵台文的觀眾,我們看不懂文字不是文字的錯,想知道文字在說什麼就要學。這當然沒辦法完全弭平所有觀眾對台文的偏見,但以魯蛋的聲量與姿態,不但證明了台灣本土語言創作環境的改善,想必也能帶來頗為正向的影響。
《廖添丁:稀代兇賊の最期》這樣用心於台文的作品,與魯蛋這樣能夠享受台文創作的玩家 / 觀眾 / 讀者,並非孤例,近年來有越來越盛的趨勢。從近處來說,或許可以歸因於基層的母語教育收到了一點效果,以及「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之後的推波助瀾;拉遠一點看,這也是政治風氣漸開、本土意識主流化、百多年來之文化累積所提供的資源。
是的,有意識的台文創作,在台灣已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遠超過1945年才進入台灣的「國語」。從清領時期以「白話字」寫成的《台灣府城教會報》,到日治時期的許丙丁、賴仁聲等小說家,都嘗試以台文創作,創造專屬於台灣人的「言文一致」。然而,不管是日治時期還是隨後的戒嚴時代,台文創作不但得不到官方教育、文化機構的支持,更往往被視為叛逆、粗俗的象徵,而遭強力壓制。這使得「台語」的公共功能持續退縮——還是有不少人能夠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台語,卻沒辦法以之進行知識傳達、政策辯論、藝文創作,前幾年所謂「母語在家學」之說法,就隱含了「台語不能、也不必有公共功能」的意識形態。
在戒嚴時期,保存台文創作一線生機的,主要是在影視戲劇和流行音樂等領域。在影視戲劇裡,「講台語的角色」往往被等同於「草根、粗俗」而定格;相較之下,流行歌詞則保存了更多庶民觀點,傳達了台灣人的美感風格、生命經驗與社會經驗。而在文學作品中,僅有少量的台語新詩創作,以及更稀少的散文、小說,比較常見的是以「地方風味」的形式點綴於華文作品之中,無論是讀者還是創作者,普遍缺乏使用台文的意願或能力。
然而,這種現象在最近幾年有了逆轉的跡象,台文創作的「正當性」與「接受度」都日漸上升。2018年,全聯推出了一批中元節廣告,其中一支廣告是由一位儒雅的男性鬼魂,以台語述說自己的過節心情。這支廣告被解讀為影射死於國民黨暗殺的數學教授陳文成。同時,也有許多閱聽人注意到,這支廣告打破了「講台語=草根粗俗」的刻板印象,呈現一種完全不同的台語角色。
這支廣告最終還是因為業主畏懼爭議而下架,難免有所遺憾。但以此為出發點,我們可以觀察到接下來幾年,台文創作的「爭議性」已經越來越低,不同領域的創作人迭有佳作,而且有顯著的多元化與年輕化的現象。2018年底,年僅二十七歲的明道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等路》,其大量融入台語氣口的作品,橫掃了金鼎獎、台灣文學金典獎等多項書獎,是當年最受矚目的文學新秀。到了2021年,洪明道更將《等路》改寫成完整的台文版,並同步推出台文有聲書,成為了真正的台語小說作品。除此之外,長期耕耘台語小說的名家胡長松,也在2021年推出了長篇小說《幻影號的奇航》,無論就規模、取材、類型,都是台語小說的里程碑。而在2020年末,這兩位小說家分別入圍兩份文壇重量級的徵選名單,洪明道被《聯合文學》選為「二十位最受期待的青壯世代華文小說家」,胡長松則以台文小說《復活的人》入選《文訊》「21世紀上升星座:1970後台灣作家作品」,亦可側面窺見主流文壇氣氛的變化。
而在流行音樂當中,也有2019年的「珂拉琪」異軍突起,以台語、日語、原住民族語創作(十分意味深長地跳過了華語),並將白色恐怖議題與動漫風格強烈的曲風融合起來,在年輕族群中掀起了一股熱潮。同樣將「台文」與「白色恐怖」兩種元素結合的,還有2021年出版的繪本《丁窈窕樹:樹á跤ê自由夢》。《丁窈窕樹:樹á跤ê自由夢》由台南女中林秀珍老師,帶領台南女中學生王亮文、蔡喻安、謝沂珍、鄭韶昀組成創作團隊,以「學妹紀念學姊」之姿,重述校園中的白色恐怖地景故事。創作團隊曾在多處訪談中提及,之所以選擇以台文創作繪本,是為了「貼近學姊的語言」,由此可見她們高度的語言意識。這兩個案例打破了「台文」與「白色恐怖」的年齡印象,無論是創作端還是讀者端,都明顯地年輕化了。
當然,上述有些樂觀的描述,並不能證明台文創作已經主流化,成為閱聽人習以為常的風景了。事實上,2021年的現在,我們所經歷的僅是一個「可能的轉捩點」——有一些改善的跡象,但整體環境仍然令人擔憂。2021年4月,阮劇團推出了大製作的舞台劇《十殿》,全劇大致以台語演出,並區分成「華文字幕」和「台文字幕」兩個版本之場次供觀眾選擇。即便在觀眾可以自由選擇的狀況下,仍有觀眾在匿名版抱怨《十殿》不尊重華文使用者,質疑創作者使用台文字幕的用意。這種「只要你用了台文就是不尊重我」的說法,本質上是一種種族歧視,卻是台文創作者一百多年不斷重複面對的日常。當我們樂觀於台文創作新浪潮的出現時,也不能忽視根深柢固的保守觀念依然頑強,隨時有可能反撲、淹沒目前所獲致的成果。
1930年,日治時期的作家黃石輝曾有一段名言:「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見的是台灣的狀況,耳孔所聽見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亦是台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亦是台灣的語言;所以你的那支如椽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去寫台灣的文學了。」這段話,揭開了「台灣話文論戰」的序幕,也鮮明地點出了台灣人「言文一致」的渴望。當我們移植來自中國的白話文,並且將這種白話文當成天經地義的創作語言時,實際上是有點時空錯位的——白話文號稱「我手寫我口」,但台灣人口中的「台語」和筆下的「白話文」其實是格格不入的。真正的「言文一致」,應當是在台文(及客語、原住民各族族語之書寫文字)普及的前提下,才能完成的。隨著時代的進展,我們看到越來越多台文創作的作品,廣泛出現在文學、戲劇、音樂、遊戲等領域裡,發揮了前人所不及的影響力;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本土語言也正從社會上流失,不但失去了公共功能,也日漸失去了家戶內的基本溝通功能……
因此,擺在我們眼前的,是一組逆向競爭的時間——在本土語言完全流失之前,我們的創作者來得及抓住「言文一致」的最後契機嗎?
・原文刊載於《BIOS review 2021 台灣文創動態回顧》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