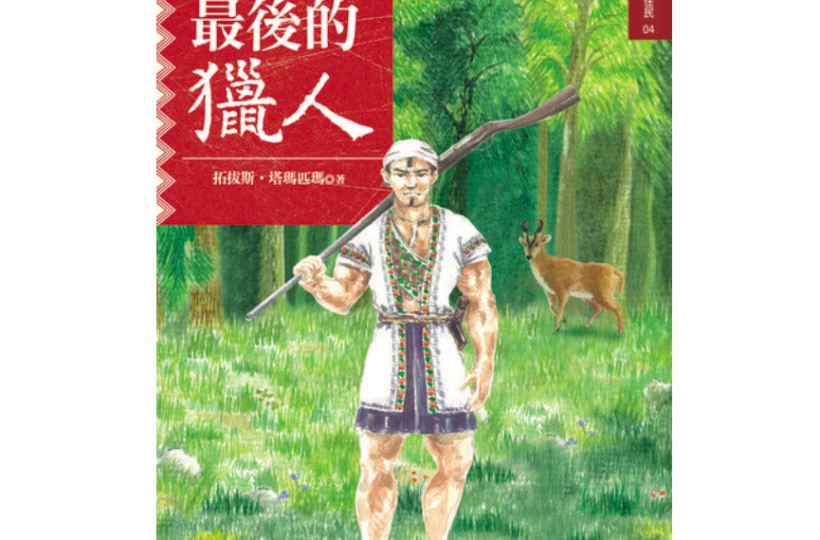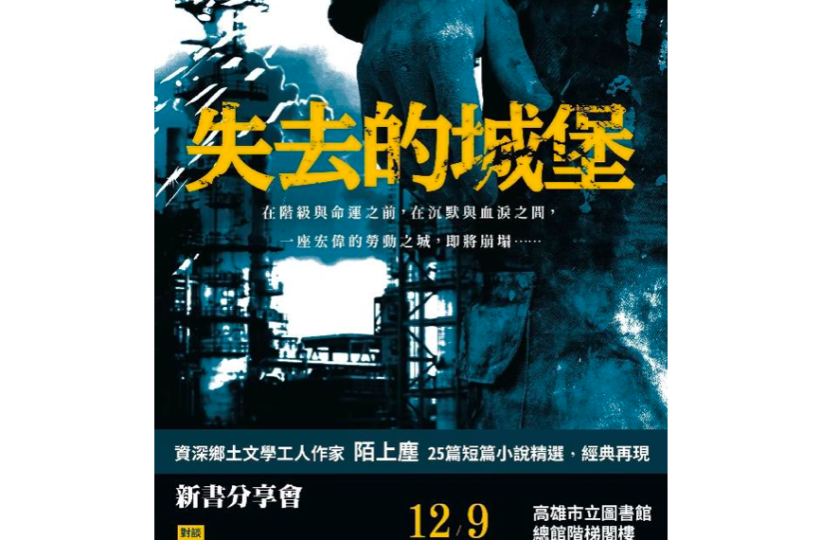有一個社群網路的小遊戲是這樣的:發起人虛構一本只有書名、實際上不存在的書,其他網友則在留言區七嘴八舌,討論書中內容。由於這本書並不存在,所以大家所虛構的「第八十七頁那隻北極熊是不是象徵主角的生命啊」、「我覺得這應該跟最後一章的『茶杯』是同樣的意涵」這類留言,反而會讓這本書彷彿有具體的形貌。對書的評論,取代了書的本體,甚至成為了書的本體。
但這個遊戲,其實遠在社群網路發明之前就存在了。更精確地說,早在1966年的臺灣,就有一位叫做黃華成的藝術家,徹徹底底玩過很類似的遊戲了。
黃華成是臺灣1960年代最重要的現代主義藝術家之一。甚至,我們也許可以省略「之一」,也不會有太多人反對。他所參與的《劇場》雜誌,也是大力介紹西方戲劇、電影,視覺設計極為前衛的刊物。1966年,就在《劇場》雜誌第五期,黃華成發表了一份〈大台北畫派宣言〉,宣告成立一個「大台北畫派」,並將於舉行畫展,歡迎各路人馬參展,參展即等於入派。
這個消息立刻傳遍了藝文圈。〈大台北畫派宣言〉洋洋灑灑寫了八十一條,內容充滿了強烈的「反藝術」之前衛精神,姿態聳動,引起眾人注意並不意外。而在消息發酵後,有媒體前來訪問黃華成,他更是宣稱已經有超過百位藝術家加入了「大台北畫派」。這一宣稱耐人尋思:臺灣整個藝文圈才多大,可以讓「大台北畫派」吸納一百多人?更別說當時的畫壇上,已有「東方畫會」和「五月畫會」兩個非常活躍的現代畫團體,黃華成到底是串連了哪些藝術家,可以如此聲勢浩大卻又無人知曉確切名單?這可比光明會還要神秘了。
隨後在《劇場》雜誌第六期,黃華成刊出了「大台北畫派1966秋展」的廣告,廣告詞延續了「宣言」的戲謔風格:「不兮看兮白兮不兮看兮,或兮是兮看兮了兮白兮看兮。」你把「兮」全部刪掉,就會得到一句自我取消的廢話。
當年的8月27日,「大台北畫派1966秋展」正式在「海天畫廊」舉行。如果你當時聽信了《劇場》雜誌上的廣告,真的興匆匆跑去逛展,一定會傻眼——哪裡有什麼「畫派」?哪裡有一百多人?甚至,哪裡有什麼「畫展」?從頭到尾,就只有黃華成佈置的一個奇怪的展覽空間:裡面散亂著米開朗基羅等世界級畫家的名畫,但卻是鋪在地上,任人踩踏;一臺唱機,在播放放慢了轉速,所以聽起來詭異莫名的「黃梅調」和披頭四;一大堆亂七八糟的「現成物」,如凳子、電扇、拖鞋、正在晾的濕衣服、看起來衛生頗有疑慮的茶水(可以喝,如果你敢喝的話),這些東西都可以隨觀眾的意思移動⋯⋯
此展一開,藝文圈恍然大悟。這個所謂「畫派」及「畫展」,不過是黃華成的一整套藝術行動。他壓根沒有開山立派的意思——正好相反,從〈大台北畫派宣言〉的內文,到「大台北畫派1966秋展」,他所有的言行,都是在嘲弄藝術圈的建制與傳統。比如宣言第十條:「記著,20世紀不是藝術家的世紀。」第六十條:「如果藝術妨害我們的生活,放棄它。」或者更經典的第二十九條:「藝術是會腐朽的,而且立即腐朽。新的總比舊的好。」更何況,第四十九條他不就明說了嗎:「根本反對繪畫與雕塑,理由從略。」都已經說到這個份上了,他的「畫展」又怎麼可能真的是「畫」展?
黃華成透過這套藝術行動,展示了他既前衛又戲謔的「反藝術」觀念。所有正經八百的,把藝術當作崇高真理來追尋的觀念,都是他想要爆破的對象。而「爆破」,不管它有沒有道理,卻正是1960年代的臺灣很需要的東西。在那令人窒息的時代,藝術與文學都充滿了各種陳腐的「傳統」,端著「不可數典忘祖」的架子;政治上則處於戒嚴箝制最盛的時期,一言一動都在老大哥設定的條框限制之下。如此一來,「爆破」自然充滿了吸引力。如果你聽膩了「建設反共基地、復興中華文化」,那會產生一種既不想建設什麼、也不想復興什麼的破壞衝動,也是很可以理解的。
不過,「大台北畫派」系列作為,一向被理解為經典的藝術行動案例,而廣為藝術史研究者和藝術家所稱道;然而我卻覺得,黃華成的「大台北畫派」也未始不能理解為一系列有趣的「文學作品」,或者至少是「非常依賴文學手法的藝術作品」。
如同小說家郭松棻曾經指出的,黃華成其實在1960年代,就曾寫下了非常精彩的現代主義小說〈青石〉等數篇作品。如果我們拿1961年創作的〈青石〉和七等生1962年發表的〈失業、撲克、炸魷魚〉相比,時期相近、同樣是現代主義、也同樣是兩人的第一篇小說,我認為黃華成的「起步」要比七等生高得多。但奇妙的是,〈青石〉雖然也在白先勇等人主編的《現代文學》刊登,但黃華成卻一直沒有被文學圈和社會大眾當成是「作家」。陳佳琦的〈迷失而腐朽,或者不朽:黃華成筆下的文青之死〉詳細評介了黃華成的文學成就,此文的第一句話卻非常耐人尋味:「不知道能否稱黃華成為一位作家。」衡諸全文,陳佳琦顯然沒有要質疑黃華成的文學深度,這句話更像是一個含蓄的問號——為什麼文學圈會漏了這個人?
如果我們把黃華成的文學創作放在心上,再回頭來閱讀〈大台北畫派宣言〉,應更能讀出這裡面的「文學感」。「宣言」也者,直覺令人想到堂堂正正的論述性散文,尤其開山立派,似乎更應該旌旗鮮明、軍容嚴整。然而〈大台北畫派宣言〉卻打散羅列了八十一條,刻意使其「不成文」,這種形式感本身就很文學。而細看內容,八十一條條目之間也無明顯邏輯關係,甚至多有跳躍突梯之處,例如:
7.保持輕鬆愉快。8.按時交費。9.不可以辦正事的時候興奮過度。即便一點點興奮,也不科學。違者早洩。
或者:
60.如果藝術妨害我們的生活,放棄它。61.英國女王是會大便的,天天都會。
這些條目不但不成文,甚至可以說是接近詩。其跳躍突梯,正近於現代詩的思維;但你要說這些是亂跳一通嘛,卻又未必。比如上引第七條到第九條,顯然有一經過設計的「正-反-正」結構。如果「輕鬆」是正,「按時交費」之嚴肅感則為反,而第九條則再做翻轉,以「違者早洩」戳破嚴肅感。或如第六十條,似乎很正經地提出了「生活大於藝術」的信念,卻又在下一條寫出了根本不勞旁人贅言、然而千真萬確的「女王天天會大便」,這既翻轉了前一條的語氣,又延續了前一條的「生活」。甚至不用考慮上下關係,光是第六十一條本身「根本不必宣言,卻寫在宣言裡」的內在拉扯,本身就有一種遊戲性的詩意。
更有趣的是,如果「大台北畫派」是一套作品,那它並不只是包含了「宣言+展覽」,它還另外打包了兩篇文字,一是黃華成自己撰寫的〈無題(大台北畫派秋展現場對話)〉,一是郭松棻撰寫的評論〈大台北畫派1966秋展〉。後者是一則嚴肅的藝評,並且不是由黃華成執筆,我們暫且不論。而黃華成自己下筆的前者,最後因為政治壓力而沒有公開發表,但內容非常有趣——黃華成將現實中、想像中,朋友們跑去看展之後的心得,交錯寫成了一則對話紀錄。除了黃華成本人,這則對話紀錄還包含了郭松棻、劉大任、張照堂、莊靈、邱剛健、韓湘寧、丘延亮、李至善⋯⋯等《劇場》成員與藝文圈人士。這些人化為文中的角色,直白抒發——當然是經過黃華成剪接的「直白抒發」——他們各自對展覽的想法,以及黃華成本人插科打諢的回應,形成一種類似劇本或小說的趣味。比如開頭的幾句:
女記者王小香:你展覽的目的為何?
黃:我打算開完這個展,上飛機出國。因為我要證明出去之前,我已經走到那裡那裡,我並非一無所有才出去的。
邱剛健:你的宣言可以流傳下來,《劇場》可以留下來的大概只有這篇東西。
莊靈:「尿急時可面牆行之」,嘻。
郭松芬:你仍然太悲壯!
由此,我們回頭盤點一下,就會發現黃華成透過大量的文字操作,形塑了「大台北畫派」這套作品的奇特形狀:這是一個既無畫、也無派的「畫派」。(甚至也沒有「大臺北」,因為宣言的第七十九條是:「臺北,位於球面體的兩個座標的交點上─北緯25°02 東經121° 31 。本身無意義。」)但是,這個畫派有宣言(〈大台北畫派宣言〉)、有展覽(「大台北畫派1966秋展」)、有觀眾反應(〈無題(大台北畫派秋展現場對話)〉)、也有藝術評論(郭松棻〈大台北畫派1966秋展〉),如此陰蝕陽刻、層層指涉卻又通通落空的結構,讀起來幾乎就是一篇打破敘事障蔽的後設小說了。
這正是「只有書名、實際上不存在的書」,也正是黃華成的社群遊戲。只是他玩的不是社群網站,而是藝文社群;那時也有網路,不過卻是人際網路、概念網路、權力網路⋯⋯。
文學圈從未把黃華成當成作家,他不是那種「自己人」。然而,黃華成的一言一動卻充滿了「文學感」,總是以某種「側面」的形象,出現在文學史裡。當我們談到小說家陳映真之「左轉」,總會提到他與黃華成所代表之《劇場》的決裂;當我們閱讀七等生經典的〈我愛黑眼珠〉等現代主義小說,我們想到的永遠是由黃華成設計封面的,那個意象魔魅的版本;當我們讀到1980年代,郭松棻以小說家之姿躍上文壇,最初一系列短篇小說〈青石的守望〉時,也會恍然想起黃華成的〈青石〉;甚至更隱微的,在1960年代以降,世世代代的文藝刊物,都習慣了將漢字放大、旋轉、並列、變形,利用漢字的圖像性質,來排出有強烈風格與文藝質感之版面——而這,正是黃華成主編《劇場》時,因應「沒有資金獲得圖片」而採行的節省成本之法。這可比日後以大字塞滿畫面的經典動畫《新世紀福音戰士》還早了三十多年。(巧不巧,《新世紀福音戰士》也是為了省成本)
黃華成透過「大台北畫派」系列,嘲諷了藝術圈僵化的建制與觀念。然而,面對這麼一位充滿文學感、運用文學手段創造了許多嶄新感覺的創作者,文學圈卻仍未給予足夠的重視。如此想來,被黃華成的案例嘲諷到的,又何止是「畫派」而已?
★ 作家小傳
黃華成(1935-1996),師大藝術系畢,是《劇場》季刊核心成員,刊物排版與內容著力甚多。其創作實踐橫跨多種領域,舉凡繪畫、文學、廣告等皆有涉獵,曾創立成員僅有一人的「大台北畫派」,其創作影響臺灣藝術界深遠。
・原文刊載於拾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