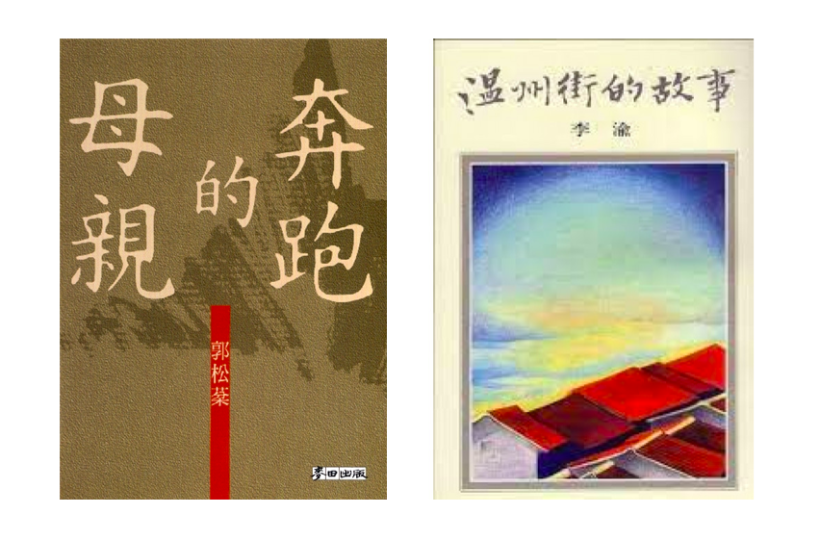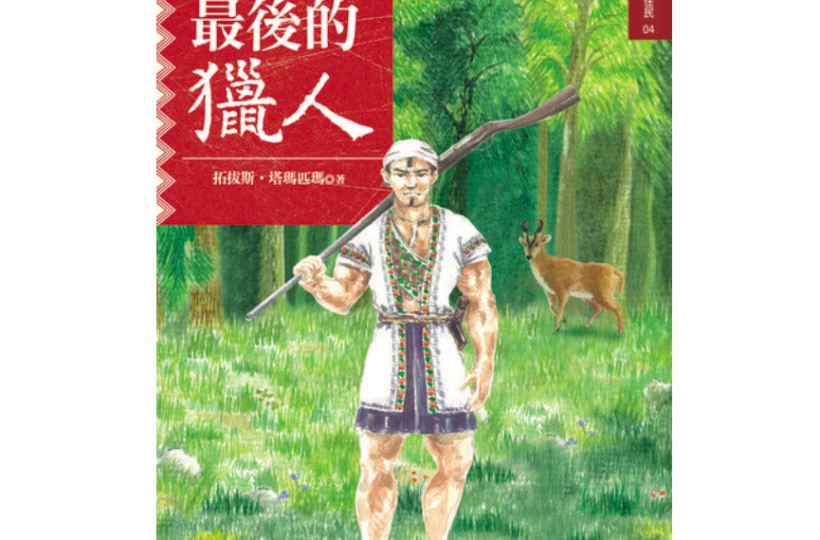過去一個禮拜,我在三個不同的場合,講了「小說中的二二八」的相關主題。這個題目我每年都談,但今年我都會特別提及兩篇小說,用來對照「本省人」跟「外省人」的觀點,那就是郭松棻〈月印〉與李渝〈夜琴〉。在這紀念的日子裡,如果你想要讀相關的文學作品,我非常推薦優先讀這兩篇。在文章最後,我會附上收錄這兩篇小說的書目。
郭松棻和李渝兩位小說家,是一對夫妻。文壇中的夫妻所在多有,但像他們一樣,雙雙寫出文學史經典、折服整個文壇的,卻可說是絕無僅有。更有趣的是,這對夫妻並不只是各寫各的,他們不只是生活的伴侶,更是文學上的伴侶,兩人的寫作題材、風格、思考都有許多互相影響、互相對話的痕跡。有些時候,讀者甚至會覺得,他們兩個會刻意一起寫同一個主題,然後展現出各自的風貌。如果說有所謂文字版本的「琴瑟和鳴」,大概沒有比這對夫妻更適合的了。
郭松棻的〈月印〉與李渝的〈夜琴〉就是這樣的作品。如果你單獨讀任何一篇,都會覺得是憂傷而充滿詩意的作品。但只要你把兩篇排在一起讀,很容易就會發現這是一套雙人舞。它們都發表於1980年代,都描寫了左派青年遭遇二二八事件,隨後被白色恐怖毀滅的故事。它們同樣都選擇了妻子的視角,去感受「隱瞞抗爭行動的丈夫,最終死亡 / 失蹤,留下茫然無措的自己」之歷程。當然,更鮮明的特徵是,兩者的文字都極為柔美,場景跳接與意象安排近於詩,並不是特別容易讀懂的作品。
更值得注意的,或許是兩篇的相異之處。郭松棻是出生於大稻埕的本省人,李渝則是中國重慶出生,幼年時來到台灣的外省人。這兩個人的出身,顯著地影響了兩篇小說選擇的視角——〈月印〉描寫的是本省夫妻,〈夜琴〉描寫的則是外省夫妻。而這樣的差異,也是我為什麼推薦大家可以對照閱讀這兩篇的原因:因為它們都各自以誠懇的態度,寫出了各自族群在二二八、乃至於白色恐怖中的記憶與傷痕。
在郭松棻的〈月印〉裡,我們會看到「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故事,是從日治時期講起的。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所受到的教養、所習得的語言、所歷經的戰爭,讓他們期盼著戰後的安寧;然而二二八與其後的白色恐怖,卻使得這一切破滅。郭松棻的小說最常見的主題之一,就是「語言」問題:本省人到了戰後,是要學「國語」的。但是學「國語」的同時,就等於捲入了語言背後的權力糾葛。〈月印〉的丈夫鐵敏就是如此,他認識了一群外省人,跟著他們講「國語」、談論時事,而這群外省人也欣賞這位才華洋溢、充滿理想的本省青年。最終,這群外省人拉了鐵敏「入伙」——原來這是一個左派組織。他們瞞著妻子文惠進行組織活動,不但閱讀禁書,更在附近建立了簡易電台,為共產黨傳遞情報。「國語」於是成為導向死亡的語言,如此「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之間的挫傷,正是本省人的特殊經驗。
底下摘自〈月印〉的這個段落,就可以看到郭松棻將本省人的二二八經驗,與日治時期以來的歷史連結起來的痕跡:
翻過年的三月,文惠在收音機聽到淒厲嘔血般的廣播。
她驚住了。她趕緊把音量轉低。
夜裡,她把收音機拿到廚房,繼續守在那兒小聲收聽。
台北發生事變了,聽說市街戰已經發生了。
這段日子,自己關在房子裡一心看顧著敏哥,跟外面完全隔絕。沒想到戰爭又要來了。
[……]
再聽到教堂的鐘聲響起來時,她也有了母親的消息。
母親說:「又太平了。」
不久,跛腳的區長連踢帶拐地踽過來。
他挨家挨戶通知,傳達上面的命令。他要每一戶把家裡收藏的日本刀統統繳出來。
「不管是軍刀、刺刀、短刀、佩劍,或是擺設用的飾刀,統統不能留了。」
區長強調說:「這是命令。」
文惠問區長說:「事變過去了?」
「過去了,過去了。」
鐵敏在夢裡被吵醒。他從枕頭上轉過頭來,奄奄地問是誰。
「沒有,是換藥袋的。」
文惠隨便回了他一句。
初夏的黃昏,天氣一下熱了起來。文惠臉上冒出豆子一般大的汗粒,把家裡日本遺孀留下來的軍刀一把一把放進浴盆的火爐裡。等到刀刃烤紅了,她從炭火中抽出來,拿到廚房外邊,用鐵鎚敲打,直把筆挺的軍刀敲得捲成一團。
天色暗下來,文惠在牆角下,挖出一個個深洞,然後把一把一把變得捲捲曲曲的軍刀統統埋下去。
文惠背著鐵敏,花了三天的時間,完成了這個工作。
她和母親商量。母親也說把它燒掉埋起來的好。免得繳出去,官廳看到藏了這麼多大刀,反倒起了疑心。
最清晰的一個細節,當然是「日本刀」。主角夫妻所住的,是日本軍官離開台灣後留下的宿舍,因此有很多軍刀,象徵了日治時期的歷史遺留。而這些遺留,在二二八之後,便因為官方要收繳武器、文惠又不願意讓官方起疑,因此自行銷毀了。如果你把「日本刀」代換成「台灣人的日治經驗」,就可以明白這段要表達的東西了。在國民政府的壓制下,這一切「關於日本」的東西,通通都要被毀棄了,而且是自我噤聲式的毀棄。另外,前半段有「沒想到戰爭又要來了」一語,指的當然是本省人本以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可以迎來和平了,也是將二二八放在「戰爭後的戰爭」來理解的本省觀點。而在遣詞用字上,郭松棻也有意識地保留了某些日本詞彙,呈現本省人的語言習慣,如「市街戰」、「事變」等。
相對來說,李渝的〈夜琴〉當然就不是以日治時期為根源,而是將「二二八‧白色恐怖」的脈絡,連結到中日戰爭、國共內戰以來,中國十多年的動亂。這是外省人所面對的處境。值得注意的是,郭松棻描寫本省人面對「二二八‧白色恐怖」時,其實帶有一種天真的慌亂: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正在面對的國民黨,是怎麼樣的政權。因此〈月印〉的女主角,會將不該交給警察的一箱禁書送出去,導致了丈夫的死亡。但李渝的〈夜琴〉不同,故事裡的外省人在這方面是相對「老練」的,因為他們早就在中國見識過國民黨的手段。不只〈夜琴〉如此,在整本李渝的《溫州街的故事》裡,我們都可以強烈感覺到,在台灣的政治恐怖,對外省人來說是「舊苦難的延續」;而對郭松棻筆下的本省人來說,他們雖然曾經被日本人殖民,但卻是第一次面對這種形態的政治恐怖,是「新苦難的開始」。兩種苦難沒有誰大誰小的問題,然而我們可以想見,如此不同的歷史經驗,必然讓兩個族群面對「二二八‧白色恐怖」時,有著截然不同的感覺與應對。
李渝的〈夜琴〉就有一個頗長的段落,呈現了外省人——並非加害者的那群外省人——在二二八的遭遇:
……她用一支木勺,把飯粒攪了攪,讓紅豆均匀分布在開始黏的湯中,準備等會就起鍋,進門就炒菜。
這時她又聽見了槍聲。
起先她還以為哪家放爆竹,劈劈地在遠處慶祝。可是一輛掛滿樹枝的卡車從眼前開過。她趕緊回屋走,手裏還拿著勺。
巷子太窄,車身搔刮著門前的矮樹,枝葉紛紛折落。車後架著機關槍,圍站了穿憲兵制服的人。匆匆一眨在他們臉上她又看到熟悉的面目;戰爭並沒有結束。
不要出去。他終於回來,比平日晚一些,回身關緊前門。不要出去。
她收拾了一點衣物,第二天,在戒嚴令頒下前,由女老師帶著,繞過鐵絲網和砂包,穿過市區,來到近河的兩層樓房,最裏頭的一間寢室,窗閂好,門關好。
黑暗的白天和夜晚一樣寒,每個角落都濕漉漉的,摸在兩個指間一層水,霉雨的天氣。
靜聽尖銳的哨聲,沉悶的砲聲,沉重地壓過去路面的車輪聲。爆竹似的槍聲變成輕脆的嗒嗒嗒。
有時候,這些聲音都沒有,她們就聽見樓上女老師和母親或者其他人的講話聲,鼻音很重的台語。
以及腳底踩在木板和木板嘰吱的聲音,從一頭慢慢傳過來,在門口停下。扣門。暫停呼吸。
不是請願團,不是工作隊,不是憲兵隊。
那是女老師的母親請他們去陽台透透氣。很夜了。
黑暗的街,游魂的人,一羣過來一羣過去。木板架成篝火在不遠的地方燃燒。有一隊暗影向這邊移動。看不見人的臉,但是你聽見踏步的聲音。像閱兵的隊伍經過陽台,整齊地進入霧茫的那頭。篝火靜靜燒,眾人再回來。爬上電桿。電線像蜘蛛網一樣飄落。消火栓拔起來,沒有水花。卡車開過來,人撿收起地上的東西,爬進後車,開走了。人影又蜂擁過來。拆散的大門,木板,招牌,扔到火頭上,重新燃燒燃燒。
在這一段裡,你可以看到經典的「本省人保護外省人」的橋段,以及外省人在全然陌生的語言環境中,所感受到的肅殺氛圍。所有腳步聲、敲門聲,都令人束緊神經。有趣的是,引文第四段也出現了「戰爭並沒有結束」,與〈月印〉裡的「沒想到戰爭又要來了」遙遙呼應。同樣是在講戰爭,我們可以看出兩種視角的理解方式不太一樣。〈夜琴〉的語氣是「又來了」、久病厭煩的無奈,〈月印〉則是措手不及的困惑,正可對應外省人、本省人不同的歷史經驗。
此外,〈月印〉和〈夜琴〉也都涉及了「丈夫瞞著妻子參加抗爭」的情節。在〈月印〉裡,這種隱瞞最終造成了「告密」的悲劇。在〈夜琴〉裡,這種隱瞞則是更徹底的:妻子甚至連告密的機會都沒有,因為她直到「二二八」平息、丈夫隨即失蹤、特務上門來訊問的那一刻,她才知道丈夫參與了某些政治活動。因此,〈夜琴〉有一個更強烈的「我們無法知道人的另一面,即使親如丈夫」主題。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這段:
她應該早注意他平日的言行和交往的,在飯桌上和他說點話。在還沒睡的晚上,剛醒起來的早晨,和他聊聊學校的事。或者去野外玩玩。——或者生個小孩。已經有這樣的打算,總以為還有時間呢。
戰爭,戰爭,中國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戰爭。
戰爭轟然進行,她和他和父親母親妹妹若不是常在分離,就是從這一地轉到另一地。低語收拾,沉默的急走,奔跑,躲藏。連好好說幾句話的時間都沒有。炸彈在洞壁外爆炸,她閉眼靠著冰凉而戰慄的壁石。有一天,等戰爭過去了,一切都要重新開始重新開始。
連續出現兩個土黃色中山裝,問她很多關於他的事,問到後邊軍營悠悠吹起了熄燈號。
聽著聽著她就走了神,心裏在兩個問題上打轉:是回去了呢還是抓去了呢?
對方穿著寬腳的長褲,黑色的皮鞋。放在另一個膝頭上的腿一顛一顛,露出黑色有金線的尼龍襪,和褲管之間長著灰白色汗毛的腿踝。
最近有什麼特別的事嗎?灰汗毛說。
她端正地坐在桌旁,低頭在腦裏努力地搜找線索。
從牆角的霉痕伸出一條裂縫。沿著底邊走。往上斜著走。消失在椅的背後。
霉縫在煙裏逐漸恍惚。她努力地尋找,特別的,特別的,特別的事。
列車的車輪,向前駛,沒有聲音;草原的聲音,河水的聲音,車隊的聲音。靜止的水面,黑黝的車廂,混濁的鼻息吹在臉上。低飛的軍機。突然閃下一線強光,她驚醒過來——
其實,她是一點都不知道他的。
一個好人,在小學做六年級的級任老師,從不打學生,下課就回家,睡前喜歡喝一碗加白糖的紅豆稀飯,就這樣了。
想想看,想想看。灰白汗毛在褲管的邊緣探頭。灰白色的報絮燒成灰,飛揚起來,小卷小卷的。
她咳了一聲,用手背遮住唇角。
為什麼人人都要去不見呢?
有一天她去街上走,中飯和晚飯都沒吃,天黑了還沒回來。有一天她一直哭一直哭,哭到用抹布擦眼睛,辣子擦進了眼皮。她用水一直沖,忘記了為什麼哭。
這整段裡,我們不但可以看到「戰爭並沒有結束」的主題,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她是一點都不知道他的」之主題,將左派地下黨隱匿身份的情節,表現得更加鮮明。除此之外,〈夜琴〉的妻子在被訊問時,心裡閃過了「是回去了呢還是抓去了呢?」這句話,也很有代表性——這正是外省族群才會有的疑問。「抓去了」,這好理解,就是被國民黨抓走了。「回去了」,這顯示了外省人想像的社會空間,也顯示了左派份子有可能「潛回祖國」的路徑,這是本省人「比較少見」(但不是完全沒有)的選擇。跟〈月印〉對照,我們就會發現這裡面有兩種族群的「後路」差異:〈月印〉的本省丈夫被殺之後,本省妻子雖然孤獨存活,但至少仍有本地親族能夠照顧她;〈夜琴〉的外省丈夫失蹤之後,外省妻子在台灣真的就是獨自一人了,她既回不了故鄉,在本地也無社會支持,所以立刻就要獨自搬家、工作。
而引文後半出現的「為什麼人人都要去不見呢?」,這就不是外省人獨有的了,不管在本外省的「二二八‧白色恐怖」敘事裡,這都是一個經典主題。那是一個身旁的人會莫名其妙消失的年代,而且往往是越好的人越先消失。
以上,簡單介紹郭松棻〈月印〉與李渝〈夜琴〉的一些看點,以及可以比較之處。當然,這兩篇小說各自都很複雜精深,真要講起來還可以再寫幾萬字,在「二二八紀念日」這一天,就先以「二二八」相關段落為主,在此打住吧。在「二二八」七十五週年的這天,遠方有戰爭,而我們保衛台灣人歷史記憶的戰爭也還沒結束。甚至,不僅僅是「保衛」,更是要「熟悉」這些記憶,「精煉」這些記憶。過去的文學作品已經為此做了很多努力,但在這條路走完之前,這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都還需要更多人的參與。
對郭松棻〈月印〉和李渝〈夜琴〉兩篇小說有興趣的朋友,可參考春山出版社的《白色恐怖小說選》第一冊,這本書同時收錄了這兩篇,並且將這兩篇編排在頭尾的位置,看完我這篇文章,也許你多少能理解為什麼該叢書主編會把它們排在第一冊、會這樣編排了吧。如果想要閱讀兩位作家各自的作品,可以參考郭松棻《奔跑的母親》與李渝《溫州街的故事》,不只我們所討論的這兩篇各自收錄其中,也還有很多精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