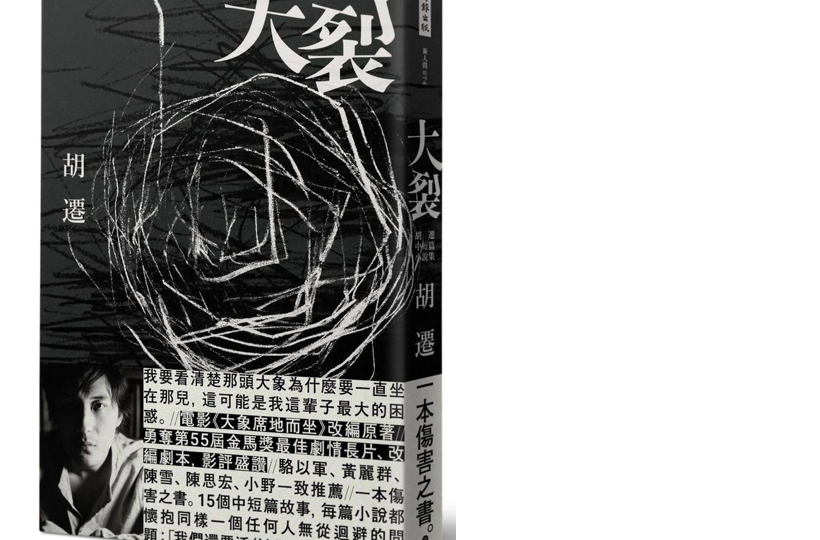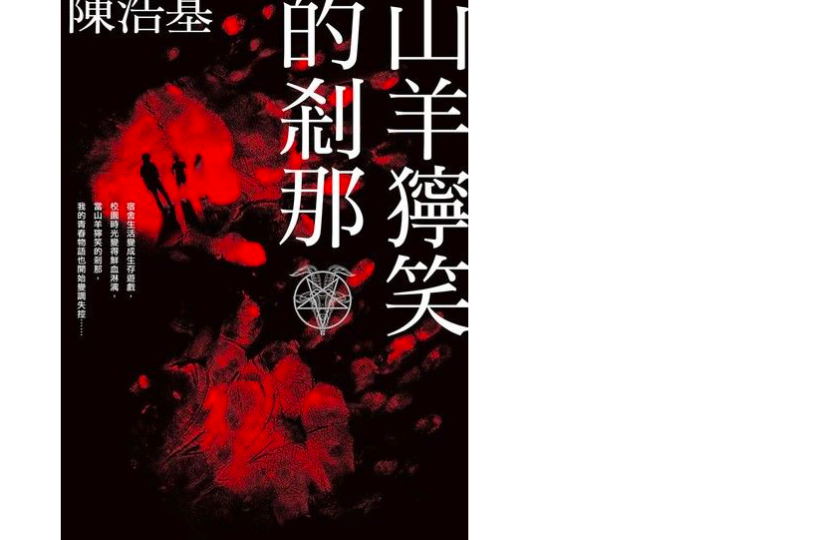那些細節,往往都是情感最真切、銳利甚至痛楚之處。我自以為明白她為什麼會這麼問——許多剛開始寫作的人,害怕在文章裡袒露真心話;把真心寫出來,不但是卸除自己的武裝,更可能引起許多人事麻煩。畢竟,人的痛苦往往都是他人帶來的,那些「他人」,很可能完全沒有自己正是「地獄」的自覺。
然而,在文學裡,特別是在散文裡,這種真心特別珍貴。
於是我自以為是地回答她:「不用擔心,就寫吧!文學是最能容納這些情感的地方了。」
但在多讀幾篇林佳樺的文章之後,我才意識到自己的回答是多麽不負責任。
沒錯,站在讀者的立場,作者當然是越真心越好。文學不批判,文學容納傷口,這都是對的。但問題是,世界上不是只有文學讀者,寫作及其帶來的效應,也包含了不寫、不讀、不懂文學的「他人」。
我之所以能夠輕鬆講出「就寫吧」,是因為在我有限的經驗裡,這些「他人」並不難應付,甚至於可以不用應付。
因為我是異性戀、中產階級、漢人、男性。我所屬的族類,從一開始就是一層防護罩,讓我有更大的資本「寫出真心」。
就拿林佳樺的新作《守宮在唱歌》來說吧。書名取為「守宮」,指的既是曾經豢養過的寵物,更是指涉了「子宮」。書中有大量篇幅,都圍繞著作者所經歷過的「關於懷孕的一切」:天生體質難以受孕,好不容易走過不孕症療程,生下一名女兒後,又在第二胎遭遇困難。中間不但多次流產,甚至還遇到醫療糾紛,身體嚴重受創不說,院方為了規避責任,還指控她精神狀況不正常⋯⋯
這些文字,在我這樣的男性讀者看來,是極為驚心動魄的——懷孕、流產、不孕這些「好像沒那麼遙遠」的概念,在林佳樺筆下寫來,才一一令我感到,我實在對這些身體經驗和社會關係一無所知。當然我生理上不可能「知道」這些事情,但我的無知,是到了一種「甚至不知道自己無知到如此地步」的程度。
而更難的,不在她寫出了多少細節,而是當我想到她處理這些內容時,必須顧慮多少「他人」,就覺得頭皮發麻。從原生家庭到夫家,從丈夫到子女,從醫院裡的醫病關係,一直到工作上會遇到的人——是的,這一切「懷孕情節」進行時,林佳樺還是一名中學教師,要面對學生跟家長的。
如此層層夾擠,「說出真心」何嘗容易?
當時我輕率地說「就寫吧」,自以為是給了文學創作者該有的答案。但閱讀更多之後,反倒換我遲疑了:這,她竟然真的寫下來了?
然而,她還是寫了,而且比點到為止更多一些。這當然是讀者之福,但風險卻是由作者承受了。比如〈吃飯這件小事〉裡,她第三次流產,身體不斷出血,狀況時好時壞,就有了這樣的場景:
某天上到第四節課,教室蒸飯箱傳來鮭魚氣味,學生嚷嚷肚子餓,鼓譟想提早吃便當,我下腹突然悶痛,喉嚨一陣腥味,衝到走廊間洗手台乾嘔,只好在家休息兩天。休養期間,幾位家長陸續來電,「老師保重」「孕期何時?會不會影響孩子學測?」「老師,產假隨時可以休,孩子的前途只有一次。」
對,你沒看錯,家長說的是:「老師,(你的)產假隨時可以休,(我的)孩子的前途只有一次。」
這還沒完,等她銷假回校,學校說:有家長來告狀,則問她怎麼又在段考前夕請病假?並且,林佳樺還寫:當時許多家長一有意見便撥打台北市的1999市民專線,這些家長沒有直接告上去,還先在學校「內部溝通」,已經算是幸運的。為此,她寫了兩頁報告回應。
除此之外,描寫醫療糾紛的〈往返舟中〉、描寫不孕療程的〈瓶子裡的畢業歌〉與描寫產後憂鬱的〈光源〉,也都非常值得一讀。在我印象裡,傳統散文處理親子議題的不少,但在歌頌生養、親情之外,如此正面迎擊整個懷孕過程之艱困險阻的,卻不是太多。
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做到的。但總之,她真的「就寫了」。在這本《守宮在唱歌》,「文學容納了這些情感」是一個不太公允的說法,彷彿是文學幫助了她似的;從讀者的角度來看,毋寧說是她慷慨幫助了文學:謝謝林佳樺願意扛住人世紛擾,寫下如此珍貴的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