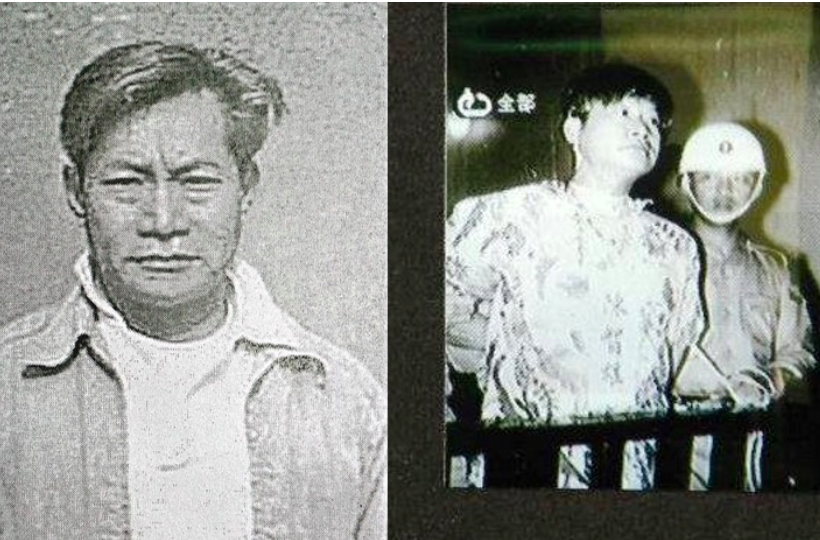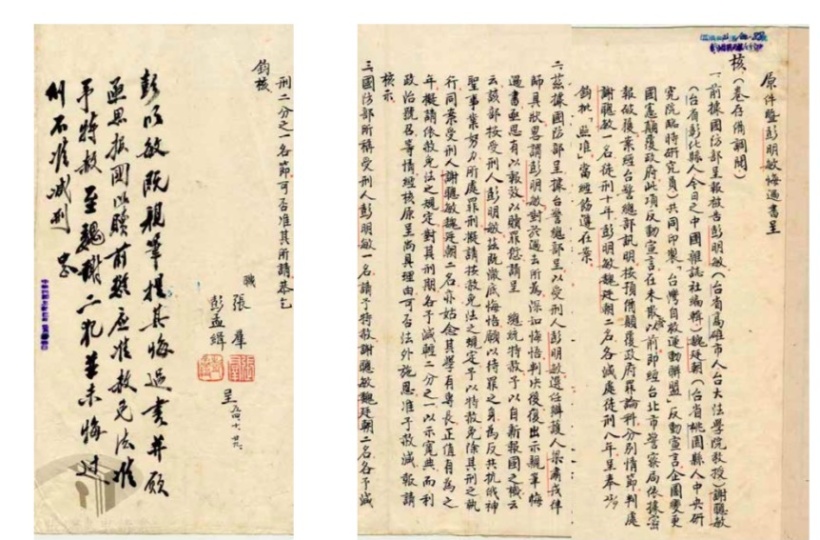1963年,陳智雄遭到槍決。
陳智雄是第一個以「台獨」名義槍決的政治犯。由於嚴密的戒嚴體制,台獨運動者幾乎只能在國外活動,特別是在與台灣有淵源的日本、支持自由民主的美國。然而陳智雄的舞台比較特別:他活躍的地方,是印尼。
事實上,台灣人早在日治時期就活躍於東南亞了——或者該說,是「被活躍」於東南亞。由於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侵略東南亞各國,台灣人也就隨著日軍的徵調,而踏上了這塊國籍紛雜、文化融混的炎熱地帶。作家陳千武便以志願兵的身分轉戰各地,而有了《活著回來:日治時期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這部短篇小說集(這副標很笨拙,但小說本身很好)。
陳智雄不同,他不是以基層士兵的身分踏入印尼的,他是日本派駐於此的外交人員。陳智雄毫無疑問,是日治時期最精英的台灣人之一。他畢業於東京外國語大學荷蘭語科,除了母語台語之外,還精通英語、日語、荷蘭語、馬來語、中國語。而當時的印尼主要荷蘭的殖民政府控管,所以當日本侵略印尼時,首先要對抗的時盟軍陣營的荷蘭,其次也要跟當地的印尼人、甚至是華僑接觸。在這種情勢下,陳智雄這樣的語言人才,毫無疑問是派駐東南亞的首選,於是被日本外務省派往印尼擔任翻譯。
二次世界大戰的東南亞,是無數台灣人的斷魂之地,卻也刺激了許多台灣人思考自身的問題。這裡有多元的本地人族群、歐洲殖民者、華人移民的後裔、侵略而來的日本人,以及既是侵略者又是被殖民者,身分尷尬的台灣人。「他們是誰」這個日常的問題,很容易就會轉為「我是誰」的自省。
日本戰敗之後,東南亞的情勢更有戲劇性的變化。日軍及從屬於日軍的台灣人在駐地等待遣返,被擊敗的歐洲殖民者則試著捲土重來。不過,在二次世界大戰遭受重創的荷蘭人,基本上已經沒有控制印尼的力量了。印尼人乘勢而起,在蘇卡諾的帶領之下接起了獨立運動的大旗。無計可施的荷蘭人,把腦筋動到還沒撤退完的日軍頭上了:名義上,日軍是向盟軍投降,因此荷蘭人命令日軍鎮壓印尼獨立軍。附屬於日軍的台灣人,自然也要一起攻打印尼獨立軍。你猜猜,當時的台灣人怎麼想?
「干我屁事。」
大概就是這樣。這是荷蘭人跟印尼人的戰爭,無論輸贏,都不干台灣人什麼事。印尼人也知道台灣人沒有戰意,所以雙方都意思意思。陳千武的小說〈默契〉開頭的第一個場景,就是(日軍)台灣人架起機槍,對著印尼獨立軍的軍營,旁邊的大樹,打完一輪子彈。接著,印尼獨立軍也對著日軍軍營旁邊的空地,打完一輪子彈。今天這樣就算收工了,台灣人溜出軍營,一遇到印尼獨立軍的崗哨,就敬禮說:「蘇卡諾默迪卡!」(蘇卡諾萬歲!)印尼人就放他們過去了。台灣人可以自由地在印尼的城市裡面遊蕩。
台灣人於是做起了台灣人最擅長的事:他們和當地的印尼人打好關係,購買食物、糖果、衣物之類的物資,轉賣給有錢但不敢進城的荷蘭有錢人,大賺一筆。
「蘇卡諾默迪卡」根本是提款卡密碼。
但陳智雄比較不一樣。在印尼獨立的熱潮中,他想必想起了台灣自己的命運。台灣有沒有自己的蘇卡諾呢?台灣會有自己的獨立運動嗎?他同情印尼獨立運動的發展,於是藉著他的太太,一位擁有1/4荷蘭血統的印尼人的掩護,他開始把日軍遺留下來的武器轉送給印尼獨立軍。也因為這樣,陳智雄曾經遭到荷蘭殖民政府的逮捕。印尼獨立之後,蘇卡諾更授予陳智雄「榮譽國民」的頭銜。
台灣人陸續遣返回台,但陳智雄就這麼待了下來,並且加入了廖文毅所發起的台獨運動團體。由於他長期在東南亞的外交圈子活動,人脈廣泛,於是也被廖文毅任命為東南亞地區的代表。1955年,陳智雄攀上了外交生涯的最高峰:在他的運作之下,廖文毅以一介流亡政府領袖之姿,參與了「萬隆會議」——同席的各個第三世界國家代表,包括了中國的周恩來、印度的尼赫魯、埃及的納瑟、馬來西亞的東姑阿都拉曼以及印尼的蘇卡諾。
在1950年代的後半,一連串錯綜複雜的過程之後,陳智雄被國民黨的特務綁架回台。由於缺乏證據,陳智雄很快就被釋放。但親眼見過東南亞風起雲湧的獨立運動的他,並沒有放棄台獨運動。1961年,陳智雄發展的台獨組織敗露,本人以叛亂罪被起訴。1963年5月28日,陳智雄被槍決。在法庭上,陳智雄全程都以台語答辯。法官怒斥:「為何不講國語?」精通六種語言的前外交官回答:「台語就是我的國語。」
根據獄友的回憶,陳智雄被帶出牢房時,全程都喊著「台灣獨立萬歲」(這次,終於不是喊別人默迪卡了)。為了阻止他繼續發聲,獄卒以鐵絲貫穿他的臉頰,並以斧頭砍斷帶著腳鐐的腳掌,就這麼把他拖行到行刑槍隊之前。
(七年後,當黃文雄刺蔣被逮捕時,說出「讓我像台灣人一樣站著」的時候,是否有感受到某種冥冥的意念輪迴呢?)
隔年,我們前面提過幾次的作家陳千武,提筆寫下了他的「志願兵」系列的第一篇小說。在〈默契〉這篇裡,有個善良的印尼獨立軍小兵,與台灣人主角有了這段對話:
—
「老兄!日本戰敗了,你們福爾摩沙是不是也要獨立?我也要喊你們國家默迪卡……」
林兵長一瞬躊躇了再說:「福爾摩沙被殖民五十年,神經都麻木了,不像你們這麼年輕鬧獨立。在我的故鄉,兄弟們都為了回歸祖國而興奮呢……。」
—
「躊躇」。欲言又止的刪節號。
陳千武真正想說的是:我們台灣人多麼羨慕你們,我們台灣人多麼恨自己的兄弟如此麻木。
而在陳千武這系列的最後一篇〈遺照〉裡頭,他描寫了一名歷經了戰火而活下來的年輕人。他沒有死在南洋戰場,反而是在回到台灣之後,死於二二八事件。
我想他們兩個人應該不熟。但我每次讀陳千武,都會忍不住想起陳智雄。
他們都是見過東南亞那茂盛的生命力的台灣人,從此就沒辦法再麻木自己了吧。
他們證明了,台獨從來不是內向的運動:從一開始,它就是跟世界的脈動連結在一起的。
・原文刊載於臉書「退讚故事系列」
【退讚台灣史】1963年,陳智雄遭到槍決。
2019/10/15 _時事雜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