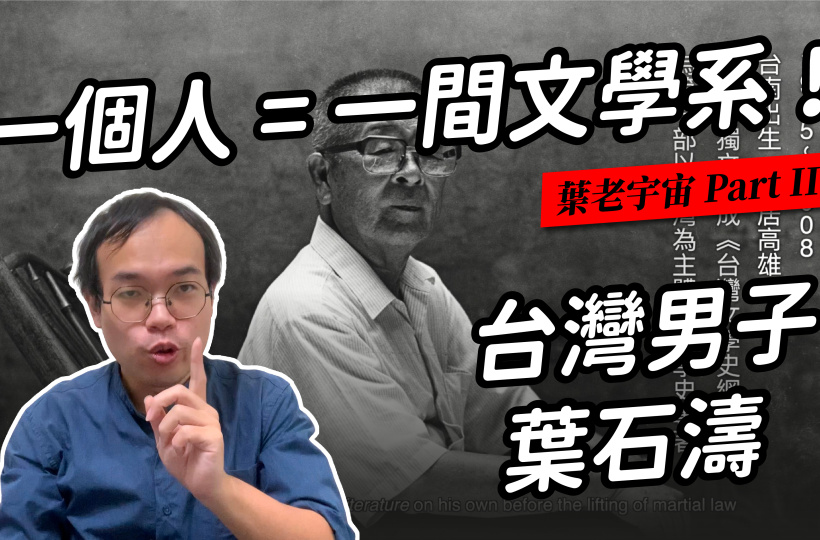在開始談論紀錄片《台灣男子葉石濤》之前,我想先來談談「遲到」。雖說英語有「遲到總比不到好」之說,不過在台灣文學史的方方面面,我們也真的是太受「遲到」的困擾了。從日治時期,台灣開始有「新文化」的自覺起,人們普遍就陷在一種「落後」的心理狀態。所有急起直追、迎頭趕上世界的努力,都是由這種落後而形成的遲到焦慮。偏偏台灣的歷史命運曲折,這些努力又常因外力之介入,不得不半途而廢。日治時期的「殖民地漢文」銳意革新,卻被二次世界大戰打斷;1930年代高度發展的日文文學,卻在終戰之後被國民政府打斷。而戒嚴時期的種種倒行逆施,更是把此前的文學資產斬得柔腸寸斷,不斷上演「重新發明車輪」的慘劇。
於是,只能繼續「遲到」。
即便把時間快轉到2022年的今天,我輩文學人還是多有遲到之感。這次,不只是焦慮跟不上世界的脈動,更是焦慮於歷史的流失。解嚴之後,本土化運動躍上檯面,雖然一路走得跌跌撞撞,但總是累積了數十年的研究與創作。這些能量,在2014年「三一八運動」之後,與整個「天然獨」世代的本土意識覺醒結合起來,激發出最近十年蔚為大觀、橫跨各個領域、以台灣史為題材的創作。
這些創作極有價值,我毫不懷疑幾十年後的人回看此刻,會明確感受到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然而在這股浪潮中,「遲到」之感仍然揮之不去。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些青年創作者都是解嚴之後出生長大的,他們對過往台灣史的認識乃至於轉化,都是從文獻、調查當中「補課」而來的。不管他們的創作表現良窳,終有一種不安貫串其中。小說家黃崇凱的《文藝春秋》裡有一篇〈遲到的青年〉,或可視為縮影:標題所指的,一方面自然是作為小說主題的前輩作家黃靈芝;但換個方向想,這又何嘗不是作者(及其同代人)的自況?我們其生也晚,都是遲到的青年,並且都這麼遲這麼遲地,在黃靈芝(及其同代人)凋零之後,才開始認識他們。
我認為,許卉林導演的《台灣男子葉石濤》最可貴之處,就是以各種方式去處理這種「遲到」。作為一部以作家為主題的紀錄片,卻在作家逝世十多年之後才開拍,從一開始就有不可跨越的時光落差。如果沒有拍好,很可能就會變成「以葉石濤為主題的文獻回顧集」,只是覆述已有的前行研究結果。畢竟作家已逝、全集與相關文獻俱在,將這些內容影像化,也不能說是毫無意義,至少有推廣之功。
然而,《台灣男子葉石濤》的野心顯然不止於此。紀錄片裡的每一個設計,幾乎都意在「從已有的文獻資料,激盪出新的觀點」。比如說,文學紀錄片總是要引用幾句葉石濤的文學作品吧?《台灣男子葉石濤》的引用方式,不是直接貼上字卡完事,而是找了「莊子」莊益增扮演葉石濤,並且以台語演繹葉石濤的小說段落。莊益增的聲音魅力毋庸置疑,但我除了沉醉於他的台語氣口之外,更驚豔於這層設計的深刻用意:葉石濤那一代出生於日治時期的作家,一生都必須以「他人的語言」寫作——明明母語是台語,卻必須以日文、中文書寫。因此,莊益增的台語朗讀並不只是「朗讀」,而是一種「還原」,那是葉石濤無法在戒嚴時代發出來的聲音,此刻卻在紀錄片裡回到本來面目。
進一步說,這甚至也不只是「還原」,更是莊益增的「詮釋」,因為葉石濤將台語轉換成中文時,勢必削足適履,將文字改成中文的語法和用詞。而當莊益增以自身對台語的理解,推敲那「履」裡面的「足」本來是什麼樣子,並將之讀出聲音,一種極為深刻的閱讀就在那一刻發生了。在我意識到這一點後,只要莊益增的聲音響起,我就一定緊盯字幕,不放過任何「葉石濤的原文」和「莊益增的聲音」有字句落差之處。這些落差,正可以體現《台灣男子葉石濤》逼近已逝作家的虔誠努力。
更驚人的是,同樣結構不止發生在莊益增的演出上。在片中,許卉林導演找了十一位藝術家,讓他們閱讀葉石濤的作品之後,以各自擅長的舞蹈劇場、舞台劇、落語、動畫等形式,來演繹小說的情節。比如兩組不同的藝術家,以不同的舞蹈形式表現〈西拉雅末裔潘銀花〉和〈牆〉,將文學語言轉換成身體語言;或者將〈群雞之王〉的一段角色衝突,改編為語言風格鮮明互衝的「落語」;或者將〈有菩提樹的風景〉最恐懼的「眼睛」意象化為黑白動畫;將〈葫蘆巷春夢〉的孤寂慾望改編為舞台劇……凡此種種,都讓觀眾不只「讀到作品」,更讀到「只有紀錄片才能完成的版本」。文學紀錄片一怕只談作家而不談作品,流於人情八卦;二怕生硬置入文本,不知為何要捨書籍而就影像。《台灣男子葉石濤》一次解決兩個問題,以創作激發創作,以藝術對話文學,讓作家的身影可以深深挺立於文字世界,又不止於文字世界。
相對於葉石濤,這些藝術家自然也通通是「遲到的青年」。從我這樣讀文學的人來看,我雖偶有「他們對文學的理解並未百分百到位」的感受,但更多的卻是「原來這樣的理解,可以激發這樣的作品」的驚艷,彷彿葉石濤的文學生命不僅僅延長了,更增生繁衍了。當然,隱身在這種種結構背後的許卉林導演,自然也有她的觀點與詮釋,這很可以從擇取的文本與材料中看出來。但《台灣男子葉石濤》難得的是,它不只是要成為「一家之言」,而是希望打造出「一整代人回望葉石濤」的,「遲到青年」的大平台。在這裡,「遲到」不再只是一種焦慮,而更是一種翻譯時間、跨越差距的方法:我們就是其生也晚,但晚有晚的讀法。
重要的不是重回歷史現場,攔截所有流失的時光;重要的是繼續以我們的觀點讀下去,接上一度被阻塞的水源,讓歷史從這個時間點開始,湧出新的支流。這或才更是「在島嶼寫作」的積極姿態吧。
・原文刊載於自由副刊2022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