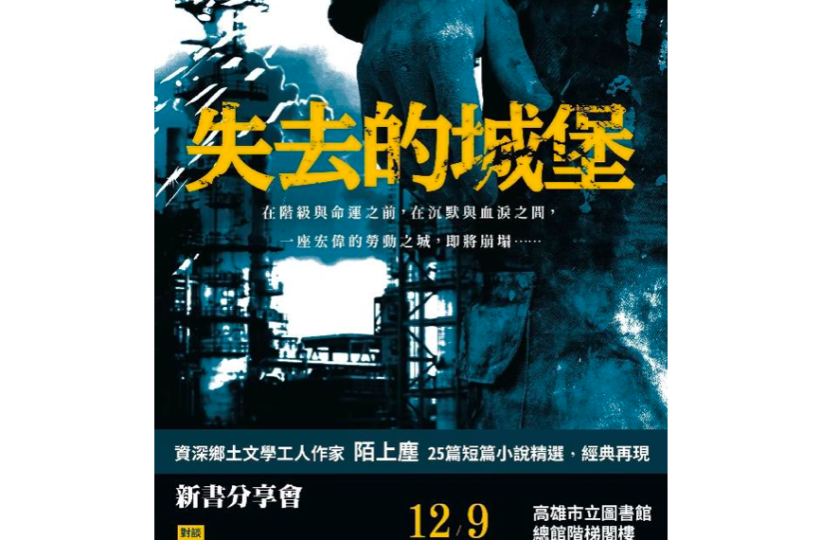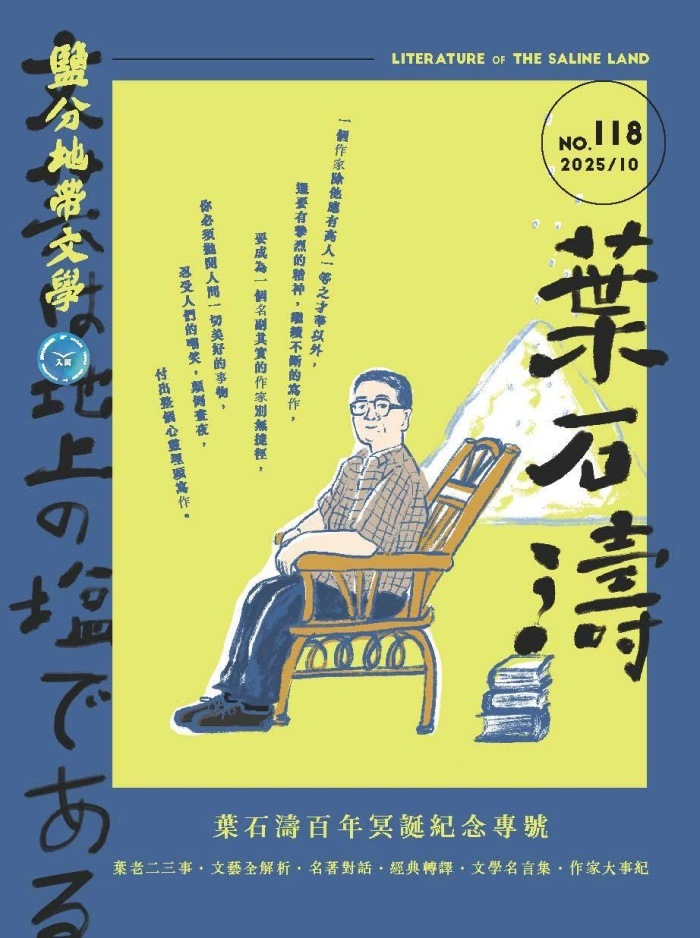本文為《新編鍾肇政全集》解說,收錄於該全集第30冊。
若以時間序來排列,本冊實是倒著排的。全書最末的附錄《寫作與鑑賞》,乃是鍾肇政於1956年出版的譯作;當時,他甚至還沒出版自己創作的第一本書。接下來,是散佈在中段的各式討論日本文學、評介台灣作家的篇章,這是鍾肇政於文壇上嶄露頭角,甚至站穩腳步的時期所撰述。而本冊開篇的數篇談論「台灣文學」之文章,則全是解嚴之後,乃至於二十一世紀政黨輪替之後,台灣文學衝破政治禁錮的時代寫就的。
也因此,雖然本冊只是鍾肇政全集當中的一小部分,卻很有代表性地跨越了鍾肇政文學生涯中的三個時期。以下解說,便以這三個時期為綱,分別補充脈絡。
一、「寫作與鑑賞」:作家的起步
如果將翻譯作品也算在內,《寫作與鑑賞》便是鍾肇政的第一本書了。然而,這本書的出版,卻是無心插柳的結果。
鍾肇政出生於1925年,他二十歲以前的「文青」養成時期,都在日治時期度過。也就是說,雖然我們現在讀到他的作品以中文為多,但他的「第一文學語言」,實際上是日語。在二十歲以前,鍾肇政還沒有立定文學創作的志向,因此沒有太多寫作紀錄;然而,那時的他已是耽讀文學作品的青少年了,從日本的和歌到西方的翻譯小說,他都十分沈迷。這些閱讀經驗不但打下了他的文學基礎,也奠定了他跟「日文」的不解之緣——在往後的文學生涯裡,他的日文閱讀能力將成為他立足文壇的重要資源。
然而,這份「資源」,在國民黨政府剛來台的那段時間,卻更像是「負債」。1945年終戰,台灣轉交中華民國政府。這時候的台灣媒體呈現了「國文」、「日文」交錯呈現的局面——台灣人雖然熱情學習「國語」、「國文」,畢竟五十年來的語言環境難以一夕改變,還是需要日文、日語來緩衝。不料,到了1946年的「光復節」,當局下令廢除報刊上所有日文欄位,強制以「國文」取代之。
這一粗暴且缺乏社會語言學常識的政策,究其後果論,幾乎可以說是一次文化上的大屠殺。日治時期所累積的深厚文學傳統更是首當其衝,其載體之日文遭禁,也就等於斬斷了傳承與創新的管道。諷刺的是,在日治時期猶能與殖民者周旋,努力創作的作家們,反而在「回歸祖國」一年後,因為語言政策而全面退出文壇。
鍾肇政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了他艱困起步的創作生涯。不過,比起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這些文學前輩,鍾肇政的優勢在於年紀較輕,在咬牙苦練中文之後,還能勉強獲得一些成果。若是比他大一輩的作家,文字轉換的難度勢必更高、經年累月的轉換期也會將創作的黃金歲月耗費殆盡。
《寫作與鑑賞》便是在這種特殊條件下動筆的。1951年,鍾肇政首次以〈婚後〉這篇短文投稿成功,激發了創作的慾望。然而,接下來的投稿卻屢投履退。鍾肇政在挫折之餘,也苦思如何鍛鍊。於是,就有了《寫作與鑑賞》這系列文章:鍾肇政從自己熟悉的日文入手,尋找日文作家的創作經驗談,並且將之翻譯為中文,投稿到報刊上發表。這一舉動有一箭三鵰之效:一來閱讀名家的創作經驗,吸收創作知識;二來透過翻譯來練習中文,加強文筆;三來投稿報刊,可以略收一些微薄稿費,也能有一點曝光度。
這裡需要附記一筆的是,當時的版權觀念並未如當代一般健全,因此這系列文章應該都是未有正式授權的。因此,這種一箭三鵰的毅力與創意誠然可感,但卻不是當代的我們能率然仿效的。
總之,這系列「日文轉中文」的文章,可以說見證了鍾肇政「練功」的時期。鍾肇政以「路加」為筆名投稿報刊時,並非以出書為目的,然而世事流轉往往出人意表。當時,創辦「重光文藝出版社」的作家、同時也是立法委員、黨國文藝政策的主力陳紀瀅,在報紙上看到了這批文章。他覺得這些文章不錯,便透過副刊邀約,將這些文章結集為《寫作與鑑賞》一書出版。在譯者序裡,鍾肇政謙遜地自稱「荊棘長途上的一個摸索者」,又自稱「先天不足的羸弱幼苗」。衡諸文學史事實,荊棘是有的,那便是國府粗暴的語言政策;「先天不足」一語卻不能當真,能夠憑自己的努力跨越語言障礙,已是先天豐沛、後天堅毅的結果了。這本書的出現便是證明。這株嬴弱的幼苗,已在《寫作與鑑賞》裡展現了他不凡的決心了。
而若是對日本文學有興趣的讀者,更是可以對照《寫作與鑑賞》中引述的名家,與當代我們所熟悉的日本作家名單有何異同。若您覺得陌生,那或許正顯現了鍾肇政那一代人與日本文壇的理解,是與戰後台灣文壇大不相同的。他們是在另一個脈絡下成長起來的讀者與創作者。
二、日本魂與台灣夢
本冊〈日據時代的新文學〉到〈窄化的文學世界——淺談日本小說之神的短篇小說〉,可以視作第二部分。這部分的文章大多數時間落於戒嚴時期,是鍾肇政作家生涯最成熟、活躍的時期。
這批文章當中,「日本」與「台灣」是兩個顯著的群集,也展現了鍾肇政立足於文壇的特殊位置。
先談日本。從〈虛幻與淒美─川端康成筆下的女人像〉、〈日本文壇怪傑─安部公房〉到〈窄化的文學世界——淺談日本小說之神的短篇小說〉等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鍾肇政對日本文學史以及日本文壇動態的熟悉,並持續在台灣文壇擔任引介日本文學作家、作品的角色。
這其實延續了上一節我們提到的「跨語」問題:在戰後初期,國民黨政府廢除日文報刊之時,日文似乎成為一種必須除去的「負債」。然而在文壇漸漸恢復生機,媒體與出版的版面增加之後,台灣本地文壇的「生產」不可能滿足所有「需求」,這時候就需要引介更多翻譯內容。縱使1949年遷移來台的外省文人當中,也有若干外文能力頗佳者,但數量仍然不足,這時候,熬過「跨語」、熬出基本中文能力的本省作家,就適時填補了此一空缺。
鍾肇政就是其中佼佼者。從《寫作與鑑賞》之後,文學副刊、雜誌便常常與他合作,邀請他翻譯日本文學作品。如果需要緊急介紹某一日本作家(比如某作家得諾貝爾獎,或者其作品改編為電影在台灣上映),也會請鍾肇政從日文資料裡摘譯改寫。在版權觀念不健全的年代,甚至也有報刊主編緊急託人在日本購書,寄回台灣讓鍾肇政即譯即刊的情形。
在戰後初期的台灣,懂日文的人不少;但懂日文又懂文學的,就相對稀有了;懂日文、懂文學、又能以流利中文書寫的,便可說是鳳毛麟角了。慢慢的,如鍾肇政這樣符合所有條件的本省作家,他們所持有的日文能力,就從「負債」變成「資產」了。
更有甚者,在國民黨政府殘缺的文化政策引導下,台灣各世代的文學讀者,很少有強烈的文化主體性,對於外國文學的興趣遠高於本土文學。而戒嚴時代可以取得外國資訊的管道很少,基本上被冷戰結構壟斷,一般人所想像的「高尚的外國文學」,實際上就等於美國文學、日本文學和特定國家的西歐文學。由此,日本文學便成為文學市場上的重要領域,在日治時期成長的「跨語」世代作家,也就有了更多展現身手的機會。更有趣的是,由於英文、日文以外的翻譯人才極為缺乏,所以要介紹歐洲文學作品時,往往也會依賴本省作家的日文能力,從日譯本來引介歐洲文學。鍾肇政所著之《西洋文學欣賞》等書,便是這種「從日本進口」的「西洋文學」。
本冊及他冊所收錄的各篇日本文壇、文學介紹,就是上述脈絡的產物。
其次,這個部分還有一系列的台灣作家介紹,包含龍瑛宗、李喬、吳濁流、鍾鐵民、魏畹枝、鄭清文、李獻章等人的評介。這些文章,呈現了鍾肇政文學生涯裡最深沈的夢想:建立起「台灣文學」的主體性。
在戒嚴時代,「台灣」二字是一個曖昧的禁語。說是禁語,因為本省人如果以「台灣」為名發起組織,往往就被視為有台獨的嫌疑,會被政治打壓;說是「曖昧」,因為這個詞又不是明文規定的禁忌,打壓時有時無,讓人難以捉摸規律之所在。
就在這種詭譎的文學環境下,鍾肇政試圖以各式各樣的報刊、出版資源,勉力組織起一支「台灣作家」的隊伍。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為了讓這支隊伍有自己的陣地,他主持雜誌《台灣文藝》、也應邀編輯《民眾日報》副刊,讓台灣作家有地方能夠發表,不必受制於黨國規定的反共文學教條。在這些報刊上,他一方面讓日治時期的文學作品重新「出土」,讓文壇重新認識被粗暴的語言政策湮沒的前代作家;一方面也讓新世代的本土作家躍上檯面,展示政治打壓也無法斷絕的文學意志。
而與報刊相輔相成的,還有出版。1965年,鍾肇政假藉「光復二十週年」的名義,向文壇社、幼獅文藝兩個出版社提案,各編一套十本的「台灣作家作品集」,簡稱「台叢」。這個策略非常聰明,利用「光復二十週年」的名義來編「台灣作家作品集」,可以取得政治上的掩護,既是台灣文學的一次火力展示,面對政治打壓時,又可以說這是展示「光復之後的文學建設成果」。詳細過程,在本冊的〈鐵血詩人──吳濁流〉一文當中,鍾老已有記述,非常值得一讀,在此不再贅述。
本冊所收的各篇台灣作家專論,幾乎均為上述兩個脈絡的產物。鍾肇政或者在自己主編的報刊上大力推介台灣作家,或者在「台叢」上評介有潛力的新人。時至今日,鄭清文、李喬等鍾肇政大力稱讚的新人,已經確實成為台灣文學史上毫無疑問的經典作家了。當我們展讀這些名家的作品時,更不應忘記鍾肇政文壇環境險惡時期的苦心經營。
三、台灣文學的開花結果
本冊的《台灣文學十講》到〈客家運動十年〉,可以說是終於迎來了鍾肇政作家生涯裡,春暖花開的時期。
從1950年代提筆寫作,歷經退稿挫折、透過翻譯練習中文,再到嶄露頭角、在文壇上成為一員大將,努力撐持「台灣文學」的大旗,構築台灣作家的陣地。努力了數十年,到2000年後,鍾肇政終於成為文壇內毫無疑問的耆老級人物。
在文壇內,要成為「耆老」是很不容易的。每個人都會老,但若非有足夠的人望、厚實的經歷和文學上的成績,年齡也不能保證一名老作家受人敬重。鍾肇政在最艱困的年代裡,屢屢突破語言與環境的雙重不利因素,開創了自己的文學風格;再加上他扶助其他作家,串連日治時期文學傳統與新生代本土作家的實績,這使得他成為當之無愧的「耆老」。也因此,在政治禁忌完全解除,「台灣文學」一詞能夠抬頭挺胸、躍上檯面時,鍾肇政便成為毫無疑問的代言人了。
在這個脈絡下,本冊開篇的數篇文章,為何會如此頻繁地提起「台灣文學」,也就非常清楚了。站在2021年回望的我們,或許會困惑:鍾老為什麼這麼執著於這個概念,要把並不複雜的「台灣文學」之意涵一說再說呢?那些說法,在今天的我們看來已經沒有太大的爭議,甚至可以說是沒有新鮮感了,何以鍾老還要反覆提起?這是因為,「台灣文學」這個字的金字招牌,起碼有半邊是他一肩扛起的,那是他一生犧牲奉獻、執著奮鬥了半個世紀的結果,自然萬分珍惜。
如果今天的我們,覺得鍾老的那些說詞有些陳腐,那正是因為有鍾老這樣的作家全力拼搏,才能「化禁忌為陳腐」。這份日常感,覺得「台灣文學」四個字沒什麼不能提起的日常感,正是他們當年不敢夢想,卻在今日完完整整實現的。
您可以特別注意《台灣文學十講》裡,鍾老回顧過去歷程時的語氣。他會不時提起,自己是一名「有問題」的作家,也不斷稱許邀請他演講的武陵高中很特別,竟然找他來講台灣文學。這樣猶疑不定的語氣,正顯示了鍾老那一代作家心中,還是遮蔽著一片戒嚴的陰影。即便在已經解嚴十幾年後,他們仍有點不敢相信:真的嗎?所有禁忌真的都解開,且大家都願意接受我們了嗎?
這樣的猶豫令人心疼。在全世界的文壇裡,恐怕也很難找到第二位語氣如此猶疑的文學耆老了吧。然而,即便猶疑卻還是要說下去,不管反覆幾遍,也要不厭其煩地說下去,這正是鍾老獨有的執著與勇氣。他是在禁錮裡成長的作家,也是那個迂迴迎擊,乃至於擊破了文壇之禁錮的作家。在這一冊裡,我們看到的正是這樣的一位文學耆老:他的經歷與策略極為複雜,但他所持守的信念,卻始終單純明晰,一如一名永遠不老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