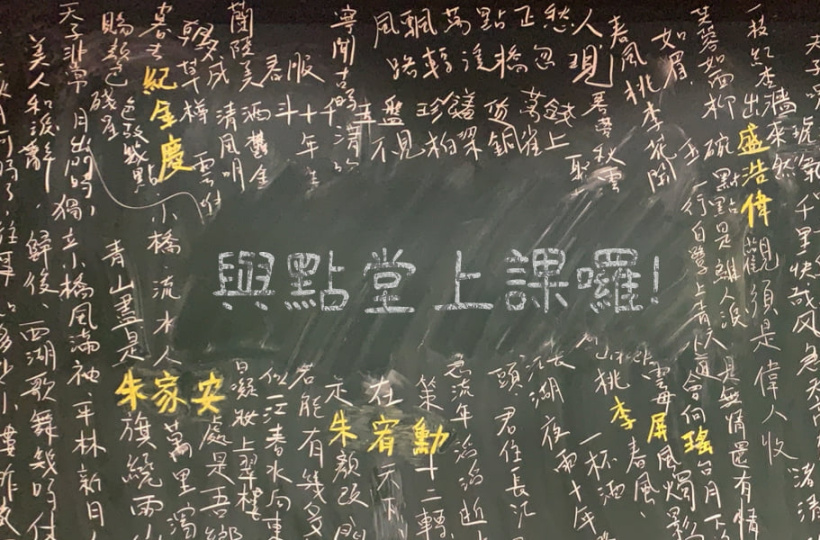本文為《新編鍾肇政全集》解說,收錄於該全集第37冊。
對於一般讀者來說,認識一名作家主要是從他的「作品」開始,也往往就止於「作品」。稍微熱心一點的讀者,還有可能進一步搜讀作家相關的論述、研究。但真的只有非常非常狂熱的粉絲,或者是該位作家的專業研究者,才會連日記、信件這類隻言片語都不放過,不讀遍作家筆下的每一個字不罷休。
您手上的這本《鍾肇政全集》第37冊,正是鍾肇政的狂熱粉絲和專業學者,會讀得興味盎然的寶庫。但且慢著急,這並不意味著一般讀者不可能讀懂這本書。這本書收錄了數百封鍾肇政寫給文壇人士、學生讀者的書信,在外人讀來或許會有種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有時吐露心事、有時商議公務、又有時充滿了生活瑣記,究竟要怎麼閱讀?但其實,只要您理解一些基本的文學史脈絡,便能獲得破譯這許多封書信的密碼,從中讀出字裡行間的曲折。
在接下來的這篇解說裡,我便會挑選幾串重要的「密碼」來講解,提供您閱讀的線索。當然,限於學力,我也沒有能力「破譯」每一封信的脈絡,因此若有缺漏處,也還請對照其他學者的研究來閱讀。
一、鍾肇政的書信有何特別
首先,鍾肇政的書信有何特別,為什麼需要大費周章收羅起來?
對於狂熱粉絲和專業學者來說,任何作家的書信都有價值。但鍾肇政的書信,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價值特別豐厚。第一,鍾肇政從1957年創辦《文友通訊》起,至2020年去世為止,都習慣以書信與文壇人士往來。就算扣除晚年,其活躍期至少有半個世紀。這意味著,鍾肇政的書信集能夠提供半世紀以來,他在文壇交遊的第一手資料,時間跨度之長,幾乎少有作家能夠匹敵。第二,鍾肇政一生最重要的信念,便是「串連本省籍作家、構築本土文壇的陣地」,為了這個信念,他除了自己的創作之外,更投入大量的雜誌編輯、副刊編輯、叢書編輯、文學獎評審等拔擢後進的工作。他所培養或陪伴的作家,幾乎就是台灣文壇的半壁江山。而這些工作,都是靠私下的信件一一醞釀、組織起來的。文壇結構有如蜘蛛網,鍾肇政就坐在蛛網正中心,這使得他延伸出去的書信線有著非凡的文學史價值,不只是研究鍾肇政的人需要這批書信,研究大半台灣作家的人,恐怕也都能在這批書信裡面挖到寶。
簡言之:在台灣文學史上,幾乎沒有另一位作家既像他活躍那麼久、又身居這麼重要的位置、又這麼勤於寫信的。這幾個條件加起來,便使得這本書信集的意義非同一般了。我們既可以在裡面讀到《台灣文藝》、《民眾日報》副刊、吳三連文藝獎、時報文學獎等文學活動的「內幕」;也可以稍微抽離,將這本書當作文學社會學的寶貴材料,從中看到半世紀以來稿費、編輯技術、物質媒介、資訊傳遞方式的變化軌跡。
即使不談這麼「硬」的議題,直接去讀信件本身,我們也可以看到文壇耆老對文學後進的溫煦照顧之情。光以本書所收羅,你便可以見到鍾肇政對每一位後進的耐心與鼓勵。比如張良澤,就算在譯書等工作上一再失誤,鍾肇政仍然願意源源不絕提供機會;或如向陽、呂昱、雪眸、呂興忠、李鴛英、李秋鳳年輕寫作者,鍾肇政都願意在忙亂之中抽出時間,點評他們的創作和譯作。這些人後來各有發展,比如張良澤最後成為學者、向陽沒有如他勉勵的去寫小說而是成為詩人、呂興忠至今仍是彰化地方台灣文學推廣的核心人物……有些頗富潛力的年輕人,最終沒有成為文壇矚目的作家,甚至未能出版作品。但這些都不能掩蓋鍾肇政的熱情;或者毋寧說,從每個人最後的出路各有不同來看,我們更能看到鍾肇政「有教無類」的文學熱情。
二、在文學史的水面下
而在閱讀此書時,若能釐清幾個文學史上的時間點,相信更能增添閱讀的趣味,理解鍾肇政的言外之意。以下便是幾個值得注意的時點。
首先,是1964年,《台灣文藝》創刊。這份刊物是由日治時期的前輩作家吳濁流創立的,宗旨是建立一個台灣本土文學自己的陣地。這份刊物最初由吳濁流組成的編輯團隊主編,鍾肇政已在一定程度協助編務,幫忙約稿、寫稿等事宜。隨著時間推進,鍾肇政在《台灣文藝》的角色日漸吃重。而到了1976年,吳濁流去世,鍾肇政幾乎是《台灣文藝》公認的繼任人選,於是接下主編之職,直到1983年陳永興醫師接手為止。因此,在這段期間裡,凡您讀到鍾肇政煩惱資金來源、煩惱稿件如何安排、乃至於急切聯絡「吳濁流文學獎」評審事宜的信件,都是這條脈絡下的產物。
參與《台灣文藝》這二十年間,可以說是鍾肇政在文壇上最活躍、最忙碌的二十年。除了編雜誌以外,他編了好幾套「叢書」,為台灣本土作家找尋出版機會,羅列老幹新枝。這些成果包含了1965年,於「文壇社」出版的十冊《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於「幼獅書局」出版的十冊《台灣省青年文學叢書》;包括1968年的「蘭開文叢」;包括1979年於「遠景」出版的十二冊《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而在1978年,鍾肇政也應了高雄《民眾日報》之邀,負責主編該報的副刊。若您在書信裡,閱讀到這幾個時間點前後的信件時,可以稍微留心信裡的關鍵字,就能看到鍾肇政為這些文學事業運籌帷幄的痕跡。同一時間,當他不斷在信中提到「好忙」、「好累」的時候,您也可以稍微想像他究竟為了多少事情同時奔忙;而他雖然抱怨忙和累,卻還是抽空寫信勉慰年輕寫作者,更能看出鍾肇政心地之柔軟。
貫穿在這段時間的,有一條直得注意的線索,即「鄉土文學論戰」之後的變化。鄉土文學論戰爆發於1977年,支持官方文藝教條的作家,與支持鄉土文學的民間作家啟動了大規模的論戰。這場論戰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在那之後,官方「反共文學」的文藝教條全面挫敗,民間的「鄉土文學」,無論是左派立場還是獨派立場,反而都獲得了前進的能量。因此,從1977年論戰爆發、一直到1987年解嚴的十年間,文壇上瀰漫著一種「鬆動威權體制」的試探氛圍,許多過去被官方壓制、乃至視為禁忌的話題,都漸漸浮上檯面。
這樣的氛圍,也反映在本集之中。比如在給張良澤的第151信,鍾肇政提及葉石濤將某篇文章給《夏潮》雜誌,指的應該就是葉石濤在「鄉土文學論戰」期間的〈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鍾肇政並不是論戰型的人,沒有參戰,但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他始終關注著事態變化。而在論戰之後,1978年開啟了一波「本土熱」,許多刊物開始對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家如龍瑛宗、張文環、呂赫若、楊逵等人有興趣,紛紛向鍾肇政索求譯稿。比如給張良澤的第189信、190信及其後的信件,便能看出鍾肇政打算有系統譯介這些作家,其成果自然也就展現在前述的1979年《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
不過,氛圍鬆動帶來的,不見得全是好事。在1960年代以降,「左(統)派」與「獨派」兩股意見不同的勢力,都在反對國民黨的大旗底下合作者,大致相安無事。但從鄉土文學論戰以後,兩派隨著勢力的各自發展,矛盾便越來越尖銳了,「統獨議題」的衝突也日漸檯面化。在這段期間,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81年的「邊疆文學論戰」和1983年的「台灣意識論戰」(又稱「台灣結、中國結論戰」),這兩場論戰都可以看見獨派越來越敢於說出自己的想法,並且對本來位居文壇主流的統派和中華民國派發起挑戰。而這些政治意識之爭,便衍伸出「台灣文學界南北分裂」之說,時人一般認為「北」是偏向統派的台北文壇,「南」則是偏向獨派的本土文壇。在給呂昱的第7、第8、第9、第31信,都提到「南北分裂」的關鍵詞,均屬於此一脈絡的產物。有趣的是,鍾肇政似乎認為「台灣文學界南北分裂」是無稽之談,純屬黃春明的造謠——黃春明、陳映真在當時的文學脈絡裡,便是偏向「左(統)派」的一方,您可多方比對相關史料,或可得出自己的判斷。
而也在這樣的氛圍下,1980年代的文壇開始有了稍微不一樣的氣象。在給呂昱的第37、第39、第42信裡,鍾肇政提及自己參與「時報文學獎」和「吳三連文藝獎」的評審過程,並且非常驚喜於該二獎的得獎者,竟是陳映真〈山路〉與楊逵。陳映真是左派,楊逵則是日治時期的老作家,兩人亦都在國民黨統治下,曾因政治案件入獄,十分「政治不正確」。也因為這樣,鍾肇政雖貴為評審,卻沒有把握說服其他評審讓他們得獎。不料就在1983年這一年,兩人雙雙達陣。鍾肇政在信件裡的欣喜之情,其意在此。如果您有興趣,更可玩味上述信件中,關於陳映真〈山路〉的評選過程——為何有評審會突然改變風向,明明投票給陳映真,隨後卻絕口不提?為何所有評審當中,只有鍾肇政願意寫〈山路〉的短評?又為何報紙只敢發布得獎訊息,不敢發表短評?種種細節,可說是意味深長。
三、「留學」與「病院」
最後一部分的「密碼」,是解讀戒嚴時代的文件時,非常好用的一個小秘訣。
在給呂昱的信件中,我們常常會看到鍾肇政提到某人「留學」,或者談及呂昱的「病」及「出院」。比如第48信,鍾肇政提到一名姓柯的人,「也是」留學生,並且有英文文法著作;而在第55信,鍾肇政說呂昱有十五年的留學經驗。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立刻發現不對勁——依照鍾肇政前面四、五十封信的講法,呂昱不是一直在住院養病嗎?怎麼突然又「留學」十五年了?
因為,不管是「留學」和「病院」,其實都是「坐牢」的暗語。這些人,都是在白色恐怖期間入獄的政治犯。
第48信中的柯姓人士,應是指撰寫了《新英文法》的柯旗化。而與鍾肇政長期通信的呂昱,更是從1969年坐牢到1985年的政治犯,在獄中遭到慘無人道的刑求。如果您了解到這一層,意識到「鍾肇政一直在跟一位服刑中的政治犯通信」,再回頭去讀鍾肇政致呂昱的全部信件,相信會有完全不同的感覺。比如,他們交換書籍時,呂昱到底是如何收發這些書籍的?他又是如何在獄中,不斷有創作、評論寄給鍾肇政的?這想必都有外間寫作者難以想像的艱辛歷程。而也因為這一重特殊身份,所以鍾肇政等人在安排呂昱的作品發表時,更別有一番顧慮。比如第23信的這個段落:
李近日來舍,談起「午后陣雨」是他臨時提出來在評會上討論的。他認定「佳作獎」當中有應你一席,不過基於一項考慮,結果是佳作獎都落空了。這個考慮是怕你病中增加非必要的困擾。大家希望你平安熬過病中歲月,平安出院。李也以同樣考慮,表示反對在下期做楊君專輯,不過編輯部好像已經做了,且下期刊出。
如果不考慮「病院=坐牢」的暗碼,這段文字就會顯得莫名奇妙了。為什麼「病中得獎」,會增加「非必要的困擾」?得獎是好事啊!但如果是牢獄之中,又由《台灣文藝》這樣的本土派雜誌頒獎給他,萬一官方認為這是串通聲息,那對《台灣文藝》和呂昱雙方來說,恐怕都會引來麻煩。因此,大家「希望你平安熬過病中歲月,平安出院」,也就是這個意思了。而在同一段最末提到的「楊君」也有類似考量,只是「專輯」終究沒有「得獎」那麼刺眼,所以還是做了。此處的「楊君」,應為1979年因為「美麗島事件」入獄的楊青矗。
這類曲筆,正見證了威權時代的歷史暴力。即便連一系列看似全無煙火氣的、兩位文人談書論藝的信件裡,都埋伏著肅殺之氣。他們看似波瀾不驚的筆調,正凝聚了一生對文學的執著與勇毅。
四、意外
事實上,我是因為一些陰錯陽差的安排,才接下《鍾肇政全集》第37冊的解說的。但當我批閱全書,竟爾感覺到冥冥之中,是有一股力量安排我來細讀這批信件的。我沒想到,我自己竟然在這本書信集裡也有一個角色。
在致陳逸華信件的第6信,鍾肇政感謝陳逸華轉了一篇「朱君」的文章給他。這封信發於2016年1月,比對內容與時間點,我基本可以確定,這位「朱君」就是我。而這篇文章,就是我發表於2015年年底的,描寫鍾老一生文學功業的〈因為鍾肇政不只想到他自己〉。(此文現收錄於拙作《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戒嚴台灣小說家群像》)這麼多年來,我並不知道陳逸華先生曾轉寄文章,當然更不知道鍾老已經讀過拙文——如果知道,我恐怕會為之流汗驚愧吧。
當然,我也就沒有機會當面向鍾老感謝他的謬讚了。但是,過往在文獻裡不斷感受到的「鍾老對後輩的溫煦之情」,我竟爾以這種遲到迂迴的方式,而有了極為直接的個人體驗。我知道眾多文獻築成的「口碑」是假不了的,卻唯有到這一刻,我才終於親身體會其熱力以及重量。
謹以此,見證鍾老一生曲折綿密的文學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