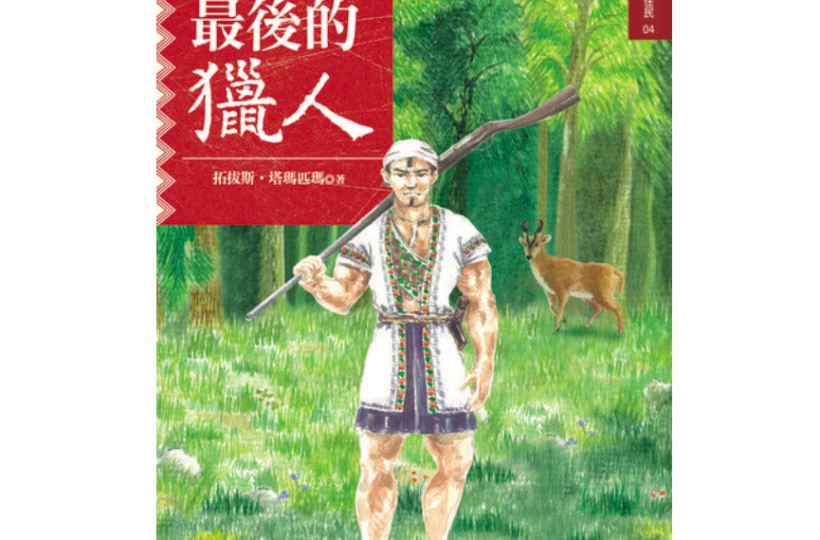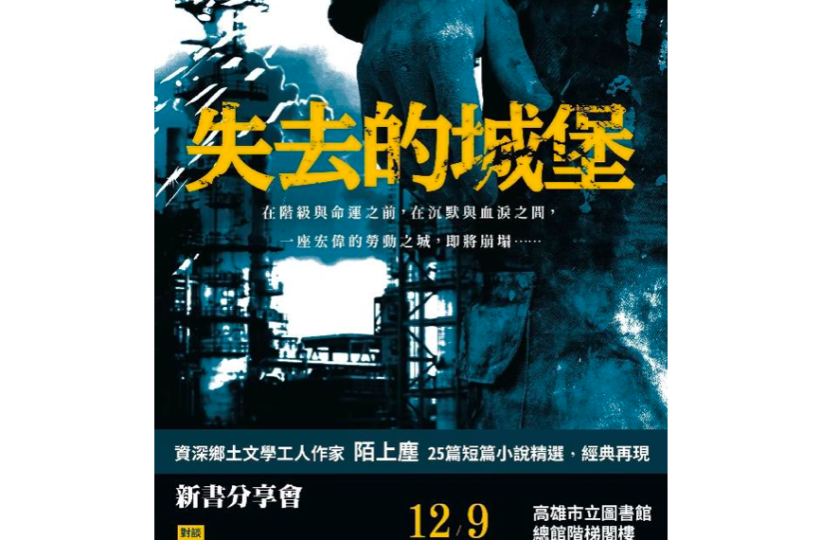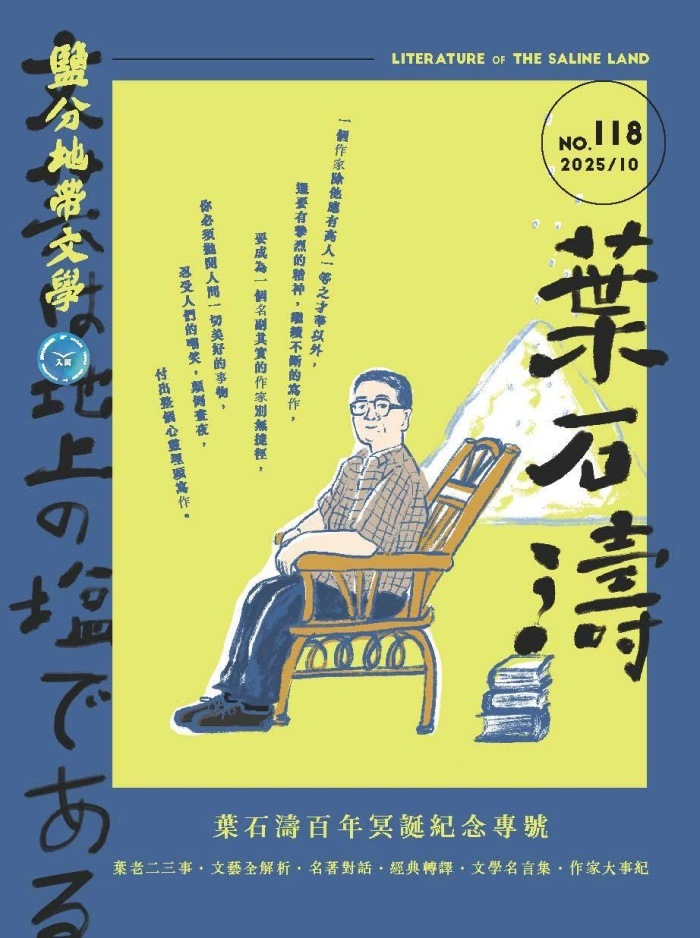在諸種社會議題中,「教育」恐怕是最容易引起激辯的題目之一。新聞媒體上,諸如「體罰」、「霸凌」、「教官存廢」、「升學制度」、「文言文比例」等等問題,總是能夠眾人的爭辯熱情。大家之所以都覺得自己有話可說,因為大家都有「上學」的經驗,也同時在這些經驗裡,投注了種種情感——懷念、受傷、期望、感激乃至於憤怒……如果你是現役學生,恐怕更會有非常強烈的感受。
然而,台灣人並不是一開始就有普遍的「上學」經驗。我們現在常見的現代學校,是在日治時期引入台灣的。因此,文學作品開始有規模地思考「學校」這個問題,主要是從日治時期開始的。以下我們便從不同時期、不同角度,來談談文學作品所記載的「台灣人的上學經驗」。
一、從傳統私塾到現代學校
在日治時期以前,台灣各地已有各種教育機構。詩人黃純青便寫過「奬學七首」的一系列七言古詩,描寫了清領時期的各式教育機構。包含公益目的不收學費的〈義學〉、衙門在大型行政區設立的〈社學〉、聘請著名學者講學的〈書院〉、針對原住民部落的〈番學堂〉,以及劉銘傳為了推進現代化建設而成立的〈西學堂〉等。在黃純青的詩作裡,我們就能看到傳統漢學教育機構與現代學校的差異。〈書院〉一詩描寫的傳統教育,仍以科舉考試為目的,因此強調:「名題上取詩文選,金榜連登捷報來。」但在〈西學堂〉裡,卻已經意識到現代教育的內容遠比傳統漢學複雜,而有了「專修儒學嫌孤陋,智育兼行養達材」的句子。
不過,台灣教育的現代化並沒有在清領時期完成。1895年,日本政府取代清國衙門統治了台灣。日本殖民台灣,最核心的目標是「榨取最多經濟利益」以及「控制被殖民者思想」,這兩個目標都可以藉由「教育」完成:教育可以培養高素質勞工,提高台灣的經濟產能;也可以培養一群意識形態親日,順服殖民統治的人才。因此,日本政府在台灣建立了大量的「公學校」、「小學校」,正式讓「上學」進入台灣人的生命經驗。
對於這種變化,知識份子的看法不一,也自然在文學作品裡留下了不同的看法。比較親日派的如李種玉,他的詩作〈奉迎皇太子殿下恭賦七言古〉(這裡的「皇太子」當然是日本的)細數台灣歷史,把日本殖民者誇讚成救世主。在他筆下,這些救世主的「功績」之一,就是帶來了教育:「學校如林日日興,培養人才為國使。現今世界尚文明,競爭才智相倍蓰。鯤島幸隸新版圖,書見同文車同軌。」有趣的是,他用「書同文、車同軌」的典故,來表示台灣有幸能與日本的體制接軌,雖然姿態極為諂媚,但是……這典故似乎是來自暴君秦始皇呀。
作為對照,也少不了極為反日的洪棄生。他的〈鹿港乘桴記〉描寫了鹿港的沒落,並且將一切都怪罪給日本人。而「教育的現代化」也成了罪狀之一,他是這樣寫的:「蓋藏既富,絃誦興焉; 故黌序之士相望於道, 而春秋試之貢於京師、注名仕籍者,歲有其人,非猶夫以學校聚奴隸者也。」翻成白話就是:鹿港人有錢之後,非常重視教育,在科舉時代成績很好;才不像是日本人現在蓋的學校,是拿來「聚奴隸」的!「奴隸」一詞,自然是批評日本人透過教育體制來控制思想了。
不只久居台灣的文人不滿意,連偶爾來旅遊一趟的中國知識份子梁啟超也聽說了教育體制的差別待遇。他在一系列描寫台灣旅行見聞的文章裡,寫了〈公學校〉一詩。這首詩寫梁啟超在路上遇到一群小學生,問他們在學校裡的狀況。一問之下,梁啟超傻眼:「所授何讀本?新編三字經。他科皆視此,自鄶寧足評。莫云斯學陋,履之如登瀛。」梁啟超精通漢文,首先問的大概是「漢文科」吧?但他沒想到,這群入學好幾年的學生,竟然還在讀《三字經》,程度實在不行。第四句的「自鄶寧足評」是一個典故,接在「他科皆視此」後面,意思是「其他的更爛,問都不用問」。梁啟超的邏輯推理雖然不太對勁(漢文科程度爛,不代表其他科目都爛啊),但他的結論卻是符合時人經驗的:日本人專門開給台灣人讀的「公學校」,教學水準遠遠比不上日本人讀的「小學校」,常常讓家長困惑,為什麼讀了半天什麼也沒學到?
即使有種種不滿,日本人建立的現代學校制度,還是在台灣落地生根了。而在同一時間,傳統文人所主持的私塾、書院等機構,當然面臨了強烈的危機。雖然有部分家長基於文化認同的因素,還是願意把小孩送來念書。但在缺乏政府支持,且現代知識越來越重要的背景下,傳統的私塾、書院逐漸無法與現代學校競爭,學生越來越少。
最鮮明描寫這個過程的,當屬小說家楊守愚。楊守愚的父親是清代的秀才,自幼就熟悉古典漢文;同時他也是「彰化公學校」畢業,對於現代知識也有所了解。因此,他站在新舊知識份子的交界處,對兩種教育體系都有所認識,描寫起學校的「改朝換代」自然更加深刻。他的短篇小說〈捧了你的香爐〉批判傳統私塾教育的死背硬記,教育方法嚴重過時,正可見到他「現代」的一面。
但除此之外,他也用一種嘲諷的、無奈的筆法,寫了一系列私塾教師「王先生」的故事,包含〈開學的頭一天〉、〈就試試文學家生活的味道吧!〉、〈夢〉、〈啊!稿費〉、〈退學的狂潮〉。這五篇小說從王先生自行「創業」,想要在農村裡開一間私塾,並且幻想會有大批學生捧著錢來求學開始,一直寫到人們對私塾完全失去興趣,學生一一退學為止,嘲諷了傳統知識份子面對時代變化的無能。當王先生發現無法靠私塾的收入來維持生計時,還試著投稿給當時剛剛冒出頭的新文學刊物來賺取稿費。然而這些刊物也很窮,王先生不但沒賺到稿費,有時候會被刊物編輯反過來拉贊助,情節充滿無奈的幽默感。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情節顯示了台灣的「古典文人」和「新文學作家」並非壁壘分明,他們有時候根本就是同一群人——就像楊守愚自己同時會寫小說、新詩,但也是一名優秀的古典詩人一樣。
如果說古典文人對現代學校,有比較強的抵抗、競爭之心,那新世代的知識份子,則有著比較正面的態度。最熱切擁抱現代學校的宣言,首推蔣渭水的〈臨床講義〉。這篇發表於1927年的文章,把台灣模擬成一名病人,要為病人開一張診斷書。蔣渭水認為,台灣是「世界文化的低能兒」,並且有「智識的營養不良」的問題。而他開出的藥方非常簡單暴力,第一項就是「正規學校教育最大量」,接著還有補習教育、幼稚園、圖書館、讀報社,也通通都要最大量。簡單來說,他認為台灣需要全面普及現代教育,才能從根本改造社會、改造文化。不過,蔣渭水也對日本人建立的現代學校並不滿意,文章中有「轉居日本帝國後,接受不完全的治療」一句,顯示他對教育還有更高的期待。
二、「上學」是怎樣的經驗?
但是,前一節都是「大人們」在吵教育問題。實際要去上學的學生們,在現代學校裡的經驗又是如何?
關於這一點,小說家們有比較多的著墨。(畢竟會拿著毛筆寫古典詩的人,通常都不需要再去上學了)我認為最精彩的描寫之一,是廖清秀的《恩仇血淚記》。這本長篇小說寫於日本人離開台灣之後,因此比較能夠明白描寫「在學校裡,台灣人是怎麼被欺負的」。小說一開場,台灣籍的小學生主角,和隔壁「小學校」的日本學生吵架,搞得家長、校長、老師雞飛狗跳。一場毫無營養的小學生拌嘴事件,竟然被日本警察上綱到「有反對大日本帝國的思想」,差點有人因此被關。在這一章節的最後,日本籍的校長為了「保護」台灣籍的小學生,竟必須下令老師體罰沒有犯錯的主角,否則日本警察追究起來,很可能就不是挨幾下板子可以了事的。這樣的情節發展,讓我們看到本該追求公平、真理的校園,是如何被殖民地的政治環境給徹底扭曲了。
相較於男性作家多半在意政治、殖民、權力關係,女作家楊千鶴的小說〈花開時節〉,則能讓我們看到「身為女性」的另一重禁錮。小說描寫一群中學女生畢業前夕的煩惱,「花開時節」便是比喻她們此刻的人生正要開花,是應當燦爛之際。然而,生在日治時期的台灣,這一「花開時節」往往成了「花落時節」——因為不管她們在學校裡習得了多少知識、接觸了多少世界潮流、產生了多少高遠的夢想,等著她們的卻只有一個選項,那就是「結婚生子」。楊千鶴透過〈花開時節〉,讓我們看到當時教育體系的虛偽和自相矛盾:號稱要讓人啟蒙的學校,卻在女學生們開了眼界之後,強行把她們塞回古老的婚姻結構中。數十年後,當代小說家楊双子也寫了同題的致敬之作《花開時節》,同樣處理「日治時期、畢業前夕的女學生」,但卻在小說裡添加了女性之間互有情愫的「百合」情節,再一次把「無法選擇花開的樣子」這個主題,從職業進路延伸到了性別認同。
教育牽涉到「未來」,因此不只學生會煩惱進路,師長也往往將自己的願望寄託在下一代所受的教育之上。將「好好讀書」與「翻轉階級」連結起來的觀念,也就不只限於日治時期,更是隨著教育的普及而綿延至今。林海音寫於戒嚴時期的〈要喝冰水嗎〉,是很早觸碰到此一議題的佳作。小說敘述一名不識字的農夫,費盡心力要讓自己的孩子考入中學。農夫認為自己一生所受的一切委屈,都源自於不識字,因此只要孩子能夠讀書,就能夠改變一家人的命運。然而,在小說的最後一幕,農夫陪孩子去考場大考,卻發現自己完全無法跟上週邊家長、學生的話題,最終只能粗暴地以「要喝冰水嗎」的問候切入對話,寫盡了中下階層的卑微與驕傲、屈辱與榮耀。
林海音寫出了「期待學校能夠翻轉階級」的渴望,鍾肇政的《魯冰花》卻以更加細密的長篇,對此命題提出了質疑:如果學校本身就深受成人社會的惡習所染,那我們還能期待它翻轉階級嗎……甚至,學校會不會正是抹煞才華、複製階級的機構?《魯冰花》以天才少年古阿明的際遇,對照平庸但家世良好的林志鴻。最後,學校的「成人們」選擇屈從鄉長的意志,除了才華一無所有的古阿明,也就因此失去了出頭的機會。古阿明的姊姊茶妹在小說結尾的詰問,正是最強烈的諷刺:「老師,天才有什麼用?」照理說,學校應是個看重才華、培養才華的地方,但《魯冰花》所呈現的教育現場卻正好相反,才華成為最容易捨棄的東西。
而最能寫出學校教育的禁錮性質,與人類追求自由之意志的對撞者,當屬郭箏〈好個翹課天〉。郭箏揉和西方的成長小說與港台的武俠元素,寫出了「小混混眼中的校園」。這些小混混雖然不大擅長考試,卻也保留了某種敏銳的直覺,能夠勘破師長所構築的種種虛偽。小說的核心主線是「純潔的消逝」,混混們將在一波一波的人生浪潮中,意識到「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是值得保衛的」。一切都骯髒,毫無例外。而當他們意識到自己也是那「毫無例外」的一部分時,他們就「長大」了。〈好個翹課天〉是台灣文學史上最多髒話的小說之一,卻也是最討論學校教育最深邃的作品之一,展現了文學「出言不馴」、拒絕循規蹈矩的特性——而這往往使文學與學校之間,存在某種微妙的緊張關係。
三、校園是國家的勢力範圍
上述作品,多少還是單純討論「學校」本身的性質,呈現了各種或好或壞的教育經驗。但當國家機器基於各種原因,決定抓緊學校的控制權時,一切就不得不嚴重地扭曲了。如果社會是一個水池,學校就是所有水滴都必須經過的濾心。由此來說,誰決定了這顆濾心的樣貌,誰就可以大規模地改造社會的樣貌。而在校園內活動的人們,當然無可避免地會受到強烈的擠壓。
在日治時期,政治壓力最強的時候,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人為了榨出每一分戰爭潛力,將台灣人改造成能為皇國犧牲愚忠族群,開始推行戰爭總動員的「皇民化運動」,同時扭曲了文學與教育。其中,王昶雄的〈奔流〉被視為「皇民文學」的代表作之一,描寫了一個任職於學校的台籍老師,為了把自己徹底改造為日本人,不但鄙視保留台灣習俗的父母,甚至在父母的喪禮上都不願意致哀。然而,這位台籍老師的種種扭曲行為,卻被小說敘事者理解為某種「努力成為日本人」的決心,幾乎可以說是教育榜樣。無獨有偶,另一位「皇民文學」代表人物周金波也寫了〈「尺」的誕生〉,描寫台籍小學生如何亦步亦趨地跟隨路上偶遇的日本軍人,期盼自己能被誤認為日本人的弟弟,從而獲得認同。
這些作品都顯示了學校如何成為政治控制的節點,使得應當幫助學生「自我實現」的校園,成了誘使學生「自我作賤」的場域。值得注意的是,王昶雄或周金波雖然被視為支持皇民化運動的作家,但他們的作品卻也意外紀錄了台灣人在皇民化運動期間的痛苦。當〈奔流〉的主角們掙扎著「要不要否定自己的家人」、當〈「尺」的誕生〉將小孩患得患失,祈求日本人關愛而不得的場景寫下來時,即便它們沒有挑戰日本殖民統治之意,卻還是暴露了殖民地教育的扭曲性質。
而到了戒嚴時期,學校更長期籠罩在肅殺的氛圍中。戒嚴早期的文學作品,為了避免遭到政治上的迫害,大多如前一節提到的〈要喝冰水嗎〉、《魯冰花》、〈好個翹課天〉一般,專注於「教育本質」的探討,避免挑戰黨國不分的威權體制以策安全。但到了1980年代,社會氛圍逐漸鬆動,許多作家便開始以作品批判校園內的政治黑手。其中,「白色恐怖」和「本土意識」這兩個過去被威權政府壓抑、不能明講的主題,都陸續破土而出。
在小說裡,「白色恐怖與學校」的常見主題有二:一是「失蹤」,二是「跨語」。「失蹤」或可以李渝〈夜琴〉的名句來概括:「為什麼人人都要去不見呢?」在這些故事裡,學校裡那個最溫和、講理、有學問、有理想的完美老師,往往會在帶班一陣子之後突然消失。任憑學生怎麼打聽,大人們通通諱莫如深。許久以後,在某個契機裡,學生才會發現原來完美老師是(或被指控是)共產黨,那時的失蹤其實是無聲的逮捕與滅殺。確實,這些「完美老師」的形象多多少少帶有一些左派思想的影子,他們通常同情弱勢,並且教導學生要平等互愛。此一情節模式的經典代表,當屬陳映真〈鈴鐺花〉。在小說的最後,完美的高東茂老師為逃避追緝,躲藏在學校附近的山洞裡面,成了蓬頭垢面的驚弓之鳥。唯一發現他的兩名主角,卻是在為期三天的蹺課遊蕩之中——這一安排幾乎有某種隱喻的意味:唯有逃離被國家控制的教室,才能看見被國家暴力排除的真相。
相較於「失蹤」這個主題鮮明的政治性,「跨語」則是更迂迴的、文化層面的迫害。所謂「跨語」,指的是台灣人在20世紀的慘痛經驗:在日治時期,被日本人強制要求學習日文;但在日本人離開以後,又被國民政府強制要求拋棄日文,短時間內改換成中文。每一次改換語言,對台灣人來說都是一次文化災難:本來學習的知識系統全面毀棄,一身學問、功夫瞬間歸零。無論是日文還是中文,都並非台灣原生的語文系統,台灣人等於經歷了連續兩次「縫上新舌頭」的痛楚。
學校正是「縫上新舌頭」的血腥之地。透過升學制度與考試,學校排除了不願意或沒有能力改換語文的人,並且獎賞拋棄母語的人。詩人陳千武寫有〈童年的詩〉,描寫日治時期的語言經驗:「陰天覆蓋著幼稚的心靈 / 黑雲懸掛在枝梢 / 不尋常的權勢禁止我們說母親的語言。」值得注意的是,這首詩雖然明確批判日治時期的語言政策,但考慮到陳千武自己也是在戰後被「跨語」經驗傷害的作家,這首詩或許也不無指桑罵槐,同時批判國民黨的意味。
而在小說裡呈現「跨語」經驗的代表性小說家,大概就是郭松棻了。郭松棻的許多小說當中,都會出現「本來是高知識份子,卻因跨語而窮愁潦倒」的角色。中篇小說〈雪盲〉和長篇小說《驚婚》都提到了類似的角色,尤其是〈雪盲〉裡「小學校長」這個角色:他在日治時期,以台灣人的身份脫穎而出,不但能夠講出色的日語,還是一個充滿抱負的教育家;但在國民政府來台後,他只得在中年之後重新學習捲舌音,變成一名庸碌畏縮的普通師長。小說的主角比校長年輕一個世代,幼時無法理解校長的精神痛苦,但等他長大、接觸到戒嚴時期壓抑的社會之後,沒有經歷「跨語」的他,竟然也像是被割去了舌頭那般陷入了沉默。
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學校外的政治氣氛變動,也逐漸滲透到學校裡面。1980年代是黨外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不只「白色恐佈」的記憶被作家召喚回來,「本土意識」的力量也越來越強,從而使小說中的學校成為諸種力量衝撞的場所。頑固守護體制的校園,和源源不絕流入校園的新空氣,終將引爆激烈衝突。林雙不的一系列「發生在學校內的政治小說」,便可一窺戒嚴時期的校園當中,是如何以種族歧視的規格,在壓制所有台灣文化元素。林雙不最著名的〈小喇叭手〉,寫的就是一名中學生與教官發生衝突,最終釀成主角被勒令退學、校內學生為此組織抗爭的事件。而這一切的起因,竟然只是主角用小喇叭吹奏了〈丟丟銅仔〉這首台灣民謠。代表著威權體制、外省文化霸權的教官,不但將台灣民謠斥之為「低俗」,更將這樣的品味判斷上升為政治事件,顯見國家體系對本土意識的「零容忍」肅清政策。
不過,林雙不的小說雖然以學生之被退學告終,但光是「這種故事能被發表出來」,就預示了社會氛圍的鬆解和本土意識的上升。小說中的學生們雖然無力跟教官對抗,但已經不是溫馴待宰的乖孩子,是能夠組織起來、以行動實踐理念、具有政治啟蒙的主體了。無論林雙不所寫的,是小說發表時的1986年的真實情況,還是透過小說對下一代年輕人寄與的期望,都讓我們看到了不一樣的可能性。
這種可能性,很快就彷彿預言一般成真了。就在〈小喇叭手〉發表的隔年,台灣終於「解嚴」,被戒嚴體制封凍多年的民主化進程重又加速了起來。而台灣人「上學」的經驗史,在此又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從日本殖民者建立的學校,到被威權政府壟斷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台灣人的「上學初體驗」並不是太愉快;解嚴之後的學校教育,雖然並非順風順水、一轉身就變得完美,但總算能夠在相對開放的社會體制下,摸索自身應有的樣貌了。
在文章一開頭,我們提到「教育是容易引起激辯的題目」——能夠激辯教育本身,且無須考慮「皇民化」、「反攻大陸」、「中華文化復興」等政治教條,已是過去一世紀以來,艱難獲得的一點進步了。但過往台灣人步履艱難的「上學經驗」並沒有被遺忘,它們已經被銘記在台灣文學史當中,紀錄了每個世代的心靈刻痕。而從這些作品裡,我們也可以不斷獲得啟示:我們到底想要怎麼樣的「學校」,或更重要的——我們到底「不想要」怎樣的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