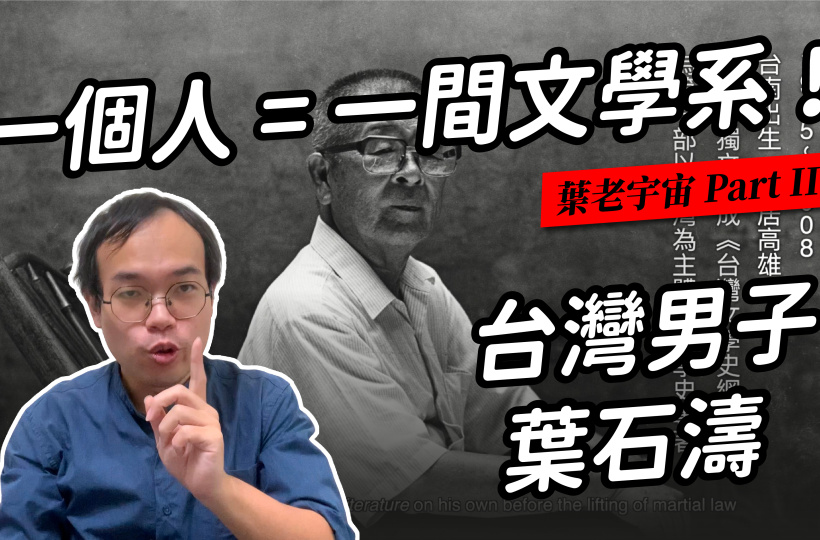這本書收錄十一個短篇小說,前九篇以「簡阿淘」這名角色貫穿,是典型的「短篇連作」。這九篇小說都不長,但每一篇都針對一個威權時代的主題來寫,加起來就又是一份「白色恐怖圖鑑」。這薄薄一百多頁,竟然就把「戰後的台灣知識份子如何陷入羅網」的主題寫完了。
本書開篇的〈夜襲〉,寫的是簡阿淘參與二二八事件當中的一次武裝襲擊,最終慘敗收場;接下來的〈鋼琴與香肉〉,則是描寫國民黨駐軍的不文明行徑,以及隨之而來的本外省文化衝突。這兩篇可以當作「預備階段」來理解,說明白色恐怖前夜的氛圍。
其中〈鋼琴與香肉〉當中,有個非常微妙的段落,描寫國民黨軍隊「借走」國小的鋼琴不還,讓師生無法上音樂課。當學校老師向軍官索討時,卻只得到一連串神秘的微笑:
「事情是這樣的,你們薛師長向敝校借了一架鋼琴,至今還沒有還給敝校。看在教學上的需要,請你們師長把鋼琴還給我們!」簡阿淘理直氣壯地說。
那軍官聽他這麼說,驀地臉上浮起了似笑非笑的怪表情。
「我是音樂老師,請你想想,沒有鋼琴怎能上音樂看?」王秀琴也噘著嘴,毫無客氣的說。
這一次,那軍官差點笑出來,用他那憐憫的眼睛仔細地端詳他們,好似在看某種動物一樣。
「這是借據!」簡阿淘拿借據出來,要他看。
哪裡知道那軍官連看也不看,仍然笑嘻嘻的。
「我知道有這麼一回事。」軍官很客氣的說。
「那麼請你務必把鋼琴還給我們。」
簡阿淘的話好比碰到一堵銅牆鐵壁般,彈回來落了空。
「有一天我們要離開此地時一並奉還。不用著急!」
那軍官似乎可憐起他們來,收斂了笑容,神色凝重地說。
「外省軍官神秘的微笑」與「本省老師天真的說理」適成對比,輕盈地點出了兩造的差異。本省老師越認真,外省軍官的「微笑」就越意味深長:可憐哪,你們這些不懂中國官場文化的傻子⋯⋯
而從〈紅鞋子〉到〈鹿窟哀歌〉等四篇,就是白色恐怖的「本體」了。簡阿淘在〈紅鞋子〉裡面被逮捕,原因頗為荒謬:他為了配合「光復」之後的語言政策,想要好好學中文,到處搜讀「祖國書刊」,結果買到、借到了左派書刊。而給他書的人,還真是左派地下黨人,簡阿淘因此在數年後被羅織入獄。
值得注意的是,葉石濤顯然努力表達那個時代的複雜性:並不所有人都無辜,也並不所有人都有強烈的政治意識。白色恐怖的羅網不分大小,一概掃倒。小說就有麼一段獨白:
我從來不知道這年輕的女孩有這樣堅決的信仰和思想;這和我跟許尚智的情況有些不同。我們以前讀過考恣基和恩格斯的許多經典之作,但是都把這些書當作教養的一部分讀的,而且我們對祖國大陸消除不了陌生感,那祖國對我們而言,只不過是遙遠的異鄉,在實際生活上並不具有任何意義。我們雖然同情被欺壓、被剝削的廣大中國民眾,但是我們更關懷的是如何從陳儀的惡政下求得解放。我們台灣民眾的再解放並不需要和祖國大陸的解放運動取得聯繫。
這一段資訊量很大。至少我們可以看到,這裡真的有信仰左派革命、心向共產黨的人(年輕的女孩),但也有像簡阿淘,將左派書刊當作「教養」(之一)來讀的人。再一次,天真的本省知識份子哪裡知道,在日治時期熟習的「教養主義」——要成為一個完整的、文明的人,就什麼都要讀一點——,在戰後竟然成為罪狀?
而從〈紅鞋子〉開始,我們也陸續看到各式各樣的政治犯。在《流麻溝十五號》裡面驚鴻一瞥的蔡瑞月,在〈紅鞋子〉也出場了一節;〈鐵檻裡的慕情〉寫到了李有邦的太太晏袖芳;〈鹿窟哀歌〉當然就有一批來自鹿窟的農民。其中,〈鹿窟哀歌〉有個非常微妙的段落。當簡阿淘問一名剛被抓進來的農民為何被抓時,農民說:
「什麼叫造反?我不懂。只是農會的陳先生曾拿名冊來叫我蓋章,說是要分配肥料,哪裡知道這名冊竟出了紕漏?在名冊上曾蓋過章的統統進來了。」
一絲絲狡猾的暗影掠過了這樸實的老農夫臉上。簡阿淘知道受過台共訓練的勞動人民,都善於偽裝自己,其實他們都懷有堅定的信念和不可動搖的決心,因為他們窮得一無所有,不怕犧牲自己生命。
這兩段引文極有張力。第一段的農民自述一臉無辜,第二段卻有「狡猾的暗影」——真的嗎?貌似無辜的農民,會不會也有自己的心機、甚至是自己的理想?當我們覺得「政治犯都很無辜」的時候,會不會反而是小看了他們?
除此之外,葉石濤也把監獄裡面的「生態」寫得很有味道。若要論「主題集中」,這本書不如電影「流麻溝」;但要說細節的微妙,葉石濤那種「令人苦笑的妙趣」,恐怕是比一本正經的「流麻溝」更令人印象深刻的。
比如〈牆〉寫簡阿淘一行人被押出牢房,面對一堵磚牆,背後傳來靴子踏地、大隊人馬整隊的聲音。政治犯們低頭一看,牆上竟然處處是彈孔——這豈不是要被槍決了?接著,軍人不斷拉動槍擊,發出「喀嚓喀嚓」的聲音。正當所有政治犯萬念俱灰,在心底向世界告別時,才發現:咦?沒有子彈射過來?
轉頭一看,帶隊進來的特務笑得心花怒放。
啊,原來這些士兵只是覺得嚇嚇他們很好玩^______^
電影「流麻溝」的主線之一,是男女囚犯的感情關係。在〈鐵檻裡的慕情〉中,卻也有著類似、但更「大人」的場景。葉石濤描寫每天早晨,男女囚犯分批盥洗。當女囚走過男囚牢房時,所有男囚都會緊張地貼在鐵檻邊,只為看一眼女性、感覺一絲絲若有似無的香氣。當葉石濤把男囚們悲哀的豬哥狀態寫盡之後,筆鋒一轉,竟也寫起了女囚:
簡阿淘自然也不例外;不過,他跟別人不同,他並沒有真正看到她們。自從被捕以後,他的眼鏡已被沒收不准戴,任他如何睜開眼睛,他所看到的只是朦朧模糊的一團移動的花花綠綠的色彩而已。女犯似乎也知道,她們會給男犯帶來衝擊的吧,她們在早晨這一刻,刻意打扮得花枝招展,盛裝而出:也許她們也渴望跟跟男犯有某種心靈或肉體的接觸吧?
我不知道女囚是不是這樣想的,但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這裡的心理描寫實在很精微。如果沒有這段,男囚的觀看就只是純粹的生理衝動;但加上了女囚的「知道會帶來衝擊」,竟然讓這個動物園猴子(這是葉石濤的原話⋯⋯)一般的性吸引場景,一轉成為相濡以沫、互相慰安的默契。
而在整個系列裡,我最喜歡的當屬〈吃豬皮的日子〉一篇。這篇和〈邂逅〉、〈約談〉等三篇,寫的是出獄之後的「餘生」。
〈吃豬皮的日子〉一開始看起來跟白色恐怖毫無關係,只是簡阿淘整天去路邊攤喝酒、吃黑白切的描述而已。然而在某個晚上,當簡阿淘再次光顧路邊攤時,發現攤上竟然多了一名陌生少女,一看到他就開始跟老闆咬耳朵。簡阿淘一開始不以為意,但發現今天的老闆似乎特別豪邁,酒一杯一杯斟、湯一碗一碗加(而且還加滿配料)。等到要結帳時,老闆竟然只收了1/4的錢,並且堅持要那名少女,也就是老闆的女兒送他回家。
簡阿淘莫名其妙被款待一頓,跟少女無言走了一程。忽然之間,少女開口了:
「老師,您家還在嶺後街那一條巷子盡頭嗎?」
「老師?妳是?」我驚出一身冷汗來,酒也醒了一半。
「您難道忘了?我是葛秋霞,六年孝班您班上的,那年學校開學不久,您就沒來上課了。我是班長,所以跟林校長到處打聽,才知道您在看守所坐牢,您不是收到毛巾、香皂、牙刷之類的東西嗎?那是班上同學出錢買來送老師的。」
秋霞用黯然的聲音說起前塵往事來,這觸到了我心裡的傷痕,我呻吟起來,如果她不在,我一定放聲大哭無疑。
「我想起來了,我的確收到了你們所捐的東西。」我心裡喃喃的說,這些東西一直在我身邊,用壞了我也沒丟棄,一直到出獄還帶回來的呀,可是我並沒有說出來。
看到這一段的時候,我雞皮疙瘩都起來了。我們直到這時才知道,簡阿淘前面整天吃吃喝喝,其實是在出獄之後,萬念俱灰之下的自我麻痺——偏偏他又很窮,買醉也只能靠豬皮油豆腐米酒的路邊攤。這一切理當被酒精埋沒的記憶,卻全都被召喚回來了:原來當時那小小的善意,是來自學生;原來看似落拓的老師,還一直珍惜著這些無名的關懷。只是,他們到現在才越過重重時光,發現「原來是你」。
而在小說的最後,少女講了一番老派卻激昂的話,鼓勵老師東山再起、不要繼續墮落了:
「老師,我爹說,您酒喝得太兇,而且現在的工作也不合您的身分,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應該另謀途徑才是。」秋霞悄悄地說,但那語意卻是毅然而堅決的。
「另謀途徑?」我有如被空氣槍打中的鴿子楞在那兒發呆了一陣子。
「是啊,人應該賺合乎自己身分的錢,譬如我爹,本是下賤的藝人,是個江湖客,賣豬皮湯謀生;他的錢賺得心安理得,我哪,是窮苦人家的女孩兒,幫傭賺錢也不辱沒了我,但是老師,您不同,您應該往上爬,您不應該如此墮落下去,我爹說,老師您太沒出息了。」
我淚眼模糊地望著那下弦月,久久說不出一句話,然後跟秋霞分手,決然往前走下去,第二天開始,我不再去上臨時工友的班了。
小時候讀到這段,覺得結尾略微可惜,前面那麼動人的情意,怎麼又落入「成功」的世俗窠臼裡呢?但這次再讀,我卻有了完全不一樣的想法。《台灣男子簡阿淘》是一本半自傳式小說,有許多情節是和葉石濤的真實人生很貼。如果這段情節也是「有所本」呢?
那,我們或許看到的,是葉石濤「重回文壇」的關鍵場景吧。1940年代的葉石濤,是在日治時期文壇活躍的天才少年,一直活躍到1948年左右。1951年,他因為白色恐怖入獄之後,雖然「只」關了三年,但隨後卻有十多年時間四處謀生,絕跡於文壇之上。
是什麼讓他決定在1965年重回文壇,即使他親身體驗過「只是讀書寫字就被關」的牢獄之災?
是什麼讓他在1965年下定決心,要甘冒禁忌寫台灣文學史,並且一路熬到1987年,真的在解嚴前夕,把《台灣文學史綱》寫出來?
是什麼讓他在1996年,台灣社會對白色恐怖還餘悸猶存之時,就寫了這麼一部完整的《台灣男子簡阿淘》,為我們留下第一手的「白色恐怖圖鑑」?
是不是真有一個路邊攤的老闆、是不是真有一個敬愛他又罵醒他的少女,我們不得而知。但小說裡的這句話,或多或少是他自我鞭策的心聲吧:「您不應該如此墮落下去。」
真實世界的葉石濤,是一個三天兩頭抱怨文學不受人重視、賺不到錢又會被政府找麻煩的作家。然而即便如此,他卻從來沒有放棄過文學,還是一筆一劃寫到了二十一世紀。也許,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答案:那是他的自我解嘲,也是他的勇氣之源;是他做小伏低以求苟全,卻始終沒有拋棄的作家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