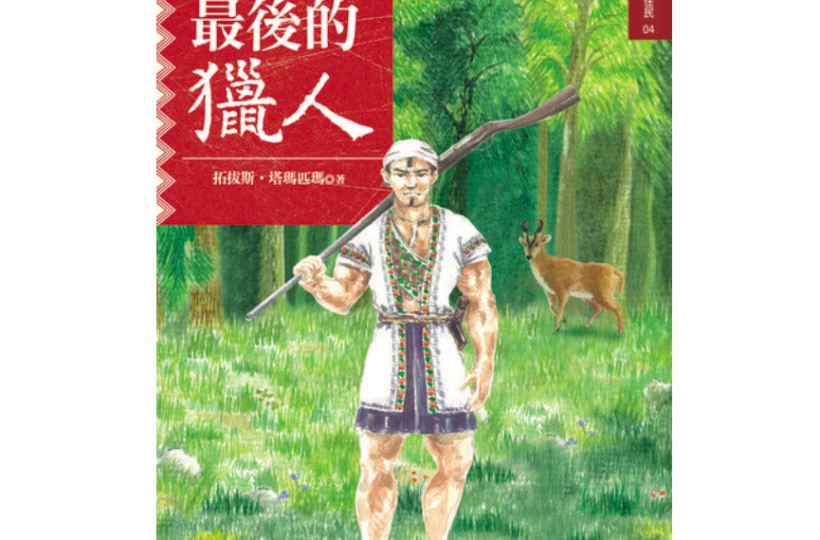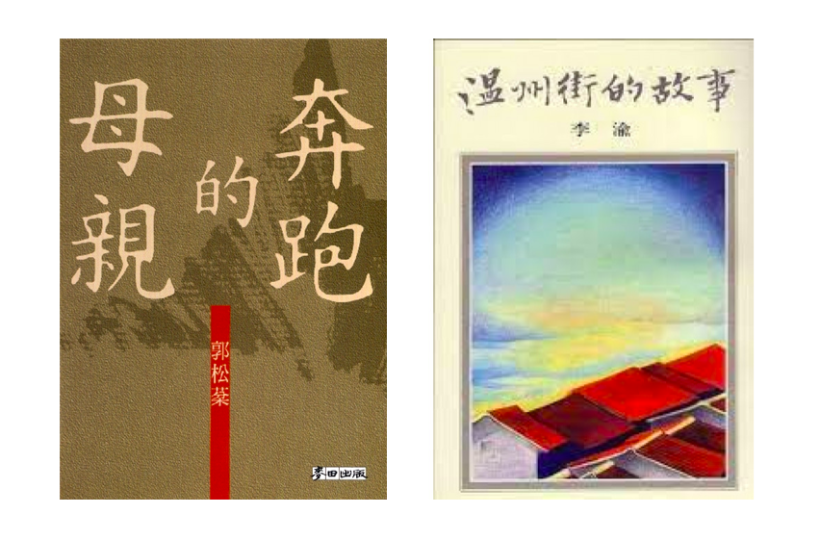大多數人,可能是從歷史課本和國文課本認識賴和的。歷史課本裡面的賴和,會被放在日治時期「新文化運動」的部分,讚揚他以行動和創作抵抗日本殖民。國文課本裡的賴和也差不多,會與他的名篇〈一桿稱仔〉一起談,概念上也不脫抵抗日本殖民者的說法。在〈一桿稱仔〉的最後,小說主角甚至悲壯地以命換命,犧牲自己而殺死了「一個夜巡的警吏」。如果學生能夠融會貫通的話,應當會立刻想到:沒錯,歷史課本也說過,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徵之一,就是警察政治。所以殺死日本警察,實際上就是反抗日本殖民的象徵。
這些概念,將賴和塑造成一位勇敢抵抗殖民者的鬥士。甚至在比較老派的老師口中,還會簡化為「抗日」。這種說法不算錯誤,賴和確實是當時戮力與殖民者拼搏的知識份子之一;但如果只用這個概念去理解賴和,就有點太可惜了。事實上,我認為賴和最耐人尋味之處,就在於他其實充滿了矛盾、猶豫和困惑,有時甚至自嘲嘲人。他並不像課本所描述的那麼立場堅定,反而更像是任何一個我們都會認識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只要我們跳脫課本的視野,實際讀幾篇他的作品,就會立刻看見一個意料之外的賴和。沒錯,賴和常常寫警察,可是他也並不是永遠將警察當作唯一的罪惡來源。在某些作品裡,日本警察之所以能夠作威作福,實際上竟有台灣人自己的默許與暗助。最鮮明的例子要數〈惹事〉這篇小說了。〈惹事〉的敘事者是一名桀驁不馴的台灣青年,在故事中段,他目睹了日本警察誣賴一名寡婦的惡行,決定聯合鄉親們反抗警察。怎麼反抗呢?青年想到一計:再過幾天,這名警察的上司將到本地來開會,屆時只要鄉親們團結一致,通通不要出席,就能讓負責的警察大出醜。而如果上司查問起來,青年就可以趁機暴露警察劣跡斑斑、不得人心的事實,讓上司出手整治。台灣人對抗日本人是很困難,但讓日本人來修理「業績不佳」的日本下屬,那可就說不定了。
青年四處奔走,詢問鄉親是否願意支持這場「和平抗爭」:只要不出席會議就好了!本來青年對此事能不能成,是不抱太大期望的,沒想到鄉親們竟然紛紛答應,甚至還有人誇獎他的計劃。受此鼓舞,青年就更努力收集該名警察的不良紀錄,打算來個一擊必殺。到了開會那天,青年從外地辦完事回來,便趕去會場,想看看這一陣子四處奔走的結果。他抵達會場,看到的卻是:
行到公眾聚會所前,看見裡面坐滿了人,我覺得有些意外,近前去再看詳細。
我突然感著一種不可名狀的悲哀,失望羞恥,有如墮落深淵,水正沒過了頭部,只存有朦朧知覺,又如趕不上隊商,迷失在沙漠裡的孤客似地徬徨,也覺得像正在懷春的時候,被人發見了秘密的處女一樣,腆靦,現在是我已被眾人所遺棄,被眾人所不信,被眾人所嘲弄,我感覺著面上的血管一時漲大起來,遍身的血液全聚到頭上來,我再沒有在此立腳的勇氣,翻轉身要走,這候忽被那保正伯看見了,他便招呼我:
「進來!進來坐吧,你有什麼意見?」他們正通過了給大人修理浴室及總舖的費用,各保的負擔分費,尚未妥當,這保正伯是首先和我表同意的……
結果,每一個答應他不出席的人,最後通通都出席了。由此可見,前面的承諾與誇獎,通通只是哄他的。這樣就算了,首先答應他會參與行動的保正伯,竟然若無其事地招呼他進來發言;而他們此刻正在討論的,還是如何攤派費用,幫警察大人修理浴室和房間……
用現在的話來說,〈惹事〉寫的其實就是「少年人不知社會事」。他一腔熱血要為鄉親爭取公道,但鄉親卻只是和他打太極,既不明確否定他,卻也從未支持他。而在這些懂社會事的大人眼中,他們還覺得自己是在保護這個不懂事的少年人。賴和在這篇小說裡點出了台灣人缺乏道德勇氣、以圓滑世故為尚、卻絲毫沒有是非觀念的一面。作為一名對抗日本殖民者的「鬥士」,青年所感覺到的羞辱與悲哀,又何嘗不是賴和感受到的羞辱和悲哀?你親冒矢石在前線奮鬥,而你為之奮鬥的群眾卻是如此愚騃不靈,這麼說起來,殖民地社會的醜惡,又豈是日本警察單方面的責任而已。
如果說〈惹事〉批判的是普羅大眾,那賴和的另一篇小說〈赴會〉,就是把槍頭調轉過來,對著賴和這樣的知識份子自己了。〈赴會〉的故事沒有〈惹事〉那麼完整,基本的架構非常單純:敘事者「我」是一名社會運動者,正準備搭火車到某處開會。開什麼會呢?從行文的暗示來看,應該就是去開「台灣文化協會」的會議——這正是歷史課本一定會提到的,透過文化來對抗日本人的代表性組織。
在火車上,敘事者不斷偷聽旁邊的乘客說話。那時正是北港進香時節,許多農民背著金紙、線香上車,顯然就是要去拜拜的。敘事者作為知識份子,對於這種迷信的行為不能苟同,更因此痛恨起「讓農民必須迷信才能活下的、令人苦痛的社會」。這裡的心思轉折,與馬克思的名句頗有類同之處:「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要求拋開關於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開那需要幻想的處境。」總之,這位憂國憂民的敘事者看到這一切,更加堅定了「赴會的勇氣」。然而當他開始思考,到會議上該怎麼發言時,徒勞感就湧上來了:
我靠近車窗坐下,把眼光放開去無目的地瞻望沿途風景,心裡卻在想適纔所見的事實。會議時將用何種題目提出?迷信的破除嗎?這是屬於過去的標語。啊過去,過去不是議決有許多種的提案,設定有許多種標語,究其實在有那一種現之事實?只就迷信來講,不僅不見得有些破除,反轉有興盛的趨勢。啊,這過去使我不敢回憶。而且,迷信破除也覺得不切實際,使迷信真已破除了,將提供那一種慰安,給一般信仰的民眾,像這些燒金客呢?這樣想來,我不覺茫然地自失,漠然地感到了悲哀。又回想我這赴會的心境,不也同燒金客越北港進香一樣嗎?
這可能是日治時期小說中,知識份子自我反省最深刻的段落之一。這段的前半,敘事者意識到了過去推行的文化運動是徒勞無功的,迷信並未破除,反而越加興盛。接著,他又反省到:就算破除了又如何呢?這些民眾要是失去信仰,還能怎樣活在這苦痛的社會?最終第三層的反省,是銳利的自我譏刺:如此一來,「我」這樣一個去「赴會」的文化人,又跟那些北港進香客有什麼兩樣?我們同樣都是抓著一個不可能實現的信念,一次一次做著徒勞無功的事情。相信媽祖跟相信「文化」,又有什麼不同呢?在這個段落裡,賴和竟然將被視為迷信的傳統信仰,與致力於破除迷信的文化運動等量齊觀,反省力道極為深沉,甚至令人觀之不忍——都已經努力到這樣了,賴和仍然自譴做得不夠、坦承自己忙然而不知方向。
這樣的賴和,還能說是一名「抗日」的知識份子嗎?當然是,但也不只是。純粹地對抗、反對一股政治勢力,口頭說起來很簡單,實際投身卻必然陷入千絲萬縷、互相牽制的社會網路裡。賴和那一代人,是台灣第一代「現代知識份子」,也是第一個知道什麼是「社會運動」的世代。因此,他們也是第一代嚐到「運動傷害」滋味的台灣人。賴和的複雜性,就在於他不只寫下了對抗的意志,也寫下了負傷、無奈與挫敗。
唯有在這樣的認知下,我們才能意識到賴和筆下正反交織、樂觀與悲觀交纏、明知不可為卻還要鼓起餘勇以激勵同伴的糾結。在賴和未完成的自傳式小說〈阿四〉裡,他描寫了一名幾乎跟他一模一樣的知識份子,站上講台對著參加社會運動的群眾演講。那一瞬間,阿四的思緒是這樣的:
阿四看這種狀況,心裡真不能自安,他想大眾這樣崇仰著信賴著期待著,要是不能使他們實際上得點幸福,只使曉得痛苦的由來,增長不平的憤恨,而又不給與他們解決的方法,準會使他們失望,結果只有加添他們的悲哀,這不是轉成罪過?所以他這晚立在講台上,靜肅的會場,只看見萬頭仰向,個個的眼裡皆射出熱烈希望的視線,集注在他的臉上,使他心裡燃起火一樣的同情,想盡他舌的能力,講些他們所要聽的話,使各個人得些眼前的慰安,留著未來的希望,把著歡喜的心情給他們做歸遺家人的贈品。
這是值得細細品味的段落。社會運動者的目標,正是鼓舞群眾一起對抗不公義。可是,像是阿四這樣的社會運動者,其實心裡並不認為「敵人」是可能打倒的,這要怎麼辦呢?這豈不就是「曉得痛苦的由來、又不給他們解決的方法」?阿四糾結半天的結論是:那就不要把這殘酷的真相說出來吧。要說出樂觀的話,要給出一切仍有可為的暗示。這些樂觀的話語並不能撼動現實,但至少能讓人們「得些眼前的慰安,留著未來的希望」。悲觀的、苦澀的心思,就留給自己吧。
因此,當我們在賴和的其他作品裡讀到那些激昂的、奮鬥的話語時,恐怕不能單純讀作「賴和是這麼想的」——比如散文〈前進〉:「在這黑暗之中,竟也沒有行不前進的事,雖遇有些顛蹶,也不能擋止他倆的前進。前進!忘了一切危險而前進。」或新詩〈南國哀歌〉:「兄弟們來! / 來!捨此一身和他一拚! / 我們處在這樣環境, / 只是偷生有什麼路用 / 眼前的幸福雖享不到, / 也須為著子孫鬥爭。」從現在的文學觀點來看,或許會覺得這些句子流於口號、缺乏曲折的文思。但是,只要我們理解賴和的心緒,那就會意識到:那是因為賴和把曲折都留給自己,而試圖把勇氣帶給他人。賴和未必是這麼想的,但他確實是決定要「這麼講的」。
賴和懷抱了不為人知的苦澀,即便在最自謔的作品裡,他也沒有講出自己最深刻的悲觀。然而,他的這份心思,卻被他的好朋友楊雲萍捕捉了下來。1943年1月31日,賴和逝世。就在他逝世前幾天,楊雲萍前往探望。賴和那天精神很好,他們談了很多關於詩的話題,談了《民俗台灣》上面有趣的文章,還談了魯迅跟連雅堂。本來楊雲萍很擔心他的病況,談著談著竟然也忘了他是個病人。然而,看似心情頗佳的賴和,卻突然坐起身來,用左手壓著疼痛的心臟,激動地說:
「我們正在進行的新文學運動,都是無意義的。」
這是課本不會告訴我們的賴和:被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他,始終認為台灣新文學不會成功,終將被日本殖民者抹滅。一旦跳脫了課本的框架,我們也才能意識到,賴和是如何堅韌地,花費他後半生十數年的精力,在做一件他根本不抱希望的事情。
現在的我們當然知道:賴和的預言是錯誤的。但這並沒有什麼關係。因為真正有份量的不是正確,而恰恰是賴和所做的一切——在複雜的、絞纏的世界裡,選擇一件自己相信的事,然後不抱期望地一直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