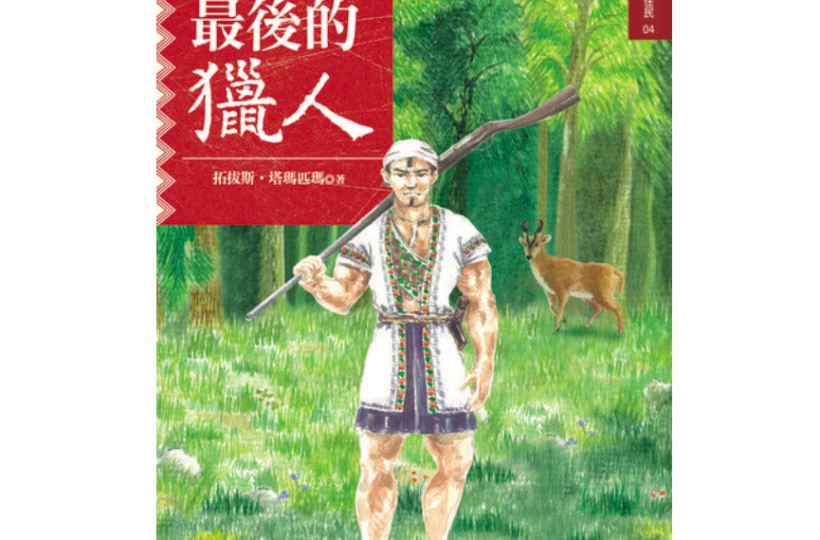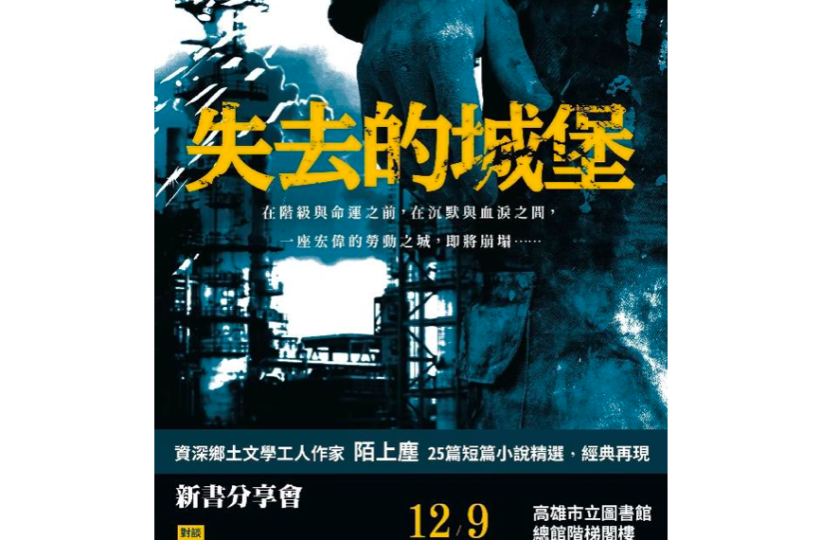本文是我受邀到「好書來一手!」節目,談「台灣文學裡的戰爭小說」之全文。原文發表於「好書來一手!」電子報:
https://booksonehand.substack.com/p/ft-5dd
1、《金排附》〈金排附〉:體制沒告訴你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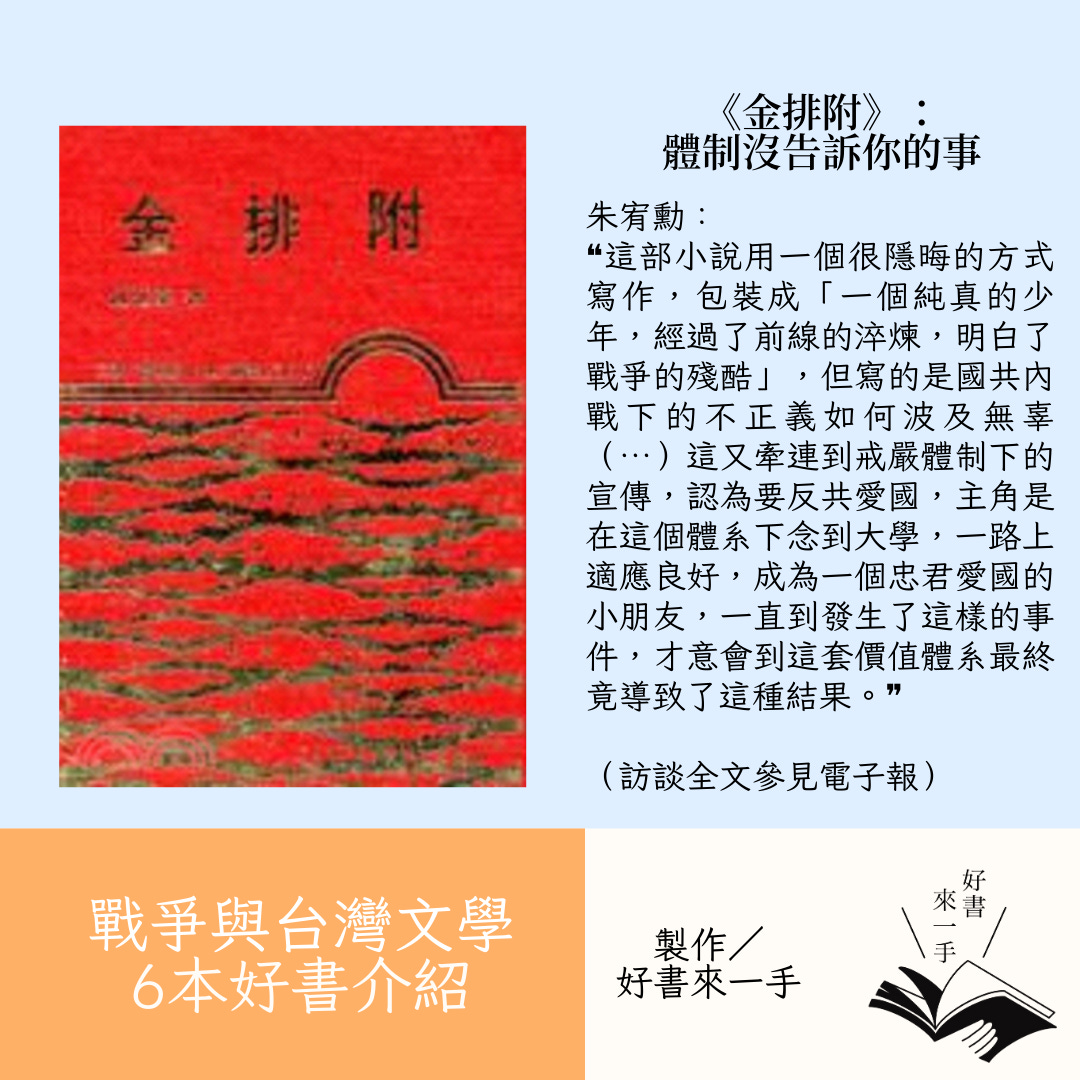
這部作品寫的是外島,他在「戰爭前線」遇到了什麼?
〈金排附〉的主角是一名到了前線的大專兵,他是軍官,但軍中有一位老經驗的士官長,士官長覺得「這個菜兵什麼不會,在那邊指揮我」,而大專兵則又想要證明自己。
小說的高潮是一個驚悚的場面:大專兵發現一艘船停泊在海上,很像共軍在監視,士官長叫大專兵不要開火,也不想多做解釋,但大專兵最後仍決定開火,士官長聽到槍聲趕來時,叫他拿望遠鏡看,這才發現他們射擊的是一艘漁船,已經有幾個漁夫掛在船邊。
小說最後一個很有趣的細節,是這位大專兵情緒崩潰,在大哭的時候,士官長抱住他說:「幾十年來,我不知道打死多少老百姓呢。」等於跟他說「你會習慣的」,這是我覺得最有力道的:士官長之所以不要打,是因為他自己也殺過。
這部小說用一個很隱晦的方式寫作,包裝成「一個純真的少年,經過了前線的淬煉,明白了戰爭的殘酷」,但寫的是國共內戰下的不正義如何波及無辜。等等會談的陳千武《獵女犯》中,面對無辜的人因自己受害,主角或許還能說「是日本人要我做的」,但這部小說中,反而是旁邊的人叫你不要做,但你想要證明自己──而這種想要證明自己的情緒,這又牽連到戒嚴體制下的宣傳,認為要反共愛國,主角是在這個體系下念到大學,一路上適應良好,成為一個忠君愛國的小朋友,一直到發生了這樣的事件,才意會到這套價值體系最終竟導致了這種結果。
而這也是戰後新世代的本土作家才寫得出來的東西:本篇作者鍾延豪的父親是鍾肇政(按:小說家,著有《魯冰花》等作品),文學圈裡面都知道他們的政治立場非常本土,跟國民黨一定有距離;但即使是這樣的立場,鍾肇政這一輩人的戰爭經驗是二次世界大戰被抓去挖戰壕,所以這種在外島前線的狀態,是到鍾延豪這一代才寫得出來,這部作品一出,當時本土文學的圈子很驚艷。鍾延豪這一代,同樣批判戒嚴體制,可是對於如何加以理解、與之周旋,卻有新的看法。
如果跳出「戰爭」這個立即的主題,更廣泛地談對戒嚴體制的思考,台灣文學界有怎樣不同的處理方式?
最直接的比如像鄭清文和李喬,舉例來說,鄭清文的寫作非常「清淡」,幾乎都寫新莊的小人物,但會在關鍵的地方切入政治;比如在《紅磚港坪》中有一篇,寫了一位女性瘋狂浪費食物,故事到最後才跟我們說,因為老人家相信浪費食物死後會墮入餓鬼地獄,而她的兒子是因為白色恐怖入獄、在獄中拒絕食物,她於是開始浪費食物,為了在地獄能與兒子相見。
更整體而言,當時的文壇,以政治立場可以區分為四個象限:
第一個象限是最官方、反共的系統,比如余光中,以及朱天文、朱天心姊妹,和她們的父親朱西甯。
第二個象限是所謂現代主義,比朱西甯再年輕一代,政治立場上未必與官方有直接衝突,但在美學上不想要跟官方走得那麼近;這一支表面上看起來都沒有政治立場,但現實上可能有,他們的東西會比較晦澀,為了迴避政治,會經常往內心世界看,比如白先勇、王文興、七等生都屬於此類,白先勇的政治立場明顯比較親國民黨,但七等生就比較撲朔迷離。
第三、四象限經常被籠統地合稱為「鄉土文學」,但其實可以分成兩派:一派是鍾肇政等人,他們的意識形態比較親本土,通常筆法也比較素樸。另一派是左派的系統,比如陳映真、黃春明,他們的批判會針對資本主義以及美國、日本,與國民黨有距離,但大多都是統派。不過不論是本土的鄭清文,或是左派的黃春明,也都有借用現代主義的手法。
但也有在這個分類之外的作家,比如郭松棻和李渝,他們長年在美國,另有他們的邏輯;他們意識形態偏左,但寫法又偏現代主義,而因為實在太強,所以在台灣文學的討論中都一定還是會提到他們。
2、《山女:蕃仔林故事集》〈哭聲〉:活下去的理由

這部作品也是談從軍,但世代跟重點都不太一樣,可不可以請您介紹一下這部?
這一篇講到一個特別的時刻:「志願兵」要被徵召上戰場了,在出發前很短的一兩天,你的心理狀態是什麼?
小說設計的情境是這樣的:苗栗的一座山頂,晚上會傳出哭聲,是一個村人都不敢去的禁地;村裡兩個年輕人要被徵召去打仗,覺得自己死定了;這兩個小伙子想,反正都要死了,不如去看一下上面有什麼東西。
整部小說中,村人與他們兩人說話,都欲言又止,不知怎麼跟他們講話:說「祝你好運」也不對,要同情你也不對,所以就會出現村人說出「這兩天好好把握機會」這種很尷尬的畫面,描繪得非常生動。
而小說後段最厲害的地方是,他們上山之後,竟然發現了一個東西,帶下山就可以發大財,可是因為要出征了,帶下山也沒有用,兩人於是約定要活著回來,一起把這東西帶下山──兩個已無生趣的年輕人,突然有了一個要回家的理由,而且成為他們的某種默契,於是從戰爭的殘酷,拉出了一個「為什麼要堅持下去的信念」,是很漂亮的短篇。
有趣的是,後來李喬寫了長篇《寒夜三部曲》,〈哭聲〉的這兩個主角,在第三部《孤燈》裡面再度出現,可是那個發大財的象徵物不見了,這裡可以去對照:為什麼把那個象徵物拿掉了?比對一下,會看到作者很多態度上的變化,在〈哭聲〉裡可能還有的溫暖,在長篇裡面消失。
李喬自己沒有經歷太平洋戰爭,他是帶著什麼樣的動機寫這段故事?
李喬他們那一代人(按:李喬生於1934年)寫作時,有一個「搶救記憶」的急迫感,他們面對的不是「歷史課本沒講清楚」,而是「歷史課本根本沒講」,焦慮感因此更強烈。
為此,他在寫《孤燈》的時候,他作了很多功課把軍隊移動的相關細節,做了十八張圖表,再作濃縮,最後剩下兩張筆記。這樣的寫法很麻煩,麻煩的不是找資料本身,而是人之常情,找到資料就會想用,所以小說就容易變得臃腫,但李喬很會拿捏,知道資料是資料,關鍵在於如何提煉,提煉的其中一步,就是先寫出短篇小說。
除了搶救記憶之外,李喬寫日治時期也是一種迂迴的策略,因為直接寫國民黨統治下的事情,強調台灣人的主體性很危險,但書寫日治時代時,「對手」是日本人,再去強調台灣人,看起來很像在抗日、反殖民。連結到後來整個《寒夜三部曲》的主軸,也是「台灣人是如何煉成的?我們如何一層一層地認識到自己是誰?」,逐步發現自己不是日本、卻也不是中國的過程。
3、《獵女犯》〈獵女犯〉:台灣人的「無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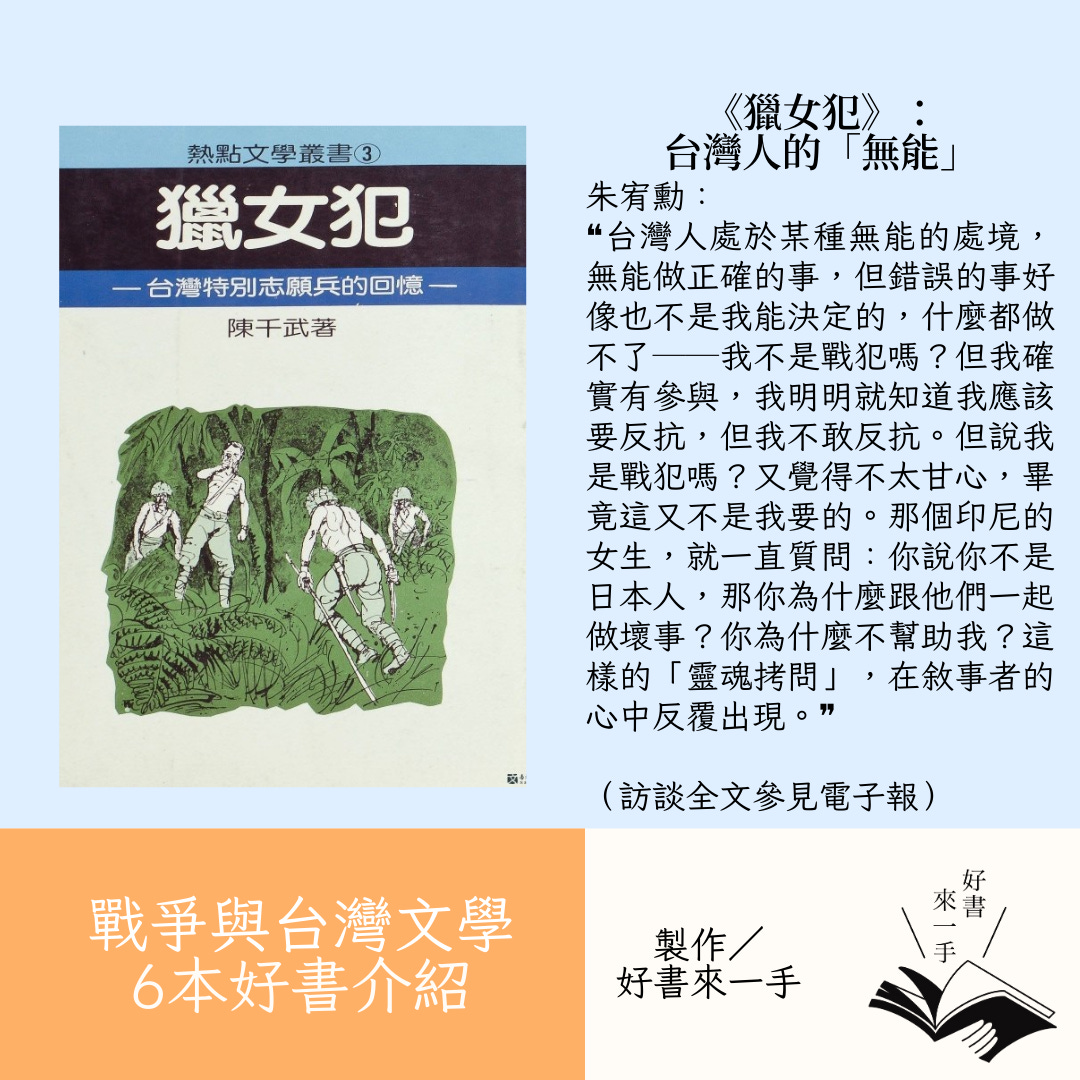
這部作品寫的也是台灣人參與太平洋戰爭,這部作品的獨到之處在哪裡?
我覺得這部是台灣本土的作品中,最適合改編成電影的作品之一。這部作品中,我們跟著一名台灣兵的視角,看他被日本人命令去抓捕慰安婦。
小說中出現意外的族群交會:照理說,台灣士兵與印尼女子應該沒有關係,但他卻發現他跟其中一位語言可以互通,因為那位女子是福建移民與印尼當地人的混血。
透過讓台灣人與印尼人產生連結,小說把台灣人放置在亞洲的脈絡裡面處理;更廣泛來說,這本書中與台灣人同行的,除了壓榨台灣人的日本兵,還有一樣被壓榨的沖繩兵,而到了印尼、新加坡又會遇到當地人,在這裡,有一個把台灣重新鑲嵌回亞洲的強烈意圖──台灣是亞洲的一部分。
〈獵女犯〉這一篇最後,長官命令士兵都要去嫖妓,主角選擇了這位印尼女性,但決定不侵犯她,就在房間待滿十五分鐘,對方反而因為這個舉動而感動,願意跟他發生關係,但他卻感到自己在生理上、心理上都是「無能」的,於是在小說的結尾裡說:「我這無能的獵女犯」,該怎麼辦呢?
這個無能的象徵意義相當複雜:台灣人處於某種無能的處境,無能做正確的事,但錯誤的事好像也不是我能決定的,什麼都做不了──我不是戰犯嗎?但我確實有參與,我明明就知道我應該要反抗,但我不敢反抗但說我是戰犯嗎?又覺得不太甘心,畢竟這又不是我要的。那個印尼的女生,就一直質問:你說你不是日本人,那你為什麼跟他們一起做壞事?你為什麼不幫助我?這樣的「靈魂拷問」,在敘事者的心中反覆出現。
在此之外,這部小說有一個核心的理念,就是主角一直在想:「為什麼我是那個活下來的人?那些比我更好的人都死了,憑什麼我可以活下來?」這組問題一開始看起來,只像是一個倖存者的愧疚或者是反省,但裡面最厲害的是,這個故事裡要的配角,在最後一篇說他們在戰爭裡沒有死,是因為「死神寬恕了我們」,但主角卻說,這是「死神遺棄了我們」。而最後,說了前面那句話的配角,卻在二二八事件中死亡──小說花了90%的篇幅描寫太平洋戰爭,所蓄積的能量在這裡展現,說的是,台灣人的精神、意志,在戰爭那樣的摧殘中沒有死,卻死在二二八。
您在寫自己的小說《以下證言將被全面否認》時,似乎也用了《獵女犯》的典故?
如同等等會談到的小說《異域》所描寫的,過去有一群滇緬孤軍,而我們知道,他們的後代,有些成為來自泰國、緬甸等東南亞國家的僑生;而我的作品〈南方的消息〉寫的是,如果有一個僑生來台灣唸書,他的同學則去中國唸書,兩個人都成為領導人的幕僚,戰爭開戰時會怎樣?這裡一方面是向柏楊致敬,而另一方面,小說的標題〈南方的消息〉,典故就來自《獵女犯》的開頭,他以自己寫的一首詩〈信鴿〉為序,最後寫到:
我回到了,祖國
我才想起
我底死,我忘記帶回來埋設在南洋島嶼的那唯一的我底死啊
我想總有一天,一定會像信鴿那樣
帶回一些南方的消息飛來
這寫的是,我們在戰爭的記憶,會讓我們認知到「我們是另外一種人」──而這一切戰爭記憶,要被贖回來。我做這樣的營造,是有意識地想要連結前面的戰爭小說脈絡。台灣的文學史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也到了可以有自己的繼承系譜的時候了。

4、《異域》:最具批判性的反共文學

這部小說被認為是有一定批判性的作品,想請您談一下他怎麼做批判?
反共文學經常是教條,如果要找有意義、有價值的反共文學,《異域》是最好的例子:他不是官方宣傳那種建國必勝、抗戰必成,而是在問:我們為什麼會輸?這個問題如果一直不檢討,一切的失敗都會變成徒勞,但現實是又不能檢討,因為你不能談蔣介石和他的手下做錯了什麼。
所以要怎麼辦呢?我們現在說《異域》是小說,但發表的時候,《異域》被當作報導文學。確實有一個士兵從前線被接回台灣,拿了一堆手稿跟報社說想要發表,報社覺得這個東西有價值,但又認為士兵文筆不是很好,於是交由柏楊代寫,假託軍官鄧克保的名義,很直接地寫出種種惡行惡狀:某某長官把我們的彈藥給吞了,某將官把中央丟下來的錢全部拿走,某長官陣前投敵,現在又大搖大擺回到台北,其中的描寫是相當悲憤的。
這部小說同時具有一些娛樂性的元素,就在於他會用一些想像力,寫出一些很誇張的英雄情節,比如一個人拿著手榴彈衝進敵人機槍陣地,讓大家看了覺得很熱血。
但這部小說真正的力道,在於批判國民黨為何會失敗。我認為這部小說之所以會成功,不只是因為娛樂性、熱血的元素,而是因為,這其實才是外省人真正想看到的東西──外省人又不是笨蛋,他們也會想:「我們怎麼會淪落到這裡來?」政府又不讓我們講,沒有人幫我們出這口氣,是《異域》幫我出了這口氣。
前線基層官兵有多努力,後面的腐敗就顯得多荒唐。比如說他會一直強調,我們家軍僅僅用了兩、三萬人的殘兵,打下了五倍台灣大的土地,如果台北官方積極進取,一定可以橫掃華南;書中描寫各種英雄式的戰鬥場景、壯烈的事蹟、鮮活的角色,簡直是好萊塢電影,呈現出很明顯的正邪對立。所以,如果要真的去深究文學價值,《異域》或許沒有那麼深刻,畢竟它所有人物都很臉譜化,好人就是好人,壞人就是壞人,但就一個通俗作品來說,會轟動不是沒有原因的。
中國傳統有一個微妙的地方,就是可以批評政治,但一定要說領袖是偉大的,只是被蒙蔽,這也就是所謂「清君側」的邏輯。這部作品也是如此:抓一個局部,指出其腐敗,但不能說中華民國政權是腐敗的,只會說某某部長蒙蔽了前線的戰報,導致後面做出了什麼決定──至於如果戰報正確,後面的決定會不會正確呢?這就不能討論了。
同樣的邏輯,也可以看鍾肇政《魯冰花》。他寫的是教育,小說聚焦一個國小中的生態,但其實是反映整個藝文圈的不公平,其中的品味的歪斜和壟斷,但把它縮小到一個國小當中。
不過在台灣文學中,連這種寫作都消失了很長一段時間,因為60年代以後,現代主義迴避政治,強調文學是「永恆」的,不應執著於一時一地的得失,所以會寫一些看不出時空的東西,批判的能力就會比較低。如果要真的批判,作家可能就會後退,變成是批判整個社會的道德觀念──拜金主義、道德腐化,好像誰都罵了,但好像誰都沒罵。這一點的集大成者就是龍應台,一切都往道德的方向走,好像罵得很兇,每個人看都覺得「對對對,就是這樣」,別人都是這樣,好像跟你沒關係。
這部小說後來也改編成電影,可以請您談一下這個改編嗎?
很多人常常搞錯的是,《異域》後來改編成電影,主題曲叫〈亞細亞的孤兒〉,但歌名的典故不是柏楊,而是吳濁流的同名小說,被羅大佑寫成歌曲,原典是台灣人的處境。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意象挪用放在這裡也通,反映的是本省人跟外省人之間,隱約有一種集體命運、集體的感覺是一致的。當然,本省人的「孤兒感」,歷史起源與外省人並不相同,但最後都會覺得自己是「亞細亞的孤兒」──《異域》電影這個挪用之所以會成立,就是因為打中了一個很準確的感覺結構。
很多人都覺得所謂「主體性」是要一個有內容的東西,是積極地說「我是什麼?我要什麼?」,可是歷史上,台灣人不是這樣煉成的:在關鍵的時間點上,假使當年日本人認可我們,台灣人會願意成為日本人,假使當年中國人認可我們,台灣人也願意成為中國人;但歷史告訴我們,他們永遠覺得我們矮他一截,永遠都覺得我們是可以任意宰割的對象,所以台灣共同體的基礎,在於認知到我們是孤兒、只能靠自己。而反過來說,一直到今天,不屬於本土派的人,心理內建的思考方式,經常是台灣人必須「靠」著別人:搞台獨都是依靠日本人的皇民,或者始終認為台灣必須要依靠中國,不然「沒有市場」等等──他們始終不相信台灣人不靠,這就是這個孤兒處境的反面呈現,是個很特殊的心理狀態。
5、《那年我們祭拜祖靈》〈失手的戰士〉:精神的失落

這部作品是布農族作家霍斯陸曼‧伐伐所寫,是90年代回頭去寫日治時期的事情,跟前面的戰爭描寫有什麼不一樣的視角呢?
日治時期,原住民跟漢人的戰爭記憶很不一樣:漢人的戰爭經驗是開頭的抗日和結尾的二戰,但原住民跟日本人之間一直有戰爭,一直是到20年代左右,用日本人的話來講才「平定」了原住民,而30年代又發生霧社事件,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又緊接著徵召所謂「高砂義勇隊」,原住民其實一直都在戰爭狀態裡面。
而〈失手的戰士〉這篇一開始,是先寫部落內部的習俗,談戰爭背後的文化跟傳統價值:這位戰士的家族,因為一個意外,被大家認為受到詛咒,必須要靠著他當戰士才能洗清,拿回家族被當成人的資格;但實際上了戰場之後,他面前要殺的那個日本女子,讓他想起他的妹妹,他下不了手,於是不割頭顱,只割了她的頭髮,謊稱她掉進懸崖,只割到頭髮──他等於欺騙了他的族人,以換取成為人的資格。
而這部小說最微妙的設計,就是他和那位沒被殺的日本女子,數年後再次見面。那時,日本人已經「平定」了這個地區,定期召集原住民集會。在這個老戰士心中,他心中覺得很屈辱,被迫參加集會聽訓,佩刀還得上繳。結果,這個女生突然走過來,送給他一床棉被,說她的女兒大了,她們要回日本了。
這裡好像可以寫成和解的戲碼,但這位戰士拿到棉被回家的路上,他一直想的事情是:自己已經老到需要人憐憫了嗎?他想想:確實也是啊,我已經失去我的刀,而且,我唯一能夠作為戰士的那一刻,我也放過去了,所以我作為一個「人」其實是不成立的──這裡拉回的是他精神面的失落,不是要繳給日本人多少稅的問題,就如同今天談獵場、談傳統領域的問題,在乎的是不是經濟上少了多少錢,而是我失去了作為「人」的樣子。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在原住民文學中,這部作品的特殊性,是他對傳統的質疑:大多數原住民作家,筆下的小說角色,多半都是抓著傳統,對抗外面的世界,要守護失落的東西;但在這本小說集中,同樣以〈失手的戰士〉來看,敘事者其實一直懷疑為什麼大家會認為他的家族被詛咒,因為他知道其實是自己沒照顧好妹妹,導致妹妹嚴重燒傷,但部落裡的人都說一定是你們家被惡靈詛咒,他爸爸本來是很受人敬重的獵人,從此被剝奪了身份,所以主角也對這個傳統有所反省,但也不是採取一個全面否定的姿態──我覺得這就是很寫實的「人」的狀況,對於傳統,本來就不會是照單全收,但也不是全盤否定。
6、《綠猴劫》:台海戰爭科幻版

這部小說是科幻小說,它怎麼描寫戰爭?
這本小說虛構了兩個國家的戰爭,但其實是直接對應台灣跟中國;劇情是關於戰爭的科幻想像,所以他會寫生物戰、細菌戰、氣象兵器等各式各樣的戰爭模式,在當年是科幻,現在看覺得是真的有可能的。
其中我最喜歡的是〈迷鳥記〉,構想是發現台灣這一方有一種候鳥,會定期飛到敵國的北邊邊境,所以如果在候鳥裡面放膠囊,膠囊裡面有病毒,可以控制融化的時間,讓候鳥飛過去之後,病毒融化、散播開來,就是完美的計畫。而當然,小說一定要出意外的:結果有一隻鳥迷路飛到第三國了,怎麼辦?所以有一名生物學家跟一名情報人員去第三國,用奇怪的方法解決這個問題。
除了這些科幻設計之外,《綠猴劫》最厲害的一點是,它很會結合華人文化傳統。比如〈高卡檔案〉中,說敵國是重男輕女的社會,我方的策略,就是研發一種藥物,讓生男生的比例大幅上升,再派江湖郎中混到敵國內,告訴每一個家族「包生男」,大家都快樂地吃,男女比例迅速失衡,十五年之後,因為男性婚配對象變少了,這個社會到處火拚、自動崩解──這些設計,就是以80年代的華人社會為基礎,我們現在講資訊戰、認知戰,這些戰爭手段都會深度結合社會文化、思考模式,這是他當時就已經在處理的問題了。
這部小說作為本格科幻小說,寫法非常商業片,很好看,是我們今天講的所有作品裡面最無上手門檻,可以純粹享受的。
後記:文學小說怎麼讀
您提到上手門檻的問題,那像前面幾本稍微比較有門檻的作品,如果有些讀者,對所謂純文學的小說閱讀經驗比較少,你會有什麼一般性的建議?
首先,不要全部都看經典作品,會非常痛苦。有些經典作品之所以是經典,可能是有特定的時代因素,比如寫了「那個時間點的人」都沒想過的事情,但你放到現在來看,你不見得覺得它有多厲害。我反而覺得,如果你對純文學作品有興趣,應該要從新的作品開始看,因為新作品是寫給當代讀者的,比如可以從台灣文學金典獎的作品中挑,反而比較容易上手。
何況,台灣的純文學曾經有一段時間非常現代主義,非常難讀,可是最近十幾年來,這個風向已經散去,小說寫作越來越回歸「說故事」的本質,難度是下降的──難度下降不代表深度下降,只是寫法不再往那個刁鑽晦澀的方向去。
我舉個前幾年的例子,之前很多人讀了《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也覺得好看、受到感動,但其實,《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在當代的文學作品裡面是偏難、偏晦澀的,如果你看《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覺得看得懂,應該70%的文學作品都可以看,如果某些其他作品你看不下去,很可能不是因為作品太難,而可能是因為你對這個議題沒有興趣──那很簡單,你就找適合你的當代議題,想看性別、族群都有很多相關的,不用強求自己什麼都吞得下去。
而在挑選上,有一個簡單的方法:你可以去實體書店裡面挑書,不用從頭開始,隨便翻,看個三、四頁,這三、四頁看完了,如果你覺得你都沒看進去,這本書就跟你頻率不合,放回去就對了。
至於在閱讀上,我要提醒的是,純文學小說與通俗小說最大的差別,在於通俗小說重視情節,所以會花大量的力氣來把情節做得複雜;但是,小說有個原理:情節一旦複雜了,人物一定會變單純──你要操縱木偶,木偶自己就不能亂動,木偶亂動,你怎麼操縱他呢?相反地,如果你希望把人物寫得深刻的時候,情節一定會變單薄,因為他只能做「合理」的事。大家可能會覺得純文學小說故事性比較差,是因為純文學小說重點在於寫「人」,它的預設值不是要「看一個好看的故事」,而是「了解這個人為什麼這樣想」,是在了解世界上的另一種人,了解深刻的人性;兩種小說的享受點不一樣,就跟內科、外科治療的病不一樣,如果帶著要看故事的心去看純文學小說,就一定會很挫折。
那在小說的詮釋上呢?
當然,我還是要不免俗地說,沒有什麼「正確答案」,但是,確實有「比較好的答案」跟「比較差的答案」。
要怎麼知道你的詮釋好不好呢?一個簡單的自我檢測方式,我們可以先自問自答,比如說小說裡的一個人,講了這句話後奪門而出,我們就先問自己:「他為什麼這麼做?」問完之後,先猜一個答案,提出一個假設,接著重新回到文本裡找證據。
以大家國文課本都念過的〈孔乙己〉為例,秀才為什麼要找小孩講話?你可能會說,因為他被其他人排擠了,不會有其他人理他,甚至是因為小孩是唯一不會毆打他的人;做出這個假設之後,就回去文本找證據,看這個答案是否可接受。我們不認為讀者要去跟作者對答案,重點是文本裡有證據;而如果有其他人提出相對立的假設,就是要來比較誰的文本證據比較強。這就有點像,以前國文老師可能說,閱讀測驗要先讀題目、選項,再回去讀文章找答案,這聽起來像旁門左道,但其實是正確的作法,就是假設驗證的邏輯。
訪談的最後,您還有什麼其他想跟讀者說的話嗎?
我最後有一點小小的呼告:我很期待有更多有志於創作的人,不管是用什麼形式,可以一起多思考軍事這個主題。我不是希望我們走向一個好戰的社會,但我們過去的文化太逃避「我們眼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對此,創作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在於為我們作預習。就比如,我們本來不會談戀愛,但聽了一百首流行歌、看了十部愛情電影,我們就學會了幾套腳本,當然我可能不會照單全收,我們可以批判性地修改,但作品提供了這個「底」。
我覺得台灣大多數人,正是因為沒有腳本,所以面對戰爭時,害怕就無限膨脹。一旦有越來越多的作品在談論戰爭,給我們一個基本的想像的時候,害怕程度就會得到控制──不會因此就不怕,戰爭當然很危險,但是,我們的恐懼得到一個控制之後,我們才能更理性地去安排說接下來該怎麼做。這是我開始投入這個主題寫作,而且還會寫一段時間、不會立刻就停下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