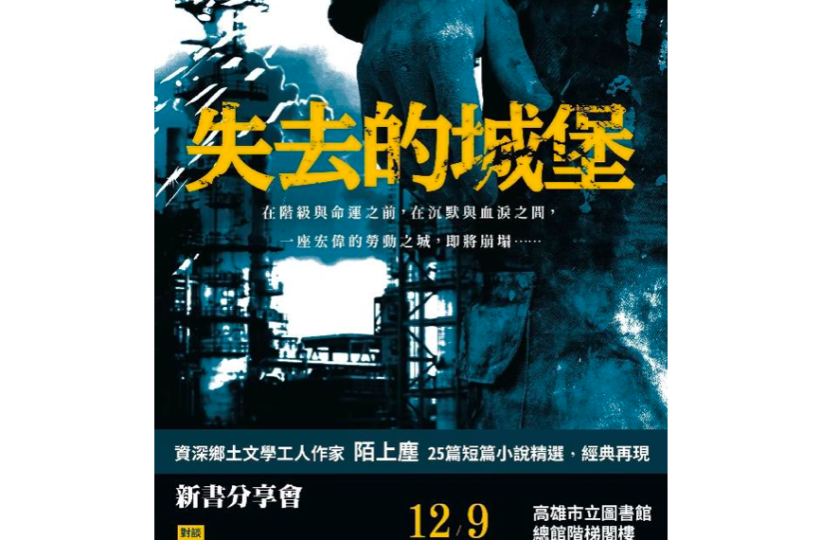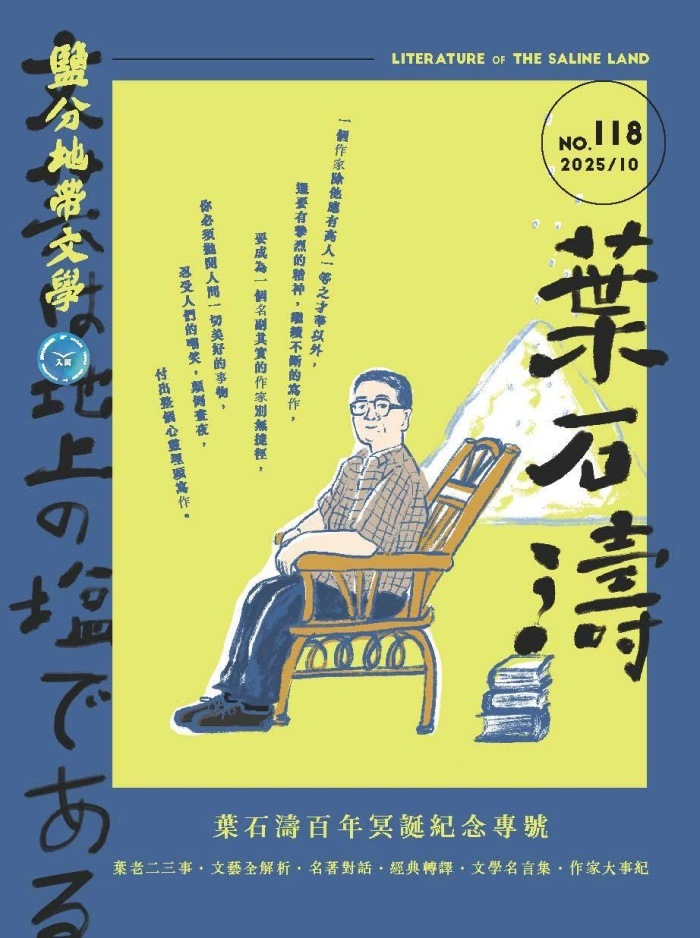想像一下:如果明天早上起床,你赫然發現台灣換了一個政府。這個政府所使用的文字、語言,都是你從來沒學過的——比如西班牙語、印度語或斯拉夫語——,政府給你一年的時間緩衝。到了明年的這一天,你不可以再用自己習慣的任何語言,而必須要轉換成新政府的官方語言。這時候,你的生活會有多大的變化?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改變已經很痛苦了,我們再加上一個條件:如果,你是一個靠文字討生活的「作家」,面對這樣的改變,你的痛苦指數會有多高?
這就是所有日治時期出生的作家,在國民政府來台之後,所遭遇的共同痛苦。接下來你將讀到的作家鍾肇政,也是這個世代的一員。鍾肇政出生於1925年,國民政府在1945年接管台灣。也就是說,在他人生的二十歲之前,他都是以客語為母語,並且以日文為主要的書寫文字;而到了二十歲的這一年,他必須立刻轉換成以中文來寫作,歷經了漫長而痛苦的「跨語」時期。
根據鍾肇政的回憶,他在二十多歲的這段時間,雖然已經用日文讀過各式各樣的文學名著,醉心於日本文學的「俳句」和許多西方文學小說,但面對強制轉換、沒有配套措施的「國語政策」,還是得從ㄅㄆㄇㄈ開始從頭學起。比他年長的日治時期作家,幾乎都因為這樣而放棄了文學寫作。或許是因為鍾肇政稍微年輕,或許是因為寫作的夢想讓他有了超乎常人的毅力,他花了十多年的時間磨練自己的中文,成為戰後最早突破語言障礙的台灣作家之一。1960年,也就是國民政府來台的十五年後,鍾肇政以長篇小說《魯冰花》一舉成名,在文壇上有了一席之地。他等於花了十五年的時間,從一個連中文都不會講、不會寫的人,變成了能寫文學作品,而且能寫文學作品當中最厚重的「長篇小說」的人。
但是,《魯冰花》還不是他挑戰過最困難的作品。在這之後,他開始進行一系列「大河小說」計畫。「大河小說」是來自法國文學的概念,意思是「同一主題下的連續長篇小說」。這種形式,通常都會拿來處理非常複雜的大主題;而在台灣,「大河小說」便長長拿來處理台灣複雜的歷史。台灣的大河小說通常會以一個家族為中心,描寫這個家族所經歷的歷史時期並且常常會以「三部曲」的形式,描寫各個世代的角色。
而鍾肇政,就是台灣最會寫「大河小說」的小說家之一。他從1960年代開始,先寫了「濁流三部曲」,以三部長篇小說描寫日治末期到戰後的一段時間。接著,他又把題材擴大,開始了「台灣人三部曲」的寫作——這次,就是要完整寫完日治時期的初期、中期和晚期了。
——再提醒一次,鍾肇政是「跨語世代」的作家,中文是他第四種學會的語言(前三種應是客語、台語、日語)。使用第四語言,卻能創作出好幾個系列、動輒幾十上百萬字的長篇小說,可以感覺到鍾肇政對文學夢想的執著、努力,以及絕佳的文字天份。
本冊所選錄的《插天山之歌》,就是「台灣人三部曲」的第三部,堪稱是鍾肇政寫作成熟時期的代表作之一。《插天山之歌》以熱血青年陸志驤為主角,描寫二次大戰期間、日本殖民統治底下的台灣。你將閱讀到的段落,是這本書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從小說一開頭,我們便看到鍾肇政非常沉穩的佈局功力:主角陸志驤從日本坐船回台,發現自己被日本警察跟蹤。從這個切入點,一瞬間就把小說的懸疑感拉起來了:為什麼陸志驤會被警察盯上?原來,他從日本留學回台,準備秘密發展抗日組織。而當我們慢慢理解陸志驤的秘密任務,注意力被緊張氣氛吸走之時,鍾肇政卻又安排了一個意外轉折——一枚魚雷擊中了陸志驤乘坐的船隻,全體乘客開始棄船逃亡,而陸志驤也必須在冰冷的海水裡面載浮載沉……
這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設計,使得《插天山之歌》一開場就非常緊湊精彩。但如果你稍微多知道一點台灣歷史,你會發現最厲害的不是「虛構出這些精采的情節」,而是「這些情節在歷史上真的有可能發生」,鍾肇政透過個人經驗與大量的歷史資料,深入體會當時的氛圍與社會制度之後,挑選出寫實且動人的情節來寫。這種遊走於歷史與文學之間的功力,正是歷史小說最困難的地方。但在鍾肇政流暢沉穩的敘事步調下,讀者讀起來一點都不費力。「讓讀者不費力」,往往就是作者已經先下了十足的功夫,才能夠讀起來渾然天成。
如果你讀了本冊選錄的《插天山之歌》,對這部小說感興趣而想讀下去的話,你可以注意一個特別的現象:《插天山之歌》雖然以「抗日」為主題,但小說卻同時也花了大量篇幅,在寫故鄉的風土民情、寫陸志驤怎麼漸漸融入客家人與原住民交會的山區社群之中。這種帶有「鄉土」風情的寫法,乍看之下沒什麼不對,但你仔細想想:「抗日」跟「鄉土」並不是必然要連結在一起的兩個主題。甚至,如果用比較「商業」的寫法,作者大可以將《插天山之歌》寫成一個純粹的諜報故事,或者純粹控訴日本人有多暴虐的小說即可。
而鍾肇政之所以將「抗日」與「鄉土」合在一起寫,正與他面對的政治環境有關。他寫作的期間,主要都在戒嚴時期。在那個時期,由於國民政府強調「反攻大陸」的國策,文學上也必須要呼應官方設定的「政治正確」而去寫「反共文學」,否則就會失去發表機會,甚至可能會有牢獄之災。於是,在那樣的年代,過度強調「鄉土情懷」或「對台灣美好事物的眷戀」,是很不受官方歡迎的——你一直強調台灣有多美好,是不是不想反攻大陸了?偏偏對於鍾肇政這樣的本土作家來說,「反攻大陸」並不是他們真心嚮往的目標,並且他們也不太清楚要怎麼去呼應「反共」這個主題。本土作家並沒有直接和共產黨作戰過,先不說有沒有深仇大恨可寫,就連「共產黨具體是什麼樣子」可能都很模糊。
因此,「抗日」就成了本土作家跟國民政府少數的公約數。國民政府經歷了十多年的中日戰爭,對日本恨之入骨;本土作家也經歷了五十年的殖民時代,有許多材料可寫。像鍾肇政這樣寫不了或不想寫「反共」的本土作家,就往往以「抗日」主題來跟政府虛以委蛇,並且以此包裝自己真正想寫的「鄉土」主題——如果只寫「鄉土」會被當作反對政府,那我寫一個抗日青年回到家鄉的故事總可以了吧?最終,這就形成了《插天山之歌》的特殊樣貌。
從這樣的一部小說裡,我們可以看到文學的各種複雜面向。一部好作品並不只是技巧好、主題好而已,更有可能包含了作家的思考與策略,特別是在「戒嚴時期」這樣政治高壓的不正常年代,作家的每一個安排很可能都煞費苦心,像是走鋼絲般維持著危險的平衡。而當你理解到一部小說除了故事好看,後面還有種種考量之後,想必就更能理解《插天山之歌》的難度與深度了。這可是本土作家鍾肇政,連續翻過了「語言」與「政治」兩座絕壁之後,才能奔流到我們面前的大河之水。作家自己消化了一切艱困之事,只為了把歷史記憶帶到我們面前,讓我們能夠輕鬆地進入。而我們呼應這份心意的方式也很簡單:只要翻開書頁,進入他為我們構築的世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