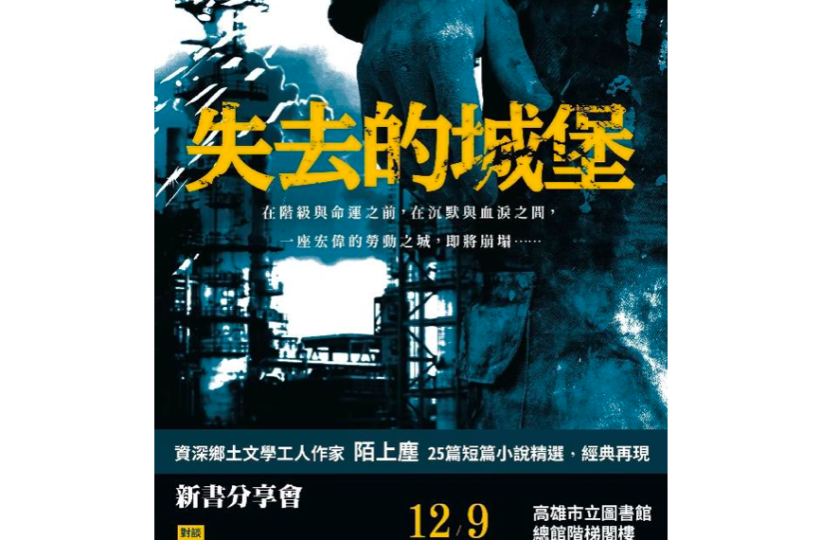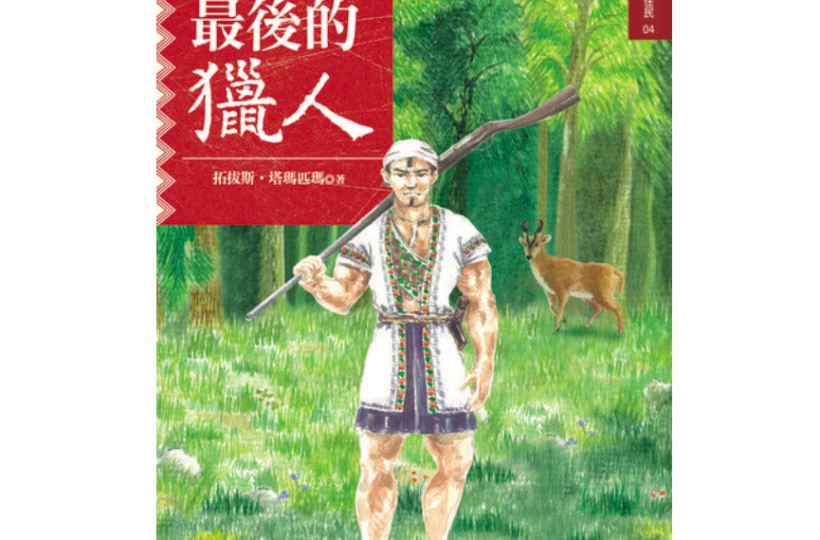如果我們把思緒放回一切文明的起點,回到人類最初的「自然狀態」裡,我們會發現,「勞工」並不是一種自然的職業。不管是採集、漁獵還是農耕,最早的人類生活,是高度依附於土地的。人們從土地上所生產的,就是自己所要食用的。然而現代意義的「勞工」則不同,縱使「勞工」的身份與處境有千百種,但有一個基本特性是不變的,那就是「不再依附土地,依靠自己的技能和體力賺取生活所需」。而這種特性,基本上就成為所有描寫勞工之文學作品的起點。一代代作家都在思考:這樣子的生活方式,能夠讓人們得到溫飽與尊嚴嗎?或者反過來問:為什麼幾乎所有時代的「勞工」們,其技能與體力的價值總是被低估,他們所生產的價值與他們所獲得的報酬,為何總是不成比例?
馬克思的《資本論》用一個非常簡潔的句子,點名了勞工的處境:「自由得一無所有。」說自由,是因為勞工不必被綁在土地上,理論上可以自由受僱於任何地方;但這種自由只是幻象,因為你要吃要睡,所以你必須出售自己僅有的勞力。
如果要用台灣文學作品來印證這種現象,我認為至少可以從〈渡台悲歌〉開始談起。〈渡台悲歌〉是一首民間詩歌,最有名的就是前兩句:「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大多數人閱讀此詩時,都會把它當成「先民渡台的血淚史」。這個角度沒有錯,但我認為換個角度想會更銳利:這是一首「移工」的血淚控訴之詩!事實上,所謂「先民渡台」,基本上就是大量漢人的移工來到台灣的歷史。大多數台灣人來到台灣的原因,跟現在俗稱的「外勞」是一模一樣的。因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渡台悲歌〉會有淒慘到甚至可說是淒厲的描寫。比如描述「客頭」(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仲介」)之無良:
客頭說到台灣好,賺銀如水一般了。
口似花娘嘴一樣,親朋不可信其言,
到處騙感人來去,心中想賺帶客錢。
千個客頭無好死,分屍碎骨絕代言。
而到了台灣之後,這些移工就依照年紀,被人像牲口一樣地挑選:
各人打算尋頭路,或是僱工做長年,
可比唐山賣牛樣,任其挑選講銀錢。
少壯之人銀十貳,一月算來銀一圓,
四拾以外出頭歲,一年只堪五花邊。
被雇用之後,非但不是安穩生活的開始,反而落入了更慘烈的勞動地獄。《渡台悲歌》用了幾十行詩,描寫各式各樣痛苦的生活細節。以下這段「抱病也得工作、做了又賺不了幾塊錢」的描寫,只是其中一小段:
落霜落雪風颱雨,頭燒額痛無推懶,
拾分辛苦做不得,睡日眠床除百錢。
各人輕些就要做,行路都還打腳偏,
換衫自己雞啼洗,破爛穿空夜補連。
自己上山擔柴賣,一日算來無百錢,
大秤百斤錢一百,磧得肩頭皆又彎。
限於篇幅,我們沒辦法完全介紹〈渡台悲歌〉全文。一般認為,〈渡台悲歌〉描寫的是十九世紀左右的台灣。若你有興趣一讀,想必會感覺到數百年前「移工」的呼號咒罵,毫無衰減、鮮明銳利地打到你心底。詩裡的每一句話,在在都印證了「自由得一無所有」的按語。
時代繼續往前,進入二十世紀的日治時代,台灣勞工面對是一個又舊又新的局面。說「舊」,是因為基本的困境仍然沒變;說「新」,則是因為新產業與新科技陸續進入台灣,將毫無心理準備的台灣人驅入了工業時代。在小說方面,呂赫若的〈牛車〉可以說是描寫「被時代輾過的勞工」最經典的小說之一。小說的主角是一名牛車夫,他本來靠著拉牛車運送農產品,就可以過上滿舒服的日子。沒想到來到「日本天年」,不但汽車、腳踏車取代了他的工作,連新規劃的道路都不允許牛車行駛了。牛車夫的困惑,正是所有即將被科技淘汰的勞工的困惑:「為什麼我比以前認真那麼多,卻反而過得更差了?」時代進步的果實屬於花得起錢的人,代價卻總是由奉獻勞力的人來支付,這樁交易從一開始就不公平。
而在產業的變革下,日治台灣也開始有了工業的景觀。其中,詩人林芳年的〈在原野上看到煙囪〉一詩就以「煙囪」這個工業意象為核心,描寫人們的焦慮與恐懼:
不論怎樣勞累
我們的口袋都是空空
我是魔術師
克琳克琳進來幾個錢
而這幾個錢又克琳克琳馬上消失了
我感到
一個工廠的增建不疑就是
一次高興
但每次出現了一個工廠
我就發抖
因為那是酷似我們的魔窟
絕不維護我們
就算詩中的「我們」沒有自我介紹,我們也看得出那是勞工的視角。勞累了,為何口袋還空空?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總是有辦法再把你微薄的收入賺回去。而面對不斷擴張的「工廠」,「我們」一下高興、一下發抖,也完全可以理解——有工廠就有就業機會,然而就業就像是進入了「絕不維護我們的魔窟」一般可怕。短短幾行,把勞工的處境寫得極為傳神:就業或不就業,似乎都找不到幸福。
好吧,既然台灣那麼可怕,那就到更繁榮的「內地」——在日治時代,指的是日本本土——找找機會吧?於是,我們就有了楊逵的小說名作〈送報伕〉。在談〈送報伕〉之前,讓我先插播一句題外話: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如果要到日本工作,是必須搭船前往的;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台語老歌描寫外出打拼的場景時,總是從「港邊」寫起。現在你知道為什麼「港邊是男性傷心的所在」了,不是火車站也不是機場。
說回〈送報伕〉。這篇小說就寫一個在故鄉走投無路的人,讓家人拮据地擠出一筆旅費,去日本打拼看看。但當一個人的勞動力在台灣都賣不出去的時候,去日本也不會比較好賣。於是,主角只能找到條件非常糟糕的「送報伕」的工作。在漫長的被欺壓與反欺壓的過程後,主角終於覺醒,組織了一場非常成功的罷工,改善了送報伕們的勞動條件。小說最後,楊逵描寫主角坐船回台灣,心中意氣昂揚:
我滿懷著確信,從巨船蓬萊丸底甲板上凝視著臺灣底春天,那兒表面上雖然美麗肥滿,但只要插進一針,就會看見惡臭逼人的血膿底迸出。
這句意有所指的話,沒有一句提到「左派」或「工會」,但事實上就是在暗示:主角即將回到台灣,運用自己的鬥爭經驗,來協助勞工對抗資本家。所謂「一針」,指的就是左派的社運精英。因此,楊逵〈送報伕〉描寫的不只是工人的覺醒,更是日本與台灣之間左派運動的連結。這也就不難想像,為何這篇小說會在東京的左派文學雜誌《文學評論》得獎了;這可是台灣作家首次以日文寫作、並且在日本本土獲得文學獎的紀錄。
如果日治時期是台灣人初次接觸到了工業化的威力與傷害,戰後的國府時期則就是工業化鋪天蓋地襲來的時代了。在美援、進口替代、加工出口區等因素的影響下,台灣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急速工業化,也因此吸納了大量勞動人口,「勞工」取代「農民」成為台灣社會最大的職業樣態。在這種背景下,更加專注於描寫工人的「工人小說」誕生了,最具代表性的當屬1970年代的楊青矗和1980年代的陌上塵;而在新詩方面,則有李昌憲的《加工區詩抄》等作品。
李昌憲的〈加班〉描寫了生產線上的女工,如何一個人操持家計與家務。為了撫育孩子,她必須加班;可是無論怎麼加班,還是沒辦法趕上物價上漲的速度,只是徒然流失了幸福:
兒女對著桌上的飯菜
搖頭,的壓力
無論再怎樣拼命
加班,也賺不回
眉頭深縐的看看薪資袋
看看稚齡的兒女
看看牆上蛛網網住的
丈夫的臉,跟著自己一起
模糊起來
相較於新詩以精簡有力的心理描寫見長,小說則能含納更複雜的社會現象,透過故事引發讀者的思考。楊青矗的《工廠人》和《工廠女兒圈》就以一系列短篇小說,描寫了工廠裡不同性別、不同階層的工人,讓讀者看見勞工之間的差異性。以《工廠人》為例,它花了大量篇章處理「臨時工vs正工」和「評等」兩個問題。在這本書裡,「等」成為最重要的關鍵字:既是等級(決定薪資多寡的工作評等),也是等待(等待機運、等待努力被看見、等待人事變化)。以此為核心,《工廠人》從最低等級的臨時工、不同等級的正工、享有較優待遇的職員,一直寫到經營管理階層,呈現了一幅完整的工廠生態圖景。
全書當中,我認為最好的一篇是〈低等人〉。小說以極為誠懇的筆調,描寫極微卑微的「低等人」粗樹伯,他是全公司地位最低的,負責清運垃圾的員工。小說開場時,主角:「甚至擔憂有一天他拖不動垃圾,公司能否僱到一位同他一樣的低等人來接替他的職位。」中後段則轉換動機:「宏興公司列位殉職的同仁們,我董粗樹三十年前進入公司為拖垃圾的臨時工,你們在生時都認識我的。我今天很羨慕你們為公殉身的精神,請諸位英靈保佑我,賜給我一個像你們一樣的殉職的機會。我將被解僱,臨時工沒有退休金,又無依無靠,無以為生,我需要一點撫恤金來養活老父。在這十幾天內賜給我機會,我到九泉地下願繼續為各位拖垃圾效勞。」當一個人全心全意相信自己「應該低等」、相信自己「死了比活著有價值」的時候,作者不必多加評判,讀者就能領會到工廠的殘酷了。也因此,小說的黑色幽默力道更強。粗樹伯之艱困不只在生活不易,連要自殺都很困難:「各工場的安全設施都很週到,粗樹伯找不到機會好在工作中置身於死地。」若要論台灣文學史上,最能寫盡「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八個字的人物,我認為就是楊青矗筆下的粗樹伯了。
相較之下,1980年代開始活躍的陌上塵,則更善於描寫「夾在勞資之間」的一群人。他的代表作《失去的城堡》收錄了二十多個短篇小說,其中有許多篇章都是描寫「工人幹部」——領班、班長、老師傅、工會代表。他們雖然是工人,卻又不是粗樹伯這種最底層、缺乏知識和意志的可憐人。但他們的悲劇,也就在於他們「知道,但做不到」。他們想要幫助同僚爭取權益,但總是面對資方的威脅利誘;轉過身來,當他們因職務而必須傳達不合理的命令時,又要面對勞工弟兄的冷眼。
在系列作品裡,〈表決〉描寫耿直的工會代表如何抵抗資方層出不窮的「說服」手段,最終無論你有多麽堅定、多麽不想對不起同儕,他們就是能讓你無法投票。〈逝〉和〈火浴〉都描寫工安意外,其中〈火浴〉的鋪陳之細膩、災難場景之絕望,在在令人不忍卒睹,是陌上塵最完整的作品之一。而與書名同名的〈消失的城堡〉一篇,則從一個刁鑽的角度出發:主角再過兩年就可以榮退,卻在此時被資遣。相較於其他篇章的激憤抗議,〈消失的城堡〉反而採取一種比較抽離、無奈的寫法:抗爭又能如何呢?這個龐大的機器早已僵化難救了。小說不但描寫現場工人與辦公室職員的衝突,更開始思考「自動化」的議題。1980年代的主角不為自己而義憤,卻為全體工人的未來而擔憂:如果有一天,機器人取代了所有勞工……在三、四十年後,我們面臨AI挑戰的當下閱讀此篇,相信會別有一番體悟。
有趣的是,在小說最後,不只是老工人被資遣,連工廠裡面最有才華的年輕工人都決定辭職。辭職做什麼呢?他決定回鄉種田,放棄「自由得一無所有」的勞工身份,回到土地裡去。
這當然是一種鄉土文學式的浪漫了。回到土地,就能解決溫飽與尊嚴的問題嗎?恐怕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從文明的起點來到今日,或許有很多事情已經回不去了。然而如果我們重溫台灣文學史上這一系列描寫勞工的作品,包括本文提及的、以及限於篇幅無法提及的更多作家們,我們或許能看到身而為人最基本的渴望與關懷,是無論科技怎麼進展都不會改變的。一代代的作家,所銘記下來的也就是這樣的心情吧:用自己的雙手,搭建自己不驚風雨、毋須向誰低頭的,真正自由的生命。
・本文刊載於《中鋼勞工月刊》勞動節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