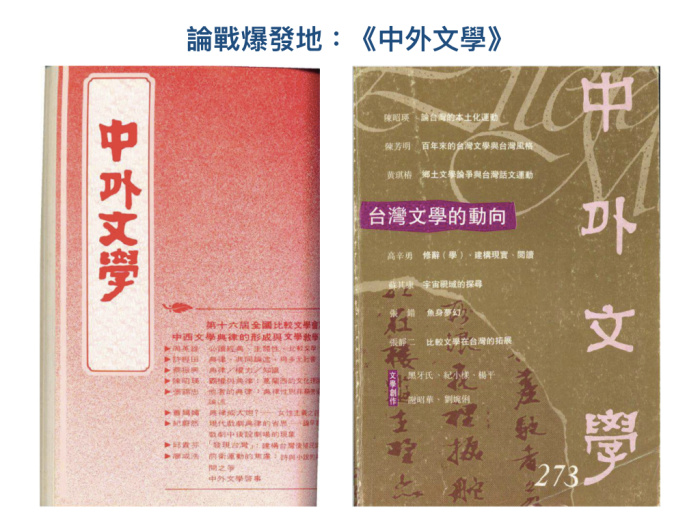歷史與文學的轉折點
1970年代的台灣,可以說正處在一個轉折點。我們現在知道,戒嚴時期是從1945年一路持續到1987年。由此來說,1970年代差不多就是戒嚴時期的中點。在此之前,台灣的文學基本上以「官方的反共懷鄉vs民間的現代主義」為兩大主流。前者充滿政治教條,後者逃避政治表達,雖然在後者的藝術成就遠遠高於前者,但兩者都有一個共通點:不寫台灣的現實題材。
這在台灣文學史上,是一個頗為奇怪的突變時期。只要稍微回顧一下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幾場論戰,就會發現每個時期都會有至少一股重視現實的文學力量。「新舊文學論戰」的新文學陣營,是為了推動現實改革而建立新文學的;「台灣話文論戰」是為了更貼近現實群眾而訴求「言文一致」;「糞寫實主義論戰」的台灣作家力抗日本作家抹消台灣現實的文學主張;「《橋》副刊論戰」更是雙方都在左派的旗幟下,思考「文學怎樣能夠更貼近現實」。
但在戒嚴時期前半,「現實」這個關鍵字突然不是文壇主調了。官方的反共懷鄉文學,心心念念的是如何回返神州大地,自然對台灣的現實題材沒興趣。而民間的現代主義選擇以晦澀的手法來鑽探內心世界,也自然而然迴避了現實題材——畢竟在嚴厲的言論審查制度下,描寫現實可是動輒得咎的,不小心批評到政府還得了?不過,現代主義也並非通通都往「看不懂」的路線奔馳到底。如上一章結尾所述,1960年代的現代詩很快在「天狼星論戰」之後,再分裂成兩大主要流派:分別是以洛夫為代表的「超現實主義」,以及以余光中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
「超現實主義」可以說是「越寫越難得現代詩」。在上一章第一節,我們引述了洛夫的〈石室之死亡〉,就是這種流派的代表作。如果你還沒想起他的風格,我樂意再引一段讓你感覺一下:
我的面容展開如一株樹,樹在火中成長
一切靜止,唯眸子在眼瞼後面移動
移向許多人都怕談及的方向
而我確是那株被鋸斷的苦梨
建立免費帳戶或
登入以繼續閱讀或繼續使用 Goo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