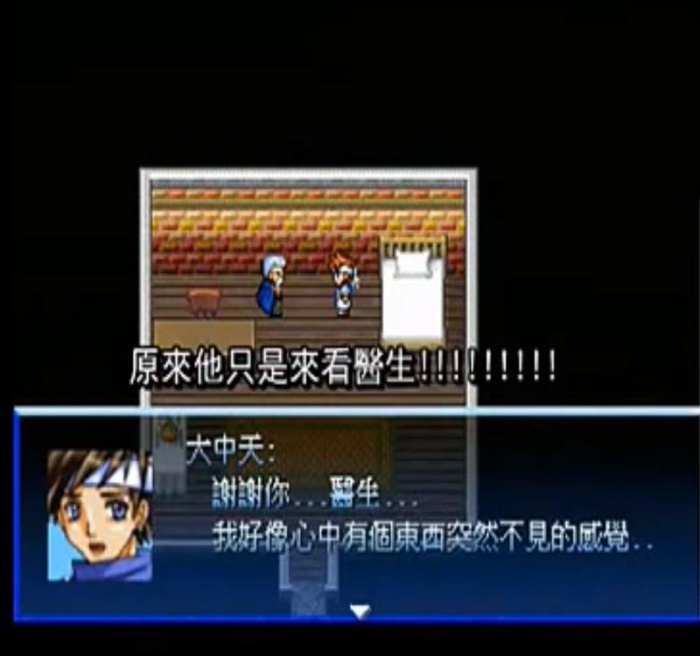小時候,我的第一個志向是醫生。大人們聽我這麼說都會笑開來,我也會跟著笑,但要到長很大之後,才發現不是在開心同一回事。對我來說,「看醫生」滿好玩的,近乎於遊戲;因此我推想,「當醫生」應該也會很有趣吧?
我從出生起就注定了跟醫院的緣分。我是提早五十天出生的早產兒,體重只有一千九百多克,是三兄弟裡最輕的。一千九百多克到底是多輕,我不太有概念。倒是有個故事,是我毫無記憶而家人津津樂道的:因為早產,我一出生就被送進保溫箱。外婆來院探望,想早點看到她的長外孫。隔著玻璃窗,外婆找到我所屬的「箱位」,但她才看一眼,就發現事情不對勁。
箱裡只有被褥,哪裡有什麼嬰兒?
人呢?
這一驚非同小可,整個婦產科動員起來,全院上下搜索這名年輕的失蹤人口。外婆飽受驚嚇,以為自己從未謀面的外孫被人綁架了。那是1988年,解嚴之後沒有多久。要到三十多年後,我才會在謝宜安一篇分析都市傳說的文章裡聯想起來:對耶,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就是台灣有許多綁票撕票案件,搞得許多家長人心惶惶的時期。
我當然沒有被綁架。我之所以從「箱位」裡消失,與我一千九百多克的原廠設定密切相關。兵荒馬亂一陣子,終於有位護理師想到:是不是應該先徹底檢查保溫箱?她回到我的箱位,乍看之下確實空無一物,但當她把被褥掀起來檢查時,發現了一隻體積幼小的不明生物。它皺縮成一團,卡在床鋪和箱壁之間的縫隙,睡得非常安穩。
結案:我沒有被綁架。只是安置一般早產兒的保溫箱,對我來說還是有點太大了。
稍微懂事之後,我常和朋友分享這個故事。不只是因為它有很典型的喜劇結構,更是因為,從我小學到研究所畢業,沒有任何人會相信這個故事的前提——我是早產兒。我看起來一點都不像。或許是初次見面的印象太過強烈,外婆在接下來幾十年裡,頗以餵食我為己任。營養均不均衡還是其次,量是一定要比足夠更足夠
登入以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