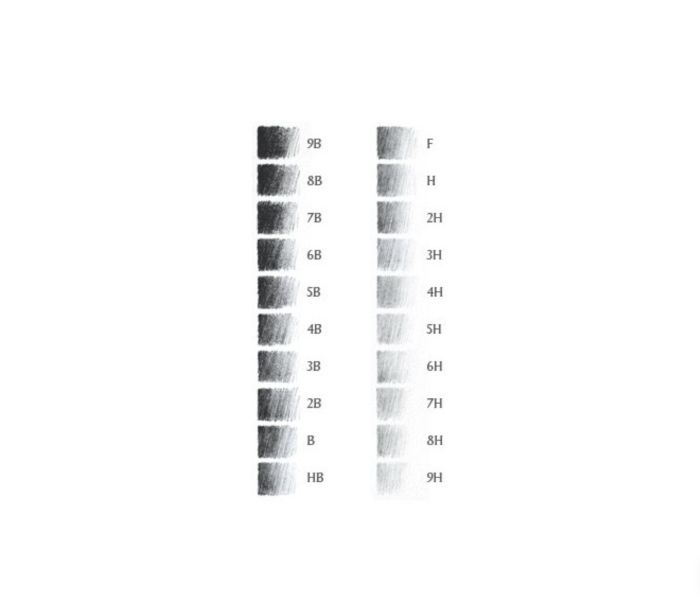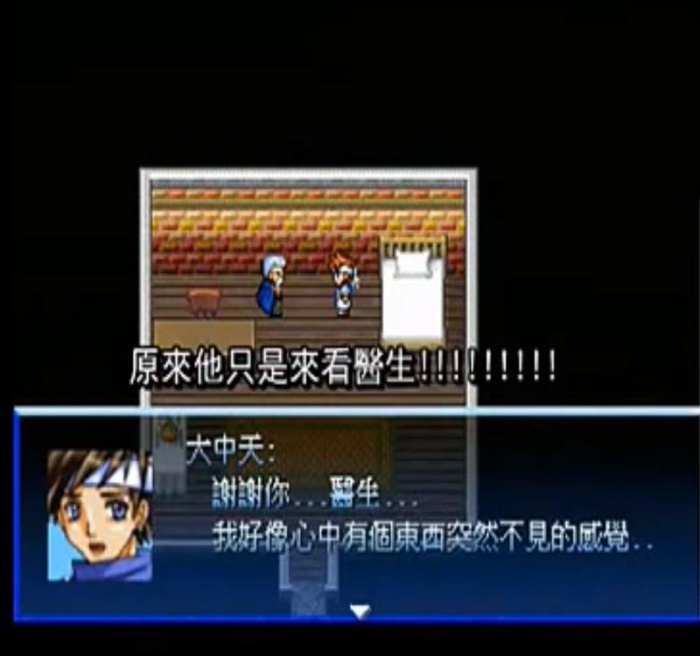有意識以來,我一直自認是毫無疑問的胖子。
認真想起來,「胖」其實並不是一個絕對的數字:超過某某公斤,BMI大於多少,或體脂率高於多少,你就會自覺斤兩已足,不好意思不胖了。毋寧說,胖是一系列生活狀態,最終合成一種類似於「身份認同」的東西。比如飲食習慣:或許挑食,但絕不忌口。一日三餐奉行「褐色是快樂的顏色」,油脂、蛋白質、碳水化合物三大營養素多多益善;但一切深深淺淺的綠色,通通都是致鬱系食物,勉強吃一口盡盡義務,那天已算非常乖巧。比如運動習慣:基本上就是沒有習慣。任何會讓呼吸急促一點的活動,都是文明發達之後,可以避免的苦役。不然人類那麼努力發展科學要做什麼?不就是為了讓我不必自己走到巷口,就能有無數種買到手搖飲料的方法?
少動多吃,於是成為我自小的身份認同座標:沒錯,我就是這樣一個胖子。
不過,所有「認同」往往都有一點以偏概全的成分。直到幾年前,我開始健身也開始學習觀察人的體態之後,回頭看自己小時候的照片,赫然發現:我竟然沒有自己以為的「那麼胖」?那種體態當然說不上好,虛軟廢弱是一望即知。但比起上大學之後急速吹脹的體型,十多歲的我其實是「還比較好救」的。青春期旺盛的代謝率果然驚人,可以在那種日日雞排與炒飯的狀態下,還維持一槓基本算是直筒的身形。這樣說起來,與其說我當時是胖,不如說是虛——我以為跑不動、站不久、走不遠、跳不高是因為肥胖,而沒想到,它也可能只是自己虛構給自己的藉口。並不是因為我胖,所以體能弱;而是我不想動,所以我決定自己必定是個胖子。
不過,上大學之後的身形可就真是「夢想成真」了。大學到研究所,我都在號稱「美食沙漠」的新竹讀書(多年以後我才明白,這種說法實際上是清、交大學生在各種條件之下,「剛好」與新竹好吃的東西隔離開來,才莫名傳開的天大誤會),但我對大學生活的第一印象,就是可以敞開腹肚放心吃。由於外婆的寵溺,我在家裡本來就愛吃什麼有什麼。然而大學生離家長住,自然又是另一番放縱光景。大一首日,直屬學長領到我們幾個學號鄰近的小弟妹,就帶到清大對面的「宵夜街」走踏。吃沒幾攤,學長問我想喝什麼飲料,他請客。我腦袋閃過的是便
登入以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