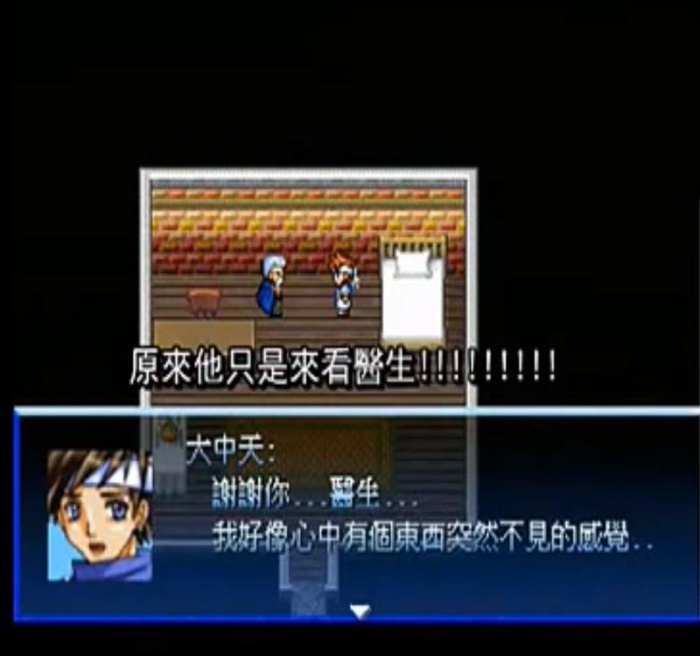在Y教我以前,我是不會吃東西的。
第一課,是辨認人工香精的味道。那時候我們已交往了一陣子,我從新竹搬到花蓮與她同住,一面打工一面寫論文。Y發現我非常喜歡吃冰淇淋,好壞不忌,為此常到特定幾家小火鍋店用餐——純粹就為了飯後可以盡情挖冰來吃。Y家裡是做烘焙的,自己也有開甜點店的夢想,對口味頗有要求,屢屢困惑:「你難道不覺得,吃到人工香精的時候,會有很不舒服的感覺嗎?」
我搖頭。什麼感覺?冰淇淋不就是冰涼、甜美和柔膩的組合嗎,怎麼會不舒服?
這就是課程的開始,Y與我約法三章:接下來的幾個月內,如果我想吃冰,要先「呈報」是哪個品牌、哪家店鋪,經她許可,方能下手;她也提供一些「白名單」,是她確認過品質無虞,我們又買得起的。不用說,小火鍋店裡免費提供的那些冰淇淋,通通都是黑名單了。我稍微覺得麻煩,但也沒有太扞格——反正我不挑,只要有白名單存在,就意味著我還有冰吃。只是,我心底偷偷不以為然:真能有多大差別嗎?我就是愛吃冰,等級低一點的,仍然會在我味覺的好球帶裡呀,何必刻意區隔?
偶有幾次,當我們吃起那些「據說品質比較好」的冰淇淋時,Y會問我感想。我會答:「好吃。」這是實話,但我沒講下半句:「我覺得你會皺眉的那些冰,也差不多好吃……。」但Y也沒有多追問,只要我能恪守戒律,她也沒有強要我像電影裡的品酒師那樣,講出各種抽象至極的風味形容詞。
長長一段時間後,我們又陰錯陽差進了一家去過的小火鍋店。我們好久沒來了,在冰淇淋約法之下,這些店家都對我失去了吸引力。若非我們要去的幾家店都剛好休息,又實在餓得太晚,大概也不會再次光顧。就在湯足飯飽之後,我目光投向擺放冰櫃的角落,又轉過頭來看看Y。我知道那裡固定會有四個桶子,裝著不知品牌的香草、草莓、芋頭和巧克力冰淇淋。店家有時會刻意把溫度調低,使得冰淇淋堅硬如鐵,防止客人挖太多。但即使如此,我還是有止不住的渴望,想去鑿點礦回來。
出乎意料的是,Y點了點
登入以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