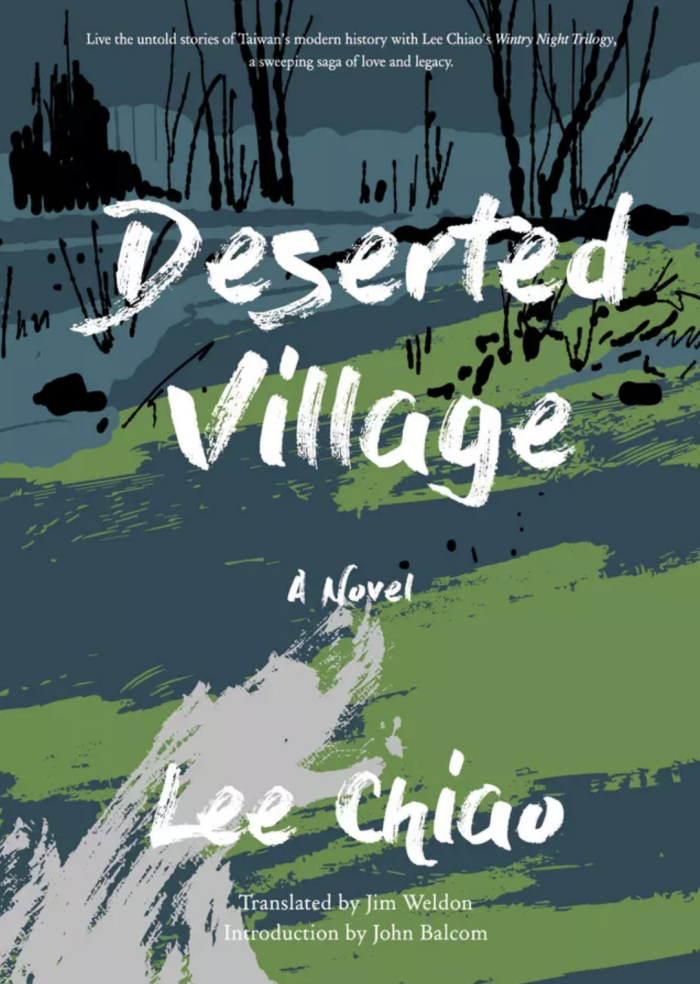按:作家李喬代表作「寒夜三部曲」中的二部曲《荒村》(Deserted Village)英譯本,在客家委員會促成下, 由金.威爾登(Jim Weldon)翻譯,近期書林出版社正式發行。本文是我受邀為該書所撰寫之導讀。
李喬《荒村》是其長篇小說代表作「寒夜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寒夜》描寫十九世紀末,客家人開墾荒地、並且經歷由清國統治轉換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巨變;第三部《孤燈》則以日本殖民統治末期為背景,描寫二次世界大戰底下,台灣人或被徵召出征、或在原鄉陷於飢饉的慘況。而您手上的這本《荒村》,這介於這兩者之間,描寫的是1920年代「文化協會」及「農民組合」向日本人抗爭的歷史故事。「寒夜三部曲」的三本長篇小說組合起來,便是一套台灣人的「被殖民經驗史」。
然而,光是明白這些背景,也並不足夠說明李喬《荒村》的特殊性。以下,我將從幾個不同的面向,提供一些可資參考的文學脈絡,幫助您更清楚理解《荒村》的定位,以及為何它在台灣文學史上如此重要。
首先,我們可以先從李喬這位作家的文學風格談起。「寒夜三部曲」集中於1979年到1981年出版,然而,在這三本書出版之前,李喬並不以「現實主義的長篇小說」見長。相反的,在他出道的1960年代、乃至於1970年代,李喬真正享譽文壇的是他的「現代主義的短篇小說」,代表作之一是1965年的《飄然曠野》。即便他日漸由現代主義轉向現實主義,有了更多牽涉歷史主題或社會議題的作品,比如1970年出版、顯然已為「寒夜三部曲」在做準備的《山女──蕃仔林故事集》,他仍是一個典型的短篇小說作家。
李喬轉向長篇小說創作的契機,是1977年出版的《結義西來庵》。為了創作這本描寫台灣人武裝抗日,最終招致慘烈結果的作品,李喬首次嘗試以田野調查和文獻資料結合,撰寫長篇的歷史小說。在《結義西來庵》的「暖身」之後,李喬正式開啟了「寒夜三部曲」的創作計畫,才再創他的文學高峰。
此一「由短篇到長篇」、「由現代主義到現實主義」的轉變過程,則與1970年代臺灣文壇的整體發展有關。在1960年代,也就是李喬初入文壇的時間點,台灣作家不耐煩於充滿官方教條的「反共文學」,卻又無力直接與戒嚴體制的文藝政策對抗,遂以西方引入的「現代主義」來消極對抗——如此一來,作家們就遁逃到複雜的內心世界與形式實驗裡,可以「既不呼應官方的政治教條,又不會與官方直接衝突」。李喬的寫作從現代主義起步,多少也受到了此一氛圍的影響。然而,時序進入1970年代,部分作家已不能滿足於消極遁逃的現代主義,試圖以更積極描寫本土題材的「鄉土文學」,來表達他們對官方文藝政策與意識型態的不滿。這種以「鄉土文學」命名的流派,實際上就是帶有左派思想的現實主義文學,只是隱匿了「左派」的旗號以迴避政治審查。不過,官方很快察覺到不對勁,遂策動支持官方的作家出手批判「鄉土文學」的陣營,這便是台灣文學史上最大的一場論戰: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
我們回頭來看李喬,此一脈絡的影響便歷歷可見了:1977年不但是「鄉土文學論戰」爆發之年,也是李喬寫作《結義西來庵》,「由短篇轉到長篇」、「由現代主義轉到現實主義」的時間點。隨後,李喬以此為基礎開啟了「寒夜三部曲」的計畫,也就可以清楚看見作家與文壇之間的共振。
不過,我們千萬不能因此誤認李喬是「鄉土文學」的一員。文學上的「共振」不代表思想上完全能「共融」,甚至可以說,李喬作品裡面的意識形態,實際上是與「鄉土文學」保持距離的。這又要引入另一政治 / 文學脈絡:在整個戒嚴時期,國民黨官方的意識形態,可以說是由「右派」與「統派」(中國民族主義)組成的。而潛伏在台灣社會裡,反抗國民黨的民間力量,也就由這兩個軸線產生了兩個陣營,分別是「左派」(對抗右派)及「獨派」(台灣民族主義,對抗中國民族主義)。前述的「鄉土文學」,就是屬於左派陣營,但他們在民族認同上,與國民黨官方同屬中國民族主義;而李喬及其同盟的文學流派,則屬於「獨派」——他們主張台灣人種種歷史苦難,都肇因於「無法當家作主」,因此不能再隨強權擺佈,必須尋求台灣國族的獨立。也就是說,「左派」和「獨派」雖然都反對國民黨,但鬥爭路線完全不同,彼此也有微妙的緊張關係。
這個脈絡,就可以解釋「寒夜三部曲」特殊的作品結構。「左派」訴求階級鬥爭,因而更重視「當下」的台灣困境,著重描寫1970年代台灣底層民眾如何受到美國、日本資本主義的入侵。「獨派」訴求台灣民族認同,就更傾向描寫台灣人的歷史記憶,以對抗國民黨官方的刻意抹除。所以,為什麼「寒夜三部曲」的《寒夜》要描寫拓荒、《荒村》要描寫為了土地而抗爭、《孤燈》要描寫戰爭時期的堅韌生命力,都蘊含了「建構台灣人歷史記憶」之宏願。而這種「以三部連貫的長篇小說,描寫台灣人艱辛奮鬥之歷史」的形式,是「獨派」作家特別偏愛的寫法。這是師法法國「大河小說」(roman-fleuve)而來的。除了李喬的「寒夜三部曲」,鍾肇政的「台灣人三部曲」亦是同樣厚重磅礴的代表作。相對的,「左派」的鄉土文學就沒那麼關注歷史,也沒那麼偏好長篇小說,並沒有「獨派」這樣「以大河小說為台灣民族建立身世」的企圖。
而在這樣的視野下,我們更會看到《荒村》這部小說最饒富興味之處。《荒村》寫的是1920年代中晚期,「台灣文化協會」帶領農民向日本殖民政府抗爭的故事。然而,這個時間點,正是「台灣文化協會」內部路線爭議浮上檯面,最終導致分裂的時期。是怎樣的路線爭議呢?嗯,正是一派「民族路線」,以台灣人對抗日本人,爭取自治權為訴求;另一派則是「左派路線」,領導農人與工人發動抗爭,爭取階級平等為訴求。也就是說,《荒村》所描寫的1920年代末期「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正與作家李喬在1970年代末期所親見的「左派vs獨派」路線分歧成為鏡像。這當然不是巧合。
因此,當我們讀到《荒村》主角劉阿漢不斷強調「他只想保護土地、從日本人手上爭取農民的權利」,並且對兒子劉明鼎日漸左傾戒慎恐懼時,其實一定程度上呈現了李喬的政治思想。甚至,如果我們從劉阿漢的角度來看,會隱然感覺到他是被左派的郭秋揚、簡吉甚至是他兒子蒙蔽了,這種微妙的欺瞞之感,何嘗不是李喬對左派的批判?而在小說結尾處,劉阿漢的「遺言」,當然也就不只是對兒子的關心,更是一種從土地——當然是「台灣的土地」,「獨派」的精神依歸——出發的、對左派的「諫言」。
我們幾乎可以說,李喬的《荒村》正是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經典例證之一。但這也提醒了我們,在閱讀這樣的作品時,如能暫且擱置我們自身的立場,試著透過文學作品所開闢的空間去設想「如果是我,我會不會做出一樣的決定」,應能獲得更豐富的啟示。在不同的國家,左右之爭、民族認同的分歧,都有不一樣的脈絡與特質,就像比例濃淡不一的珍珠奶茶一樣。如果您願意將《荒村》視為一獨特又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從而對台灣人歷史性的糾葛、掙扎與願望有更多理解,那就再好不過。那正是李喬,以及許許多多像李喬這樣的台灣作家,用盡滔滔大河那樣的篇幅,所想要傳達的訊息。
您手裡的這部小說,就是從湍急的歷史河道上,勉力航行而來的一艘小船。請聽聽它從遠方帶來了什麼消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