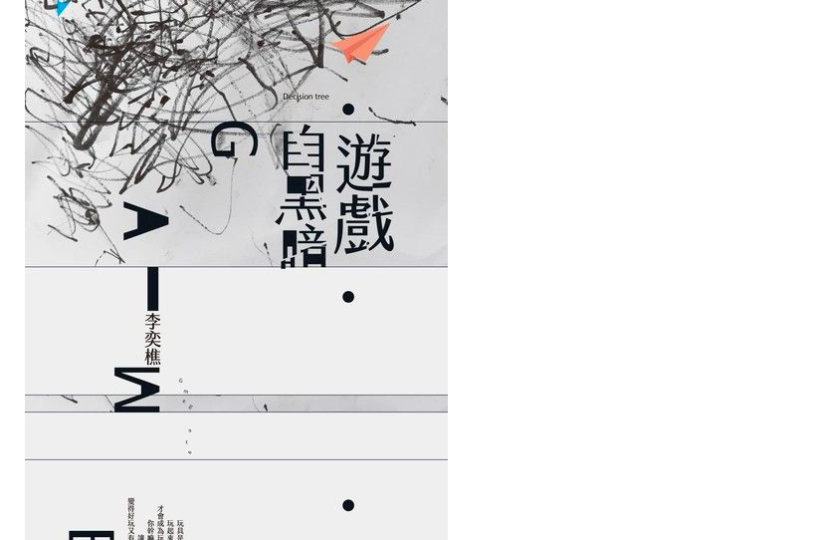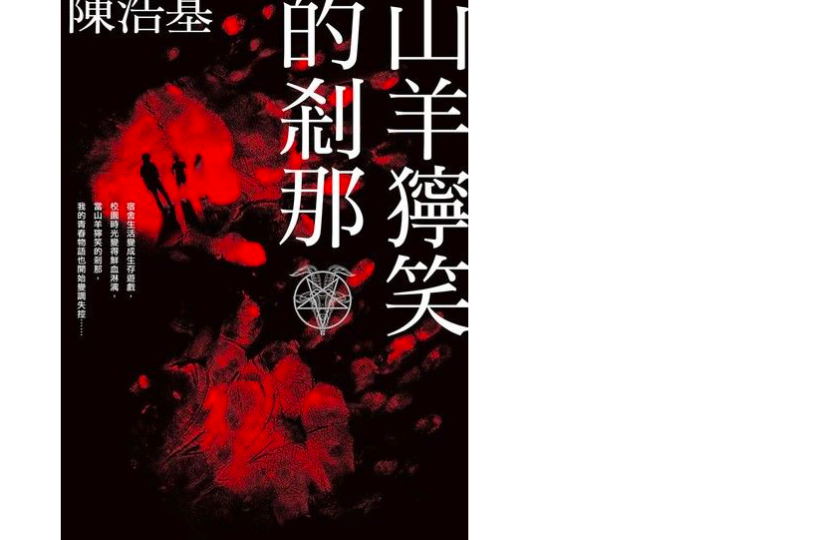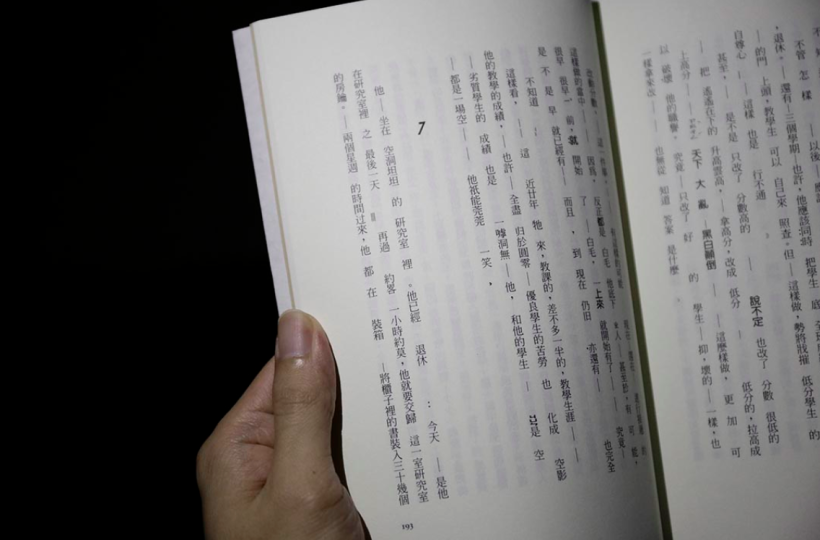我通常會在以下場合提到《桑青與桃紅》:當有人問我,台灣最好的長篇小說是哪一本的時候。當有人想要了解現代主義小說,卻又不想看一些裝神弄鬼的作品的時候。有人想讀深刻談論性別議題的小說的時候。有人想要了解外省族群的流離命運,並且不想同時攝入迂腐的黨國氣息的時候。以及,有人要我推薦荒島書單的時候。
可惜的是,當來人被勾起興趣之後,我必得潑對方冷水:「但是,這本已經絕版很久了......」不但絕版很久,而且各個版本都有或多或少的缺憾。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從發表開始就命運多舛。1970年先是在台灣的報刊連載,很快就被查禁,被迫轉往香港發表。1976年初次成書,還是只能在香港出版。接下來的十多年間,《桑青與桃紅》有了中國版、英文版(在紐約與倫敦各出一次)、克羅西亞文和匈牙利版,很抱歉,就是沒有台灣版。直到1988年,才終於有了在台灣出版的「漢藝色研」版。而現在圖書館比較容易找到的,是1997年的「時報文化」版本,但這個版本缺了漢藝色研第三章的「桑娃日記」插圖。
更氣人的是,《桑青與桃紅》英文版在1990年獲得了「美國書卷獎」,至今仍然是全世界研究亞洲區域文學、研究離散文學的必讀書目。美國的出版商很識貨,對聶華苓發下豪語:此書永不斷版。英文版永不斷版,但作為聶華苓作家生涯起點的台灣,卻是多年絕版,隱密猶如某種密教儀典一樣。
現在,這些問題,通通會在2020年版完整的《桑青與桃紅》解決了。作為長年呼喚「拜託誰來再版好不好」的、《桑青與桃紅》的密教信徒,我十分感激出版社的功德之舉。從發表日算起,這部小說已問世50年了。出版這樣一部兩個世代以前的經典作品,在記憶短暫的台灣書市是需要勇氣的。但就如我一開始所列舉的那些場合,我認為《桑青與桃紅》在過去半個世紀裡,並沒有隨著時間褪色。相反的,它不斷向我們證明,它是放到任何時代去重讀,都能獲益良多的一流小說。
《桑青與桃紅》之命運多舛,在於它一次踩上了「政治」與「情慾」兩股禁區。小說描述經歷了中日戰爭、國共內戰、戒嚴時代、流亡美國的女主角「桑青」,以及她隨著流離命運漸漸解離出來的第二人格「桃紅」的故事。家國顛覆,人身動盪,自然有政治有情慾的問題要面對。從今日的眼光看來,《桑青與桃紅》其實也沒寫什麼禁忌的東西,書中的政治觀點和情慾描寫都不算特別辛辣,純粹是1970年代的思想審查者太過玻璃心。
由此來說,當代或許正是閱讀《桑青與桃紅》的最佳時機。既然我們已經不以為怪,那就更能專注在小說本身,看出它不因時勢潮流而改變的光芒。
從大處說,《桑青與桃紅》的佈局十分細密,全書分成四大章、四小章,每一組章節都指向了中國近代的重大歷史時刻。每一大章都能當作獨立的中篇小說來閱讀,而連起來又能造成掩映勾連的效果。在最明顯的層次上,小說是以桑青的人生旅程為軸線的。但除了寫出來的精彩段落,淡筆掃到的伏線也非常有戲——我非常推薦大家閱讀時好好注意「趙天開」這個根本沒有出場的角色,不要放過那些看似不經意掃到他的段落,他其實是桑青最珍藏、以至於不太願意寫在日記裡面的回憶。(再提示一點:桑青去北平之前,人在哪裡?發生了什麼事?這也可以解釋她何以一心進入「圍城」)它在情節鋪排上的用心,是放棄了戲劇結構的台灣現代主義作品中非常罕見的。它的存在證明了「深度」與「戲劇性」並非對立,在聶華苓這樣的小說家來說,完全是可以兼得的。
在各章之內,聶華苓也展現了她鑄造場景、捕捉人心的能力。譬如在「瞿塘峽」一章末尾,一艘小舟裡面的賭博大戲,便把一群人的慾念與執念寫得極為精妙。捍衛傳統文化的老先生、充滿民間生命力的桃花女(同時,她還預示了桑青未來的第二人格)、壯悍男子流亡學生、女同志史丹,以及看似清純無害,實則堅毅逃離父權的女學生桑青,他們在戰禍之中進入了一個封閉的奇幻空間,使得家國道統通通解組,慾望就像河水退去、顯露出來的白色石頭那樣森然。或如「北平」一章,交雜著廣播與老太太絮語,令人精神疲勞的情緒勒索;或如「台北」一章的閣樓、「美國」一章的人格反覆......聶華苓擅寫封閉空間,更擅寫在封閉空間裡面勒斃了自我的人。因此,在其他作品裡堪稱名場面的場景構造,在《桑青與桃紅》俯拾即是。試舉「台北」章中的一例:
台灣是一隻綠色的眼睛。孤另另地漂在海上。
東邊是眼瞼。
南邊是眼角。
西邊是眼瞼。
北邊是眼角。
眼瞼和眼角四周是大海。
現在是颱風季節。
閣樓的小窗對著街。我們躲在閣樓窗子左邊可以看見三號房子的屋頂和圍牆。躲在窗子右邊可以看見五號房子的屋頂和圍牆。烏鴉從一個個屋頂飛過去。窗子正面對著火葬場的黑煙囪。我們不敢站在窗口,怕給人看見了。
閣樓和蔡家的房子在一道圍牆內。閣樓下面是蔡家堆破爛的屋子。
四個榻榻米大的閣樓。人字屋頂左右兩撇低低罩在頭上。我們不能站起來。只能在榻榻米上爬。八歲的桑娃可以站起來。但她不肯。她要學大人爬。
這段文字將台灣喻為「眼睛」,已是別出心裁,搭配上這一章要談論的戒嚴時代氛圍,則更凸顯了「被監視」的主題。台灣是孤島,閣樓也是孤島,人們被困在裡面,又想對外張望、卻又怕被人看見。而窗口正對面的,偏偏是「火葬場」,肅殺氣氛不言而喻。在故事中,桑青和丈夫沈家綱逃避通緝,所以被迫躲在閣樓上,時時都要彎腰走路。但在這段最後,聶華苓轉寫桑娃「不肯站起來、學大人爬」,寥寥數語,已把威權體制帶來的精神傷害勾勒無遺,堪稱台灣文學史上的經典象徵:上一代人的陰影延伸到下一代,政治的扭曲甚至在懂事以前就埋下了。雖然本章無一字提及戒嚴,但參照聶華苓因《自由中國》而遭受的政治恐嚇,「台北」章的主題是再明顯也不過了。
而在最細的文字層次,《桑青與桃紅》也毫不含糊。它的句子沒有太多纏繞堆疊的修飾,卻是鋒利如刀,簡斷的腔調中透出冷冽與俐落。比如在「瞿塘峽」一開場,就有這樣的句子:「我從黛溪的棧房窗口可以看到對河的高山,高得看不到頂──一把很尖的黑劍一直剌上去。天沒流一滴血就死了。峽裏一下子黑了。」用「黑劍」比喻「山」,然後連續幾個殘酷系的調度「刺」、「天沒流一滴血就死了」,句意既緊湊又有想像力,並且立刻定下了這一章節生死緊繃的基調。一般我們說「毫無冷場」,指的是小說情節連綿衝擊;但《桑青與桃紅》是可以做到句子跟句子之間都「毫無冷場」的。
幾年前,當我讀到傑克.凱魯亞克的《在路上》時,立刻就聯想到了《桑青與桃紅》。《在路上》被譽為「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小說中的角色們橫跨美洲大陸,在奔馳的路途中思索人生的(無)意義。《桑青與桃紅》也是一部永遠在路上的小說,它談論的是「國」「家」帶給人的傷害,談論的是一切結構崩壞之後,個體如何能保有自己。但容我僭越地說一句:或許是因為我先讀過了《桑青與桃紅》,所以完全不覺得《在路上》有什麼了不起的。這或許是因為我沒有能力讀原文,或許是因為我不了解傑克.凱魯亞克所面對的時代氛圍,所以我的判斷並不公允——
但無所謂。這樣一比,只是讓我更確定了一件事: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是放在世界文學之林,也可以比肩齊步的小說。它代表的,正是台灣文學的最高水準,是一座台灣小說家時時都要回訪的紀念碑。而希望這一次出版之後,可以讓一代代讀者都能在書店裡面找到它、閱讀它、乃至於帶到荒島上去。
(本文為《桑青與桃紅》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