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寶寶的《台灣作家全集》
2019/09/05 _抒情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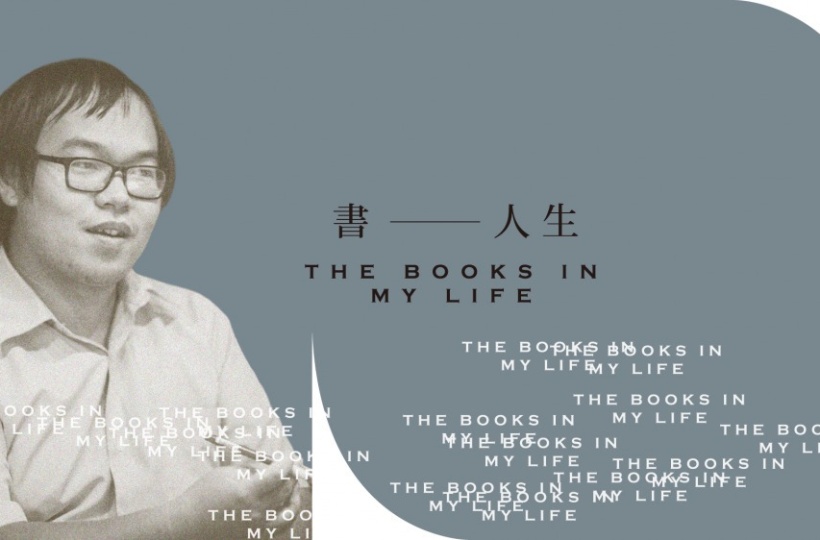
高三那年的國際書展,我站在「前衛出版社」的攤位前面,發了很久的呆。我試著走去別的攤位,但不知怎麼的,總是會被莫名的人流沖回來。吸引我的,是一套精裝硬殼的《台灣作家全集》,總共有52冊、收錄了58名小說家的作品。但對於一個高三學生來說,就算它已打了很深的折扣,也不是可以輕易下手數字。
那時我剛考完學測,成績還沒出來,但大概知道不會好到哪裡去。然而我也早早暗下決心,不管差到哪裡去,反正有什麼學校我就去什麼學校,絕不再浪費半年,去為了指考而啃教科書。不過,身為一個還算乖巧的高中生,總覺得自己還需要一個大義名分,讓自己能夠理直氣壯地放空整個高三下學期。
眼前這套《台灣作家全集》,看起來就是很堅固的理由。我不是以後想要寫小說嗎?那總要先讀夠多的小說吧?而且這一套還全是台灣小說家的作品,剛好可以探探前人玩過什麼,還有什麼未開發的領地可以去插旗子的?
念頭到此,我立刻鑽出會場,找了一台ATM。一狠心,就把存款裡面僅有的數字全部提了出來,走回前衛出版社的攤位。那是我高中三年,投稿文學獎的最後一筆獎金。錢付出去的瞬間,我就要跟整個寒假的強檔電影說再見了。
老實說,當時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買了什麼。一直要到很多年後,我才能真正理解這套書不但在物理上很重很硬,在歷史上也是份量十足。這套書的出版計畫於1990年啟動,1993年大致完成,距離解嚴不過二到五年;也就是說,它出版於解嚴寶寶我本人二歲到五歲期間。在解嚴之前,「台灣文學」、「台灣作家」這類冠著「台灣」頭銜的事物,一律都是有叛亂嫌疑的禁忌詞彙。因此,它笨拙的叢書名稱「台灣作家全集」,實際上帶著一種破繭而出的熱情:
你看,我們台灣人可以說自己是台灣人了。
我們台灣人有自己的文學。現在,文學史要列陣而來了。
這套書的召集人是戰後台灣作家的精神領袖鍾肇政。為了這堂堂正正的「台灣作家」四個字,他努力了將近三十年。在戒嚴時代,他編了好幾套實際上就是台灣作家全集,但總是要在書名上動點手腳的叢書,以免被滿街晃盪的特務抓走。1965年,他編了《本省籍作家作品》10冊、《台灣省青年作家叢書》10冊;1979年,他編了《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8冊。就像電影《賽德克.巴萊》裡頭的莫那魯道偷藏火藥一樣,一點一點把日治時期和戰後的台灣作家作品收集起來,然後用「本省籍」、「台灣省」、「光復」之類的偽裝網蓋好。等到解嚴之後,禁忌全開了,要編一套堂堂正正的「台灣作家全集」,捨鍾肇政其誰?就算他那時已屆退休之齡,實際上的編輯工作是分由青壯輩的學者負擔,也必須由他掛名召集人。
這是歷史欠他的勳章。
然而,高三的我什麼都不知道,就把三年的投稿血汗通通換成了一疊翹課的理由。為了讓自己可以更理直氣壯地對抗大人的不以為然,我啟動了一個自我訓練計畫:我要在升上大一之前,徹底讀完這套書;每讀完一位作家,我就要在部落格上寫一篇筆記。我不但打算這麼做,還把計畫告訴身邊親近的所有朋友,好逼自己下定決心。我從日治時期開始,一家一家讀,先讀作品、再讀選集中的學者評述,然後把我的想法寫下來。
於是我度過了震驚、怨念和悔恨的半年。
「這是小說嗎?這根本沒有收尾啊!」
「這什麼亂七八糟的文字啊!」
「夠了喔,老梗你們到底要寫幾次。」
「可以不要這麼囉唆嗎?是在寫小說還是在寫新聞稿啊。」
「他們也寫太爛了吧?」
我想像中精實美好,在台灣文學史裡面發憤圖強、獲得啟發、因而在十八歲這一年脫胎換骨的計畫全盤失敗。我滿腦子都是:「台灣作家真的寫得這麼爛嗎?」這些人寫得完全不如我的同儕啊,我甚至覺得自己當下的手筆,就可以單挑一半的作家了。但轉念一想,不對啊,我平常讀的那些戰後的小說家都很神,我從他們的作品中學到非常多東西。所以,不是台灣作家都寫得爛吧?
「是日治時期特別爛。」
我找了一個讓自己安心的答案。但最初的雄心壯志已全然消磨,筆記寫到十多篇就停了,接下來順手翻過去而已。
上了大學,我有好長一段時間都沒再去動這套書了。除了第一印象不佳之外,也是因為我初次接觸到社會科學,開始一頭鑽入了新的興趣裡面。《台灣作家全集》沒有讓我脫胎換骨、功力大進,反而是每週跟著課堂進度硬讀的理論書,那些談論階級、性別、族群的論述,讓我覺得自己徹底抽骨換髓,成了一個全新的人。
大約兩年後,某個無事可做、電動也打膩了的下午,我順手從書架上抽了《蔡秋桐集》下來。蔡秋桐是我高三做筆記時,最不喜歡的作家之一,會抽到他,純粹就是因為它比較近而我的手比較短。然而當我眼睛掃過書頁的時候,突然有一股顫慄的電流通過了脊椎。
等一下。我看懂了。
那一天,我把《台灣作家全集》一本一本抽下來,隨便翻一篇就開始讀,特別是挑那些我印象中「寫得很爛」的作家。我的腦袋沸騰如滾水,無數氣泡全被攪了上來:原來這裡是在講「現代性」,原來這裡是「後殖民」,而那些我覺得老梗的,是台灣一世紀以來從未解決的農村問題、土地問題、性別問題、身分認同的問題......
他們當然老梗:因為他們是第一批指出問題的人啊。我們現在熟極而流,就是因為有他們先開始大聲疾呼。
十八歲的我覺得他們寫得很爛,這本身就是歷史的傷口。因為在1945年之後,他們的存在被抹消了三十多年。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學風格,從中國強制移植到台灣來。那些讓我敬若神明的「戰後」作家,在我眼中之所以好,是因為我從一開始就受到他們的影響,口味完全被帶走;讓文學少年如我讀了皺眉的日治時期作家,也並非本質貧弱,而是他們的文學成果完全被斬斷,沒辦法從源頭培育出頻率相近的讀者。
於是我讀歐美的現代主義感到親切,讀台灣的寫實主義反而隔閡。我那時已讀過一點全球化的理論,琅琅上口「越在地的,越國際」;但真讓我讀到在地的東西,竟真的陌生猶如異國了。家鄉成了異鄉。在自己的土地上,心靈仍然流亡。
我1988年出生,解嚴寶寶。直到20歲那年,我才發現解嚴不是一個轉身就過去的事,而是大病之後的緩慢復健。在我們沒有注意到的血管裡,戒嚴的病菌始終未除,就連最純真的文學少年,也不能免於被感染。
後來,我就成為了台文所的學生。再更後來,我出了書。我給自己一項新的自主訓練計畫,並且一樣告訴身邊親近的朋友,好逼自己下定決心:我要寫一系列的入門書書,從最初階的閱讀教學、寫作教學,談到進階的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然後,通通都使用台灣文學的案例。書寫完了,我就開發成演講教材。單堂演講不夠,我就做成系列課程。
那套花了我所有文學獎獎金的《台灣作家全集》並沒有白買。至今,我幾乎每個禮拜都還要去把某本集子抽出來,再次確認細節。有時,我會瞥到自己什麼都還讀不懂時,所留下的那些帶有怨念的記號。有些記號甚至蠢得讓我心裡的那個高三的自己,都要害羞得抱頭鼠竄了。
沒關係,我會努力讓每一個人都能讀懂的。
(刊載於「Openbook」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