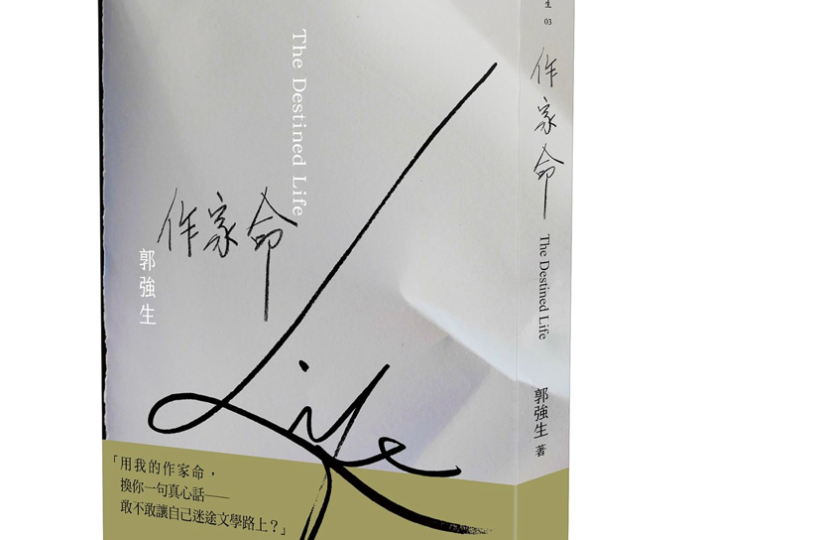平凡的都有貴重的來歷:讀張嘉真《玻璃彈珠都是貓的眼睛》
2019/09/01 _文學評論
《玻璃彈珠都是貓的眼睛》是張嘉真的第一本小說,由五篇短篇小說組成。作家今年剛滿二十歲,而在這樣的年紀、展現出這樣的筆下功夫,是擔得起「天才少女」四字的。此書的水準,與文學史上同樣被稱為天才少女的作家少作一比,便可以看得很清楚。朱天心《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浪漫有餘,但對敘事結構的掌握並不精確,時有散漫之弊;季季《屬於十七歲的》則更缺乏前者的靈動氣韻了。而相較之下,《玻璃彈珠都是貓的眼睛》最令人驚艷之處,就在於作品的純真與技藝的純熟是並存的,並不需要仗著「少年情懷總是詩」來掩護過關。如果要為此書的水準找一個比附對象,我會想到的是鍾曉陽的《停車暫借問》。
很多時候,所謂「天才」或「早慧」,指的是「年紀輕輕,就學會了一種成年人所認可的成熟腔調」。說得優美一些,則謂之「老靈魂」。但這種「天才」或「早慧」的標準,總讓我覺得有點可疑,彷彿某位年輕作家的好處,就在於他寫得不像年輕作家;而我們稱讚他,是因為他能夠把自己裝扮成老人。
然而,《玻璃彈珠都是貓的眼睛》的有趣之處,正與這種標準相反:它完全不掩飾自身的「稚氣」,甚至大大方方地以這樣的「稚氣」貫穿全書。從大處說,五篇小說全部都是校園、愛情,題材平凡到不能再平凡,不像常見的「早慧」文藝青年,會去試著挑戰看起來很莊嚴的大題目,這批小說真的就是在戀愛裡又哭又笑。甚至從小處看,常見的「早慧」文藝青年,大概不免沾染現代主義習氣,要把角色的名字取得極為抽象(仿效卡夫卡那流芳百世的「K」),或者用更關係的稱呼(仿效駱以軍的「妻」),來迴避真實人名的雜質感;但《玻璃彈珠都是貓的眼睛》裡的所有角色,都像是從班級點名簿裡面活生生走出來的一樣,楊正勳、溫如瑩、林菽恩、陳育薇 、董呈方......。如果我沒實際看到作品,有人跟我說某年輕寫作者是這樣寫東西的,我敢打賭有99%的機率,這些小說一定是搞不清楚狀況、連基礎裝飾的品味都沒有的新手,不可能是什麼好作品。
《玻璃彈珠都是貓的眼睛》的存在,映照出了我們這種讀者的偏見。稚氣與拙劣常常一起出現,不代表稚氣必然連結著拙劣。從大處到小處,這批小說毫不掩飾其學生氣息,我們十七歲就用文藝腔遮掩起來的東西,它們卻直率自信地推到前線:這就是此刻才有的光,你移得開視線嗎?如果三四十歲有三四十歲的精悍、五六十歲有五六十歲的厚實,那沒道理二十歲不能有二十歲的風采。只是技藝熟成通常需要時間,二十歲的迷人之處,往往沒有足夠精確的筆力去描,時間一過了就多少帶有後見之明的昏黃。而《玻璃彈珠都是貓的眼睛》的時光正好,筆力亦足以直擊青春的核心,「稚氣」反而成就其鮮活。
以情感的樣態而言,《玻璃彈珠都是貓的眼睛》承繼了少女小說徘徊於性別界線的傳統,除了〈撲火〉描寫純粹的女女戀情、〈貓不見了〉描寫純粹的男女戀情,其餘三篇均遊走在異同之間。套句古老的歌詞:「我還年輕 / 心情還不定。」情感與慾望自然也就沒有定式,甚至未必有堅實的「異性戀」、「同性戀」或「雙性戀」的認同。其中,〈撲火〉一篇將職場的衝突與校園社團的「學姊學妹制」交織對寫,權力與欲望的糾葛十分別出心裁。前版讀來,甚至隱隱有種女女版《蘿莉塔》之感。
而從技藝上來說,張嘉真的場景切換俐落簡潔,並且敢於拼接似而不同的段落,這使得她的小說有明快的推進力,而不至於陷入濫情的泥淖中。比如〈貓不見了〉中段,先寫董呈方與鄭如的「電影日」,一個空行之後迅速跳接到賴宇和與鄭如看的另外一場電影,僅以少數細節(角色的稱呼、是否付電影票錢)區隔,很大膽地過渡了「劈腿」的瞬間。
除此之外,〈貓不見了〉也是全書角色翻轉最有力道的一篇,作為壓卷之作,確實看得出作家成長的痕跡。董呈方一開始被建構成庸俗溫和的形象,然而到最後一段對話,卻是最能辨識出女主角「亮出來以後的樣子」的人。董呈方在感情關係上「輸了」,卻能看見「贏了」的賴宇和看不見的;而無論輸贏,都沒辦法讓人得其所求。如此一翻,庸俗的還能說是庸俗嗎?追求靈氣的鄭如、性靈絕美的「男主角」,反倒成了不知亮光所在的人。這段機鋒十足的對白,使得略微潦草的結尾也瑕不掩瑜了。如果說前四篇小說,張嘉真展現出的是一種使情感奔流而出的能力,〈貓不見了〉則更進一步,讓我們看到她建築堤壩,使情感之流迴轉滯留,終至形成漩渦的能力。
而全書最漂亮的一個意象,確實也就是引為書名的「玻璃彈珠都是貓的眼睛」了,頗能道盡這本小說集的趣味所在。在同名的短篇當中,它只是個一閃即逝的念頭,強調的是「玻璃彈珠」的平凡,和「貓的眼睛」之貴重。這正是這批小說反覆申說的:所有平凡的事物,本來都有貴重的來歷,一如我們早被前人重演過上億次的青春。只說「青春」兩個字是不夠的,唯有透過這樣的小說來展開,才能見證其精純質地。人皆有過的玻璃彈珠之年,在這樣的文字裡,才能一一還原為貴重的綠色貓眼吧。
(刊載於《聯合文學》2019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