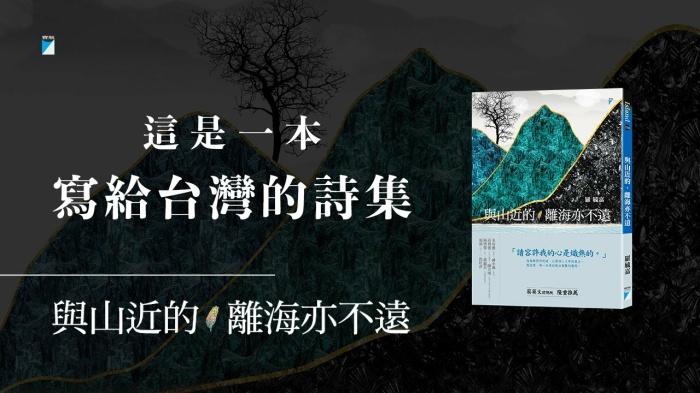說到「描寫我所深愛的土地」這項主題,有兩種常見的修辭:一種是將土地描寫為「母親」,強調它的豐饒與孕育;一種是套用「寫給XX的情書」之句式,強調濃烈的愛戀。這兩種修辭幾乎形成一種框架,許多作品在其間擺盪——有的作品沒想清楚,左右都沾,就會弄成既不慈愛也不激情的一團糨糊。羅毓嘉《與山近的,離海亦不遠》完全沒有這個問題,這本書的方向非常清楚:這就是情書,而且是限制級的、肉體與精神緊緊紐纏的情慾之書。
不只是對土地有情,而且是對土地有情欲。
從第一輯第一首的〈冷水坑〉,就定調這本詩集的風格。一開頭,便將「冷水坑」分解出「水」與「坑洞」兩個意象,並以之貫串全詩,既有「等待你再次從空中滑落到我心上的孔洞」,也有「將我洗滌乾淨 / 但不要把我熨平」。全詩激情繾綣,簡直像是一場野外的幽會——但且慢,和誰?在整本詩集裡,時常作為抒情詩喊話對象的「你」,並不見得有所實指,很多時候,更像是對著詩題所標出的那些「地方」,甚至也不是真的要寫那個「地方」,而更是以「地名」為抒發對象。也就是說,我們讀到的,很可能不是「去冷水坑幽會」,而是「與『冷水坑』這個意象幽會」。
以字生字,望文生欲,這是《與山近的,離海亦不遠》致力為之的主題與技藝,簡直是超大型的跨物種(「詩人」與「地名」)畸戀。翻開這本詩集的目錄,洋洋灑灑數十個台灣地名,但羅毓嘉並不是以一種紀錄片的態度,一一踏查摹寫各地風土民情(雖然有一些地方,看起來他是真的去過,因為選材細到不尋常的程度)。大多數時候的寫法就像〈冷水坑〉一樣,重點是冷‧水‧坑這三個字,如何與詩人的思緒糾纏交合,生下我們讀到的這首詩。因此,讀這本詩集的一重趣味就是,試圖找出「地名」與「詩行」之間暗通款曲的關係。譬如〈白沙灣〉,這個純白清透的意象,怎麼會衍生出一首性器官連綿樹葉的感官之詩?或許,人踩在白沙灣上,破壞了柔白沙地的意象,可以連結到與二至五段的「蹂躪」?而最後一行「那是我一生所能掌握的無上幸福」,也或可讀出某種張力:因為沙終究是握不住的。或如〈烏山頭〉一詩,很明顯就是以「水庫」為發展線索:
我想跟你談談那棵樹。一棵頂過了枯夏
野火,澇患,乃至於愛裡的枯水期
是你的手指在我雙腿之間,東西南北
如積雨雲般生長的樹都是時間
水庫、愛情與慾望都可能會有「枯水期」,以烏山頭水庫之壯盛,也不難想像這段關係本來的規模。羅毓嘉的寫法像是種子,可以從一個地名長出A枝椏,也能隨即岔出B枝椏,就像這首詩第三段,馬上再給出同一意象的變奏:
房間又空了一些。我想跟你談談
一個永無法釐清的缺口
是湖泊的沒水區像珊瑚,抑或
你手指讓我握著就是掌心的珊瑚?
房間又空了,當然可以是情人開始撤出自己的生活、收回他的情意;而「房間」也與「水庫」的意象遙遙呼應,如同水庫洩水,會有一個「缺口」。而當水位降低,露出的「珊瑚」(也許是一些嶙峋的樹枝,畢竟烏山頭水庫不是海洋),也就等同於愛情的殘骸了。到了第四行,此一殘骸是「你」的「手指」,一切意象就緊密扣連起來了。
種種聯想可能,正是羅毓嘉的詩作所開闢給讀者的遊樂場。〈造橋〉開場,為什麼敘事者「串起窗裡窗外兩種風景」?啊,大概是把自己造成一座橋了吧。〈貓鼻頭〉為什麼一直寫兩具「相對的身體」?啊,那是與貓(般的情人?)鼻頭對鼻頭,所衍伸出的近距離鏡像吧。甚至有些可能性充滿幽默感,幾乎就像是唐捐在搞笑,像〈林邊〉有這麼一句:「蠍子爬過使我的內褲紅腫不止。」雖然我沒有證據,但我懷疑這是從「林邊」聯想到「該邊」才生出來的句子。此類展演,到第三輯「島的音階」到達最高峰:一線天、二子坪、三仙台……到九芎林、十分,簡直就像是高雄人在背誦他們一到十號的路名。沿著地名的音階往上爬,這些詩作反覆致意「寫作」一事,也可讀作規模龐大的組詩——這倒是回到了我最初印象的毓嘉學姊:在學生時代,他可是寫過構思繁複的組詩,震懾了我這樣的學弟的。
當然,這些聯想完全有可能是強作解人,有過度詮釋的風險。不過,既然是遊樂場,既然是情欲,不冒險又怎麼會好玩呢?
而既然以「土地」為對象,就不可能與政治無涉。政治也是一種情欲,對鄰人的愛之欲其生、對敵人的恨之欲其死,其激情向來就與性愛平行。若要往這個方向解讀,第五輯各篇大概是最明晰的,基輔寫戰爭、中環和皇后大道寫香港已成灰燼的輝煌、武漢是疫情、新疆是「消失之國」的巨大象徵,青島則是台灣去年發酵至今的新興政治族群「青鳥」。這都好理解,但我更好奇的,是那些「看似沒有直接政治意涵,卻被寫出現實意味」的詩作。比如〈清境〉,這個地方是如何連結到「(沒有)戰爭的房間」的呢?難道與清境農場由泰緬孤軍開闢的歷史有關嗎?從詩集編排上來看,這首詩接著是〈合歡〉,也描寫了凌厲的戰爭場景,然後就轉接到第五輯的〈基輔〉,詩人似乎意在字面之外。「合歡」如此適合淫思飄飛的地名,羅毓嘉竟一反常態地在此寫下「像在雪地裡躺下的少年他冷卻了」,此中反差,非常值得玩味。
當然,政治也不是只有戰爭、國族這類陽剛的主題。像第四輯的〈風櫃洞〉一詩,就有著鮮明的性別主題,並且延續了這部詩集一貫的手法。詩分三段,每段第一行都是「秘密」開場,並且分別把秘密交付給「風」、「櫃」與「洞」。什麼秘密呢?從第一段開始,「鞋」也是連續出現的意象,從父親的舊鞋、到母親的高跟鞋,從「死得不能再死的父親」,慢慢接近母親的形象,終至穿上母親的高跟鞋,並且「活得不能再活」,這首詩完整呈現了敘事者追尋自我性別認同的過程。而為什麼是用「風櫃洞」這個地名,來寫這個主題呢?想必是從「樹洞」、「出櫃」這樣與「性別的秘密」勾連的意象聯想而來的吧。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與山近的,離海亦不遠》的創作思路:並不是描寫地方,而是挪用地名;並不是紀錄疆域,而是按著地圖,放飛神思。符號與現實有關,但符號不等於現實——而那小小卻必然的斷裂,就是詩意得以湧現的泉眼了。如此潮濕豐盈,如同羅毓嘉以詩歌縈繞數匝,不忍離去的台灣:這多雨多震動的亞熱帶小島。
・原文刊載於《文訊》2025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