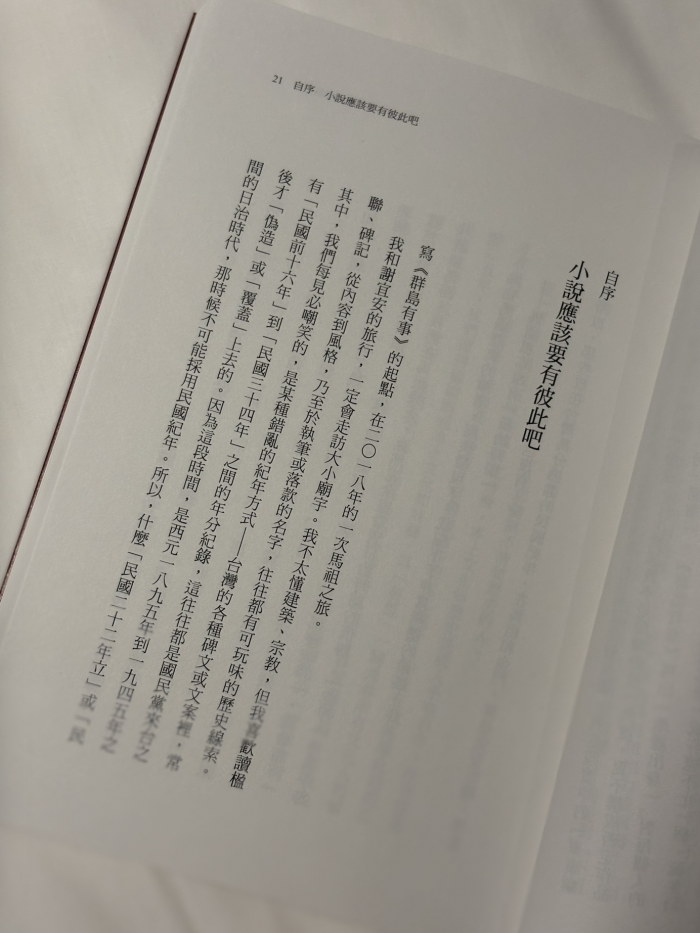寫《群島有事》的起點,在二O一八年的一次馬祖之旅。
我和謝宜安的旅行,一定會走訪大小廟宇。我不太懂建築、宗教,但我喜歡讀楹聯、碑記,從內容到風格,乃至於執筆或落款的名字,往往都有可玩味的歷史線索。其中,我們每見必嘲笑的,是某種錯亂的紀年方式——台灣的各種碑文或文案裡,常有「民國前十六年」到「民國三十四年」之間的年份紀錄,這往往都是國民黨來台之後才「偽造」或「覆蓋」上去的。因為這段時間,是西元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間的日治時代,那時候不可能採用民國紀年。所以,什麼「民國二十二年立」或「民國前三年創立……」之類的詞句,正是國民黨抹殺台灣歷史的慣技,以及證據。
我們在馬祖遊玩的幾天,就看到不少「民國十幾年」或「民國二十幾年」的字樣。
一開始,我們以為這是馬祖的政治氛圍使然——即使我不太懂馬祖歷史,也刻板地知道這裡「很藍」。所以,沒有那麼「本土化」,常有紀年被塗改,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連續看了幾天,竟然每一處都「寫錯」,我也不禁狐疑起來。國民黨雖然有抹殺記憶的傾向,但做事並不細膩,不太可能「抹得那麼乾淨」,總會留下一些蛛絲馬跡。我們在馬祖幾天,竟然完全沒看到日治時期的痕跡,「乾淨」得異乎尋常。
熟知馬祖歷史的讀者,應該發現了。我犯下了非常基礎的錯誤。
——馬祖根本沒有「日治時期」。
(不只馬祖沒有,金門也沒有。)
所以,那些放在台灣萬分愚蠢的民國紀年,在馬祖和金門,竟是完全正確、尊重歷史的。
習慣看到日治痕跡的我,才是那個搞不清楚歷史的人。
這一醒悟,讓我五味雜陳。在台灣,本土文化與歷史是前人爭取百年,好不容易才在近年有點成果,能夠進入教育、媒體與創作的主流視野。即使在我落筆此時的2025年,我們還得繼續跟視本土文化如寇讎,以「要飯」一詞羞辱所有文化人的國民黨立委對抗。然而,我們勉力爭取與守護的「本土」果實,移置到馬祖(以及金門)的脈絡裡,就會變得頗為荒謬了——對當地人來說,國立編譯館的「認識台灣」系列課本,顯然與「本土文化」沒什麼關係。
「本土」一詞本就沒有固定的內容,是隨時空位置而改變的。我理論上知道,但直到去了馬祖,我才深切認知到這件事。
而我也因此,對於馬祖的「偏藍」印象,有了新一層面的領悟。在台灣,日治時期是本土意識的源頭。因為在這段期間,「被祖國拋棄」、「與祖國分離發展」以及現代化程度超過中國各省等因素,使得台灣開始與中國分道揚鑣,「台灣人認同」也由此形成——我講得非常粗略,更縝密的版本請見吳叡人教授的《福爾摩沙意識形態》一書。這是長久以來,本土文化論的基本框架。如果這個說法大體正確,那反過來說,沒有日治時期經驗的馬祖與金門,始終對台灣的本土化浪潮無感、甚至覺得格格不入,那也是非常合理的。畢竟,在他們的歷史經驗裡,「中國人認同」是從未中斷的。台灣之「本土」,對他們來說,才更像是「外來」的東西。
###
後來我們再去金門,又是別樣的風景。
金門也沒有日治時期。但是,金門經歷了明代、宋代,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代。謝宜安這次更換了目標:他要看貞節牌坊。因為他的碩士論文,就處理到不少明清之際「節烈」的故事。金門有許多比台灣更加古老的牌坊,包括著名的「三大牌坊」:邱良功母節孝坊、一門三節坊和欽旌節孝坊。我欣然從之,因為牌坊上面同樣有楹聯可以看。結果,才到第一站「欽旌節孝坊」,我就大受震撼。
整座牌坊有四對楹聯。其中就有三對,是由進士執筆的。
進士耶。如果在台灣,鄉里之間要是出了一位,祖厝都會變成「進士第」,津津樂道上百年的等級。(……不要說是進士了,就算是舉人都矜貴得不得了)但在金門,一座附近沒什麼人煙的牌坊上,就可以隨便遇到三位。
再一細看,三位執筆的進士裡,竟然還有一位,是連我這樣只對台灣古典文學略知皮毛的人都認識的大名字:蔡廷蘭,人稱「開澎進士」,是澎湖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進士。原來他的祖籍就在金門。他雖然住在澎湖,但顯然與金門還有不少人際連帶,才會被請來「站台」吧。在我和謝宜安聊到「開澎進士」這個稱號,並且順藤摸瓜地點開「開台進士」鄭用錫的頁面給他看時,我們赫然發現:鄭用錫,台灣第一位進士,祖籍也是金門!
這一查,打開了新世界。自有紀錄以來,金門出了44位進士,參將以上的武將50人,是一個在體制內非常成功的島嶼。金門人也對此頗有自覺。金城鎮上的「浯江書院」,是科舉時代的官辦最高學府。現今,在這座古蹟的講堂裡,左右兩側的牆壁掛滿了寫有人名的木片。右側牆上,就是金門歷來進士與參將的名錄;左側牆上,則都是金門出身,拿到博士學位的名單。
如此重視「功名」,真是十分純正的漢人風味。
(做個比較:台灣歷來的進士總共33人——而且還算上了金門出身的鄭用錫。)
金門的朋友提到這些,驕傲之情溢於言表。他還補了一句:
「真要說起來,金門是全世界唯一,漢文化沒有中斷過的地方。」
台灣有日治時期,中國有共產黨和它帶來的文化大革命。而金門,這個又邊陲又上進的島嶼,反而成了封存一切的時光琥珀。雖然伴隨而來的,還有另一位朋友的諄諄告誡:如果交了金門的伴侶,結婚前要三思,這裡的家族傳統非常強大,不是台灣青年人可以想像的……。
###
知道得越多,我就越想寫《群島有事》,卻也越為難、越擔憂。
作為一名旗幟鮮明的本土派作家,我長年投注心力,研究被國民黨封藏掩埋的台灣文化。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台灣」早已是所有思考的出發點,不只是社會關懷的核心,也是一整套嶄新品味(相對於國民黨扭曲版本的「中華文化」品味)的核心。我也在多處提及,我們這個世代最顯著的特徵,就是重新連結日治時期以降的台灣文學傳統,有意識地援引、對話或批判台灣前輩作家,而不再如同戒嚴時期的某些作家,總是無視本地脈絡、全心投入西方或中國的傳統。
我自己也這樣寫。在我的文字裡,總是隱然有日治以降的歷史回聲。
我認為這套想法,是「回到了文學史的正軌」,若非國民黨橫加斬斷,台灣本該如此。每個國家的文學人,都會回應自身的文學傳統。所以,台灣作家回應台灣文學傳統,有什麼問題嗎?
然而一旦考慮起馬祖、金門的案例,一切又都不是那麼確定了。
另一方面,在近年台海局勢險峻,戰爭風險節節升高的當下,我又認為台灣人更迫切需要思考馬祖、金門的問題。在三年前的《以下證言將被全面否認》裡,我以「假想未來」的方式,寫了台海戰爭主題的小說。當時雖然也稍微提及馬祖,但還是以台灣為主要視角。小說出版後,我繼續發展同一主題,還陸續寫了一些短篇。然而,我越寫越放不下馬祖和金門,越發覺得我該換一個角度,把重心放到「政治上與台灣綁定、地理和文化上卻在海峽另一邊」的島群們……。
對我這個立場的人來說,它們實在太耐人尋味,也太棘手了——簡直就像是文學本身。本土派的我,不可能同意馬祖、金門主流的政治立場;但同一時間,我也確實覺得他們的政治選擇其來有自,並不是全然不合理。情感上,我希望能持守現有的共同體邊界,在台海的危局裡,找到一起抵抗中國侵略的可能;但在現實上,現有的軍事科技與兩岸的武裝實力,又讓我們必須承認,如果中國侵略馬祖與金門,說台灣政府「鞭長莫及」恐怕都太含蓄了些。更別說,雖然台灣人常常合稱「金馬」,但它們彼此的差異甚大:歷史悠久並以此自豪的金門,有長期被忽視、成為邊陲的相對剝奪感;而原本根本不屬一體的「四鄉五島」,則是被中華民國強制扭成一束,才形成「連江縣」這組虛幻的地理空間……。
《群島有事》便是我思考這一切糾結的嘗試。在寫作的過程裡,我越來越有一種荒謬的無奈感:其實,在台灣與中國互相對抗的格局下(或者要說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抗格局也行),馬祖與金門完全是無辜遭受波及的。先是中華民國 / 台灣需要一個前哨站,來製造守衛台海的戰略縱深,所以才把它們綁進了台澎金馬體系,並沒有問過島上居民的意見;而在軍事科技進步、政治局勢變化之後,金馬的戰略地位下降、中國統戰力度加強、台灣本土化運動興起,種種推力拉力,又使它們感到被排擠於台澎金馬體系的遠端。
如果想過這些,就沒辦法像我許多本土派的友人一般,天真地發問:「為什麼馬祖 / 金門這麼親中?」
完全可以一句話講完:是我們自己把人家拉進來,又把人家擠到旁邊去的。
然而《群島有事》,仍然是以我非常天真的一種想望為核心。有沒有可能,我們能重新塑造一個「群島」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裡,我們可以從「台灣本土文化」,變成複數的「群島本土文化」?進而,從「台灣認同」,變成複數的「群島認同」?如果有這樣想望的人,面對最嚴酷的台海戰爭局面,會遭遇到那些困難?
這便是我在幾次重寫初稿的過程裡,慢慢確定下來的核心。
而我是抱著擔憂的心情,把這本書寫完的。不是擔憂寫得好不好——這點應當交給讀者裁決,我所能做的只有全力以赴。我擔憂的是,作為一個台灣人,即使我非常喜愛群島的多元文化,也稍微做過一點研究,但我真的夠格寫這個題目嗎?即使小說有虛構的特權,但像我這樣虛構了《群島有事》那樣一種立場的夫妻,會不會是一種僭越?如果有馬祖人或金門人對我的小說皺眉,嗤笑「才不會有人這樣想」,那我是沒有什麼立場反駁的。
然而,我還是決定這麼寫了。確實,我沒有資格代言馬祖人和金門人。但是,有另一種憂心,是大過於上述擔憂的:那就是,台灣人實在太少關注馬祖、金門的議題了。在台灣熱切討論民防韌性、國防政策、國際局勢,為了漢光演習的進步而感到鼓舞時,很少有人思考過,在台灣海峽的另一邊,正有兩組情勢非常危急,我們別說不知道該如何保護、甚至都不確定該如何溝通同理的島嶼。因此,就如同我寫《以下證言將被全面否認》,是為了與讀者一同思考迫在眼前的台海戰爭議題;我寫《群島有事》,也是希望讀者,主要是台灣人讀者,可以有一個稍微靠近、稍微理解馬祖與金門的契機。
###
說到這裡,我或許該稍微交代一下《以下證言將被全面否認》和《群島有事》之間的關係。
如果順利的話,這兩本書應該會是我的「台海戰爭三部曲」前兩部。《以下證言將被全面否認》假想2040年代,台海發生全面戰爭;《群島有事》則假想2030年代,中國以「切香腸」戰術奪佔外島。這兩部小說,在情節、角色與世界觀上並無直接聯繫,可以視作兩種不同的「想定」或「思想實驗」,均為獨立作品。雖然第三部連八字都還沒有一撇,不過應該也會是另一種想定、另一種思想實驗。如此,這個系列就能探索同一議題的多種可能性。
《群島有事》本體由一部中篇和一部短篇組成。〈群島有事〉此一中篇,便是讀者接下來會看到的,由〈第一部:水尾〉和〈第二部:風頭〉所組成的連貫故事,主要角色和場景,都設定在金門與馬祖。比較需要說明的,是「外一篇」的〈水牛的影跡〉——這篇小說毫無金門、馬祖的線索,放在這本書裡,或許令人疑惑。然而,正如〈群島有事〉裡面反覆致意的,「某島的事情,應當要有另一島的人參與其中。」既然本書的核心是「群島」的共同體故事,那自然可以有金門、馬祖,也可以有台灣。
甚至,我認為必須有台灣,且必須是以「外一篇」的、「並非主軸」的形式,出現在本書。在我的小說裡,台灣已經擔當很久的主角了。直接將台灣拿掉,又彷彿在欺瞞我的視野與位置。所以,將台灣置於「外一篇」的配角、附錄地位,或許正是在《群島有事》裡,我可以稍稍做到的平衡。
最後,說回馬祖吧。這組在我多次前往之後,越來越讓我迷戀的島嶼——也正是這種迷戀,讓我不願去「想定」一種輕易放棄它們的戰爭局面吧。人在台灣的時候,我常常說自己是「一半本省人,一半外省人」。其實,當我踏上馬祖時,我仍是「一半本省人,一半外省人」,只是剛好對調位置——因為我的父親是來台很多代的福佬人,而我的母親是1940年代來台的福州人後裔。
馬祖,正是福州文化圈的一部分。即使我已經一句福州話都聽不懂了,但我還是能從馬祖話的某些腔調裡,想起我外婆說話的聲音。我自小吃慣、在長大之後越來越少見到的許多菜色,在馬祖仍然是日常的一部分。這點我就不再贅述了,讀者應該能從小說裡輕易察覺,我對某些馬祖吃食的熱情。
除此之外,我與馬祖人還有另一重緣分:我住在桃園、八德一帶。也是稍做功課之後,我才赫然發現,原來桃園正是馬祖人移居台灣時,落腳最多的地方。我們家附近的工業區,正是1960年代之後,大量馬祖人來台工作的第一站。離我們家最近的菜市場裡,好幾家有名的蔥油餅,原來也都是馬祖移民開的。在二O二五年,我邀請父母親一同去馬祖遊玩,我順帶在那裡補完最後一點田野調查。一路上,福州人母親彷彿也回到他年輕的時候,一一點評那些我完全沒有印象的菜餚,信手捻來都是我從未聽過的,外公外婆的故事。然後他不經意提了一句:你知道嗎?桃園老家對面的那戶鄰居,就是馬祖人呀。
哇,馬祖人真是無處不在,我怎麼都不知道呢?
對呀,我們一直都不知道,一直都沒有好好問過、聽過、想過。
那就只好努力寫了。這是我即使擔憂,仍然還可以致力之事。遂有了《群島有事》——希望我的虛構不致於錯解了人心。
最後的最後,要和東莒的饅頭小朋友說聲謝謝,和對不起。謝謝你陪我們到處找餐廳,也很對不起,在你問「你們的工作是什麼,為什麼不請假留下來」以及「下次你們什麼時候會來」的之時,無法給你確切的答案。如果,如果——你在多年以後,如果能讀到這本書,不知道會不會比較能夠理解,我一時語塞背後的思緒糾結呢?
你告訴我的直升機,我有偷偷寫進小說裡喔。
是為序。
《群島有事》實體書連結
博客來: https://bit.ly/45VQshH
誠 品: http://bit.ly/3UKw78H
金石堂: http://bit.ly/4fMvo0j
讀 冊: https://bit.ly/4lCwnl3
MOMO: http://bit.ly/41ee0M5
《群島有事》電子書連結
Google Play Books: https://reurl.cc/axRGMl
博客來電子書店: https://reurl.cc/Y3GXkX
樂天Kobo: https://reurl.cc/5RVpbM
讀墨ReadMoo: https://reurl.cc/6q90bd
Amazon Kindle: https://www.amazon.com/dp/B0FN7DF24X/
漫讀BOOKWALKER: https://reurl.cc/mY73pl
PUBU: https://reurl.cc/5RVp3V
誠品電子書: https://reurl.cc/6q90GM
凌網HyRead ebook: https://reurl.cc/LnVM2K
富邦momo: https://reurl.cc/eknOp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