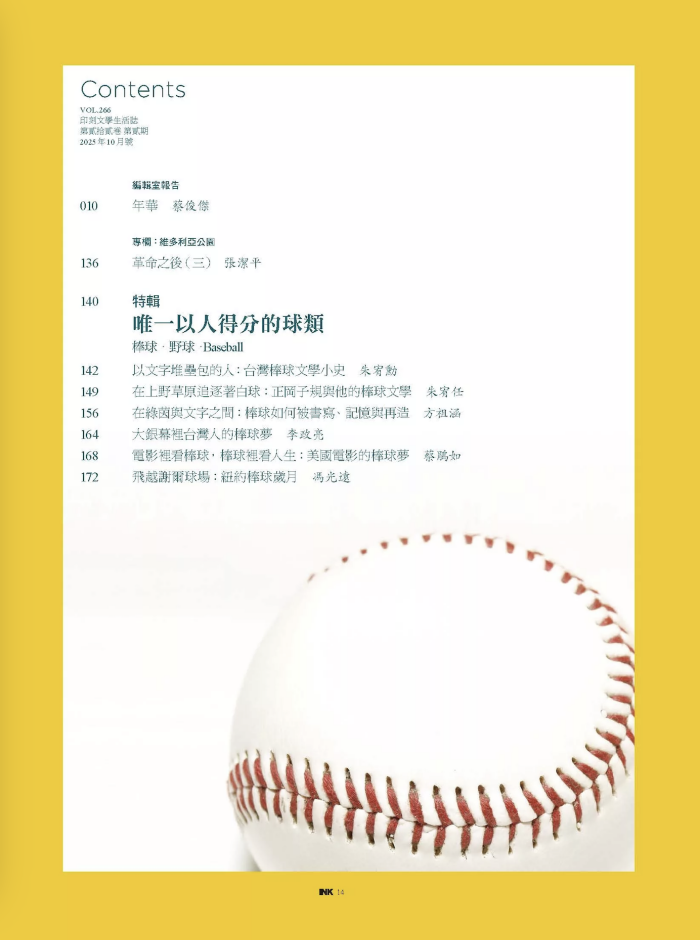1977年,小野以短篇小說〈封殺〉奪下第二屆聯合報短篇小說獎的首獎。從台灣棒球文學發展史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關鍵時刻:首次有一篇以棒球為主題,完整刻畫棒球比賽的作品,獲得了全國性的文學大獎。那是「兩大報」文學獎剛起步,注目度極高的時刻;也是「鄉土文學論戰」打得火熱,以台灣現實場景、平民生活為主題的小說,方興未艾的時刻。在這些背景交織下,〈封殺〉的出現極有象徵意義,幾乎可以將棒球文學劃分為「〈封殺〉之前」與「〈封殺〉之後」兩個時期。
在此之前,台灣人已經從日治時期開始,打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棒球——當然,在日治時期,這種運動被稱之為「野球」。時至今日,棒球場內的許多術語,仍然帶有濃重的「台腔日語」,便可見其文化淵源。比如「一壘」,在英文原文稱「first base」,但只要練過幾天球的人,都會知道教練和球員實際上會以「ファースト」來稱呼。二十世紀初期由日本人引入的「野球」,也逐漸在文學作品裡現蹤。最具代表性的,或可一讀謝汝銓的〈觀野球〉:
秋日圓山畔,野球新會盟。襟懷殊磊落,頭角總崢嶸。未肯當仁讓,翻教用力爭。相期摧勁敵,藉以著蜚聲。左右分強翼,後先接短兵。高投神鬱勃,猛襲氣縱橫。匍伏機無失,犧飛勢不驚。生還堅可陷,封殺壘能平。意態疆場壯,功名汗血成。最終輸一點,審判肅規程。
對,你沒看錯,是古典詩。這首發表於1930年代的古典詩,描寫台北圓山的一場棒球賽。「高投神鬱勃」恐怕是文學史上,對投手姿態最「中二」的描寫了。即使是對文言文閱讀比較陌生的棒球迷,也可以輕易看懂「犧飛」、「封殺」等棒球術語,顯然作者是真的會看球的。除此之外,還有王則修的〈南門野球〉四首系列,第二首是這樣寫的:
閒向寧南縱覽遊,野風獵獵角球秋。一槌打去翻身走,雙掌承來反手投。也似攻城爭霸戰,還如競馬逞雄謀。文明尚武仿兒戲,笑殺三郎醉裡休。
「一槌打去翻身走,雙掌承來反手投」描寫打者將球擊出、跑壘,守備員接球、傳球的場景,十分生動緊湊(而且十之八九是在寫內野滾地球吧)。有趣的是,不管是謝汝銓還是王則修,都採用了軍事化的詞彙來描寫棒球。謝汝銓的「相期摧勁敵」和「意態疆場壯」,王則修的「也似攻城爭霸戰」,都有這樣的味道。這反映出當時台灣人如何理解「體育競技」:這是一種「文明時代的尚武精神」,王則修以「文明尚武仿兒戲」非常精簡地概括了野球比賽的文化內涵——既帶有進步的、文明開化的意味,也帶有追求體魄、鍛鍊武功的精神。
然而,為什麼在同一時代的「新文學」——也就是以白話漢文或者日文寫成的作品,如大家所熟悉的賴和、楊逵等名家的創作體裁——作品裡,反而較少見到以「野球」為主題的作品呢?這可能就與「野球」所隱含的階級位置有關了。相較之下,「古典文學」的書寫者往往出身較高,屬於仕紳階級(比如謝汝銓就是前清秀才),觀賞球賽是他們有能力參與的休閒活動,並且他們也不忌諱在古典詩裡面描寫自己的嗜好與品味,這本來就是古典詩所擅長的。「新文學」作家則不同,無論出身高低,當時的新文學有濃烈的左派關懷,以描寫底層人民的苦境為主軸,別說「體育競技」了,他們筆下的角色,能識字、有上學的恐怕都沒幾人。因此,反而是表達精英生活情調的古典詩人們,為我們寫下了早期野球比賽的風景。
不過,到了戰後,「野球」的位階就大不如前了——這時候當然不能再說「野球」了,國民政府痛恨一切與日本有關聯之物,將之斥為「奴化」,「棒球」正式取代「野球」。雖然不是百分之百如此,然而「棒球偏本省、籃球偏外省」的運動文化現象,也於此時隱然成形。在國民政府藉由(有道德爭議的)「紅葉少棒」鼓吹民族主義以前,棒球反而從仕紳詩人筆下的「文明尚武」競技,變成了較為草根性的、帶有本土氣質的運動。戒嚴時期前半,幾乎沒有什麼以棒球為主題的名作。不過,仍然有像七等生〈午後的男孩〉這樣,寫到棒球比賽場景的小說——雖然七等生的遣詞用字,可能會讓現代球迷讀到青筋猛爆:
比賽再開始。老爺隊第一棒打了一個好球,進第一壘。第二棒的球打到外野,外野手沒有接到,第一棒進一分,第二棒在三壘。第三棒是得澤,他擊中了球跑到第一壘,第二棒再進一分。得澤在對方投球時逃跑,進二壘。第四棒擊球後在第一壘被殺死,得澤沒有進壘。第五棒打了一個很好的滾地球,對方游擊手沒有接到,他進入第一壘,得澤進到三壘。第五棒逃跑成功。第六棒進第一壘,老爺隊再進一分。第七棒打了三個空球退場,第六棒進二壘,第五棒進三壘。第八棒進一壘,義勇隊善於防守,第六棒沒有進分。
「球迷」作為一種共同社群,會以自己的用語習慣來劃分「某人懂不懂」或「是不是自己人」,這是很正常的。就像現在,如果你遇到兩個人,一人講「中外野手」一人講「中堅手」,你能馬上判斷出他們是不同年代、以不同管道接觸棒球的球迷。然而七等生的寫法卻有點微妙,他能夠準確寫出「游擊手」或「滾地球」這類用詞,但又會把「盜壘」寫成「逃跑」、「得分」寫成「進分」、「出局」寫成「殺死」、。如果有球迷朋友讀到這裡,覺得被七等生詭異莫名的用詞弄到有點煩躁,恭喜你,這也是文學界的感受:七等生就是一位刻意在文字上「變造實驗」(你也可以說是「故意亂寫」),因而在文學史留下一席之地的現代主義作家。他的作品不見得好看,但一定特別。把「揮空三振」寫成「打了三個空球退場」,還不特別嗎?地球上誰會把「揮空」講成「空球」啊。
幾乎可以說:直到小野〈封殺〉的出現,台灣才終於出現可以讓球迷感受到比賽氛圍的「棒球小說」。這篇小說發表於1977年,距離職棒聯盟成立還有十多年,但卻預言般寫下了困擾台灣棒球數十年的「簽賭」主題。小說中的少棒選手家境貧困,父親下了重注要他輸球。一面是自己與隊友的棒球夢想,一面是父親賭輸便可能家破人亡,在九局下半,代表超前分的主角擊出一支「歐把」的安打。然而,他沒有依照常理,停留在二壘或三壘壘包,而是不顧一切跑向本壘,看似是積極搶分,實則是將生命難題交給對手,最終在本壘前出局。小說的情節、文字與象徵構思都很漂亮,只有一個問題,一個球迷一眼就會看出來的問題。
——結局的出局,並非小野引以為標題的「封殺」,而是「觸殺」。
〈封殺〉實在是一個太有意義的案例,可以反映「棒球文學」(或「運動文學」)在文壇中的尷尬。就文學技藝來說,扣除「用錯梗」這部分,〈封殺〉得獎當之無愧,往後也沒有多少棒球短篇小說是在他之上的。然而,不只是小野寫錯,整個聯合報小說獎的評審逐級篩選上去,竟也沒有人發現錯誤,或者「發現了也沒放在心上」。以當時副刊文學獎的作業流程,如果任何評審或編輯意識到這個錯誤——這可是「錯在標題上的主要象徵」,很難迴避的——,在發表之前一定有機會修改,就算為了尊重作者或比賽流程而不修改,也可以由評審加個但書,表示「我們有看出錯誤但無傷大雅」。
然而〈封殺〉的錯誤並沒有被修正,就這麼以短篇小說首獎之姿發表了。如此鄉土氣息濃厚的小說,奪得向來保守、官方、偏愛反共文學與現代主義的《聯合報》所辦的小說獎首獎,本來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結果。但小說一發表,棒球迷立刻砲聲隆隆,他們不見得能細分文學技藝,卻不可能接受這麼顯眼的失誤。最後,小野公開道歉,表示確實是自己搞錯了,不過為了象徵意義的完足,他還是想保留「封殺」這個標題,請球迷原諒。
在此,〈封殺〉事件其實呈現了「棒球文學」內在的兩股張力:看棒球的和讀文學的,很可能不是同一群人,各自的社群文化與價值觀也不相同。三十多年後,當我和我弟弟朱宥任寫了幾篇棒球小說投稿時,還三不五時會看到某些評審表示:他們不看、不懂棒球,所以不選這篇了。奇妙的是,這些評審好像都不會覺得自己不夠暸解性愛、死亡、戰爭、殖民這類現代文學經典主題。棒球,似乎是一種不懂也沒關係的,「不太嚴肅」的主題。
不過,台灣史上還真的有一度「棒球與文學兩個圈子非常靠近」的時刻,那是我其生也晚,來不及趕上的1990年代。1993年,職棒球隊兄弟象舉辦了第一屆「棒球小說獎」,並且很快出版了包含得獎作品集在內的兩本棒球小說集。雖然這個文學獎只辦了一屆,但是後續出版的兩本選集卻收羅了一批水準整齊的棒球小說:《幸球場的決鬥》選錄了劉克襄、李潼、廖咸浩、楊照及侯文詠,是過去十多年的代表性作品;《棒球年代》則是「棒球小說獎」得獎作品集,那批得獎者中,張啟疆、吳明益、王聰威都是至今仍活躍在文壇的重要作家。
以棒球文學的視角來看,在「棒球小說獎」同時奪得短篇小說組首獎、極短篇組推薦獎的張啟疆,是特別值得大書特書的人物。雖然小野有歷史地位、李潼的少年小說水準極佳、劉克襄的小說也頗有風采,但單論在棒球小說耕耘之深、設思之多元深刻,張啟疆至今仍是台灣文學史第一號人物。1999年,張啟疆出版《不完全比賽》,是台灣文學史上第一本「單一作家的棒球小說集」。這不是他唯一一本棒球小說,但光是第一本書,讀者就能見識到張啟疆以棒球為核心,挖掘不同角度、不同議題的能力。獲獎的〈兄弟有約〉是一個以棒球場為背景的「恐怖份子勒索贖金」的故事,看似好像跟棒球本身關聯不大,只是借個場景;然而在小說的重要轉折處,竟是以「台灣沒有巨蛋」為關鍵,在近年巨蛋熱潮興起的背景之下,讀來別是一番風味。〈放水〉與小野的〈封殺〉遙遙呼應,是簽賭的議題,只是背景轉換成職棒之後,縱然結構類似,職棒球員與少棒選手的憂愁畢竟還是不同的。〈胡武漢與我〉解構當年的紅葉少棒故事,為了國族神話弄虛作假,敘事觀點的設置極富深意,與李潼處理同一議題的《龍門峽的紅葉》風格不同,但完全可以相互輝映。
1990年代不只是棒球小說大放異彩的盛世,以棒球為主題的新詩也開始陸續出現了。首先是1993年李進文的「棒球系列」組詩,後來收錄在他的第一本詩集《一枚西班牙錢幣的自助旅行》。這系列組詩從「投手」開始寫起,一路寫過每個守備位置,最終結束在「全壘打」,挖掘了棒球的意象可能。比如「投手」一節寫道:「在速度裡調整舞姿﹐旋轉中 / 騙過一支木棒的眼睛。」對球迷來說,這種美感想必不需多加解釋。而他是這樣描寫棒球進壘的:「當外角與內角球還在討論戰事 / 子彈已貫穿胸中的塊壘。」內外角都還沒反應過來,這球速之快可想而知;而「塊壘」的意象一語雙關,既是本壘板、也是心頭的鬱結。
此外,還有詩人羅葉。羅葉早逝,創作生命不長,但正好處於1980年代到1990年代。他在1996年所寫的〈在棒球上〉,鮮明地描寫了棒球國手所肩負的政治意涵。不過,我個人更喜歡1987年的〈右外野手〉——由於大多數打者是右撇子,所以在等級較低的比賽裡,右外野是個悠閒的位置。羅葉以此昇華成一種寧靜裡的期待:
這角落並不意想誰來說句話,
只等待:一個高飛球
或可能是高飛球的打擊聲
想起我——在這時刻,
在這青嫩如草的生命裡,
就有著這樣的期待……
一路讀來,我們可以隱然發現兩種不同的棒球書寫模式,一種是「以棒球為主題」,真的描寫選手、比賽、觀眾,如張啟疆的作品;另一種則是「以棒球為隱喻」,指向某種人生哲理,如羅葉的詩。在後者的路線上,或許值得一提的還有袁哲生的〈送行〉。這篇小說或許不是那麼標準的「棒球小說」,但已經成為現代文學經典之作的〈送行〉,其所包含的一系列疏淡渺遠的隱喻性場景,也包含了一場「棒球玩伴的失約」。這是一篇處處「落空」的小說,而棒球恰恰是那種「自己一人很難玩起來」的運動,置於文本的脈絡裡,完全能體現出作者念茲在茲的「寂寞的遊戲」。
不過,1990年代的棒球文學盛世,並沒有太長的光景。隨著職棒簽賭案的陸續爆發,棒球文學也隨之黯淡。如此氛圍的二十一世紀,似乎讓過去各種棒球敘事都難以為繼了。然而在2003年,一本堪稱奇形怪狀、非常受歡迎但卻很少受到「棒球文學史」承認的作品出現了:九把刀《魔力棒球》。作為台灣網路文學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此前的九把刀已經累積了一系列知名作品。而這本《魔力棒球》,就是「九把刀宇宙」的大會師。故事描寫狂熱且殘暴的「棒球星人」入侵地球,並且用各種手段消滅了各國職棒好手。於是,最後能在棒球場上與外星人對抗的,就只有九把刀小說裡那些身懷各種超能力的角色……。
如果用傳統的觀點來看,《魔力棒球》的比賽根本亂七八糟。比如外星人會在球場內擺上幾十個守備員,地球一方的「哈棒老大」可以直接用恐嚇的方式,獲得一支價值數十分的全壘打……。但再一細想,我們很快就會發現,正是因為九把刀本身也是深度球迷,所以才能反向構思這些離譜的情節。小野〈封殺〉全程都很寫實,就剛好搞錯一項規則,所以我們知道他搞錯;九把刀《魔力棒球》則是滿場沒一個正常人,所以我們知道他完全曉得「正常」該是什麼樣子。而且,把自己過去小說裡的知名角色,通通串在一場比賽裡,這行為不是很眼熟嗎?沒錯,這就是職棒的「明星賽」啊!更值得玩味的是,在群魔亂舞的《魔力棒球》裡,少數「正常」且有所建樹的職棒球員代表,就只剩下旅美球員陳金鋒了。這一設定,恐怕也是反映了當時台灣球迷的心情:國內職棒一片低靡,只剩下旅外球員和國際賽可以期盼了……。
2010年代之後,一批成長於「後職棒簽賭時代」的創作者,才漸漸浮出檯面。相較於前人,他們的作品往往較為灰暗,縱有熱情洋溢的時刻,但常常還是被憂愁的暗雲、理想的頓挫所淹沒。朱宥任可能是繼張啟疆之後,投注最多心力於棒球小說寫作的作家之一。2014年的短篇集《好球帶》處理了因為職棒簽賭進退不得,在榮耀與破滅之間掙扎的球員與球迷;2016年的長篇《地下全壘打王》,則將棒球夢想的興衰起落,與台灣、日本的當代關係連結。相較於前人的作品,朱宥任有著更強烈的「生於憂患」基調,並且也呈現了簽賭背後複雜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脈絡,放水與否不再只是一個「道德是否墮落」的選擇題。差不多同一時間,拙作《暗影》也用些微科幻的方式,處理職棒簽賭的困境。
如果說朱宥任和我的筆調,是比較陰鬱內斂的文學小說風格,2020年秀霖出版的《國球的眼淚》,則是更接近類型小說的筆法。故事同樣從簽賭陰影出發,但延伸到了球員離開球場,成為少棒教練之後的故事。帶著過去的記憶,面對現在的困境,《國球的眼淚》以推理小說的類型模式展開,既有新意、也微微呼應了張啟疆〈兄弟有約〉的推理路線。2024年,陳尚季出版的《斷棒:陳尚季短篇小說集》,又將棒球小說的縱深再往前推進了一步。這本集子環繞著球場周邊的諸種人物,有觀眾、有後勤、也有吉祥物扮演者,寫法帶有「新鄉土」的樸實感,更展現了新世代創作者對「棒球」的「體系化思考」——棒球不再只有比賽、只關注選手,而是交織了各種器物與文化,因而交織了不同生命樣態的場域。
最後,我想以一部「從遠方視角寫過來」的作品作結:德裔作家施益堅的《梅雨》。德國並非棒球強國,然而施益堅與台灣人結婚、長年定居台灣後,早已隨妻子成為職棒球迷。《梅雨》描寫1940年代的台灣,以熱血的中學棒球比賽開場,實際上要描寫的是台灣人、日本人、戰後來台的外省人等等族群的糾葛。這篇小說在2021年先在德國出版,2025年才翻譯為華文在台出版;反而先成德國讀者認識台灣的管道,才讓我們看到德國作家如何理解我們。小說寫的是我們熟悉的政治主題,但筆法卻與我們習慣的作品大不相同;正如小說寫的是我們熟悉的棒球比賽,但透過施益堅的視角,我們總能感受到某種異質性氛圍。此時出現這部作品,也或有某種意義:施益堅寫作期間,正是台灣職棒終於擺脫簽賭困擾,開始以新的行銷手段找回球迷,再創高峰的時期。如果再早個十多年,我們恐怕更難想像「一位德國人受到台灣職棒吸引」這回事吧。
這一趟棒球文學發展小史,在此要告一段落了。就台灣文學史整體的規模而言,棒球文學並不算非常強盛的一支,數量頗為有限。然而,如果考慮這一小支隊伍的平均水準,雖然並非壓倒性的超級強隊,但也足以和一流隊伍討價還價、有來有回了。它過去有很多表現,也有很多問題。它現在有一定程度的累積,未來不見得就能一帆風順,但也有可以期待的理由。
「台灣棒球文學」這樣的表現,或許還真是恰如其分的——球迷們一定都看出來了吧,這不就是「台灣棒球」給我們的印象嗎?
・刊載於《印刻文學生活誌》2025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