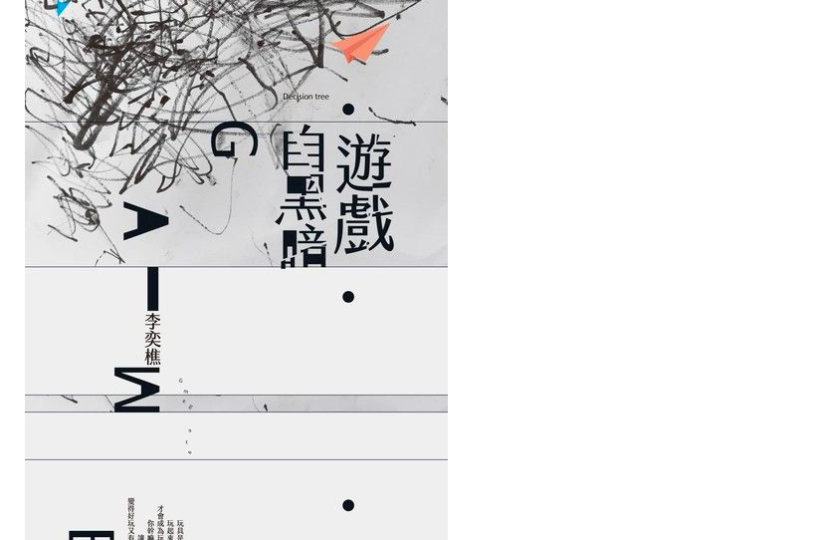電影裡沒出現的牙,及其他
我是先看了電影,才回頭去讀小說的,所以在閱讀過程中,首先注意到的是小說有、而在電影當中沒有出現的若干設計。最醒目的,自然是「牙」這個意象。第一組牙,出現開場。小說的開場和電影開場的第一幕大致相同,都是耿良辰贏了第八家武館,在咖啡店裡再次羞辱手下敗將。這個場景之所以重要,也正是因為「第八家」已到了這連串踢館的極限了——是規矩的極限(踢了八家就能開武館),是歷史的極限(從來沒人能踢八家),也是人情兇險的極限(天津幾乎一半的武館被挑,整個武行都不可能再忍耐)。而耿良辰在這個節骨眼上過份羞辱對手,結構上就注定了這個人物的結局。
但有趣的是,小說與電影的開場,除了電影版多了一位戲份吃重的鄒館長之外,最重要的差異就是耿良辰的牙。當他挑釁眼前的拳師,對方要求再比一次時,耿良辰輕挑地說:「這個月比武多了點,門牙给打鬆了,想再比,您得過十天,容我的牙長牢點。」這句話在這個場景裡,當然是更進一步的挑釁,於是迅即交手,耿良辰再次擊倒對手。以此為引子,小說版帶出了另外一個細節:對手被擊倒後,同伴立刻上前救治,耿良辰讚嘆了一聲,對手衝口而出:「這算什麽?練拳的都會。你師父沒教你?」從耿良辰的反應看來,他確實是沒學到救治的手法。在此,電影與小說又分岔開來了——在電影當中,大約在第七家武館(或更早)的時候,耿良辰似乎就已經盡得真傳(「去吧!你強過我當年。」),但在小說的第八家武館之後,小說家卻還多露了一個「師父仍然藏了一手」的細節。這樣的分岔,讓兩個文本的側重方向和詮釋可能區別開來了,小說中的師徒關係似乎還是沒有電影中的師徒關係那麼緊密;真正盡得詠春真傳的,竟可能是鄭山傲——那個與陳識一起設計徒弟的武行頭牌。
而「牙」這個意象,則繼續在小說中延展。幾乎耿良辰出現的主要段落,就會出現「牙鬆了,犯睏」的細節。這一方面當然是寫實性的細節,打架傷到牙是很正常的;而且正如徐浩峰在受訪時提到的,是到了《師父》的電影版,他才把比武的內容鎖定在刀技的,小說中是拳術、刀術同時都有。但更重要的是,「牙」在小說當中似乎更有一層象徵意義,指向了「習武之人的狀態」。武術奠基於肉體,肉體的狀態當然也就可以視為習武之人的狀態。因此,耿良辰「牙鬆了以後,生出老人毛病」,暗示著生命的倒數計時,身強體壯卻已近生命的暮年。而「牙疼」是沒有去踢第九家武館的理由,也就給了武行醞釀陰謀的時間。到將死之時,耿良辰決定不現身去嚇唬茶湯姑娘、並且最後一次去推腳行的腳車時,他「捂嘴,鬆的牙似乎長牢了。」當然,這並不是要說耿良辰還有生機,而毋寧更是迴光返照、對自己的人生做下了最後也是唯二個重要決定。到了這一刻,他終於不再是那個搞不清楚師父意圖的徒弟了,而是一個能對愛人付出深情、也決定了自身歸屬的腳行人(而非武行人,所以在小說中,也沒有腳行說要找武行報仇的情節,因為耿良辰已經以行動決定了自己與武行斷開)。
小說中的鄭山傲也以牙的好壞象徵他的盛衰,還是武行頭牌的時候「以跟小伙子比賽牙剥甘蔗皮聞名,一丈長甘蔗能剥四根」;然而被徒弟林副官暗算後,一開口就「露出三顆新鑲的金牙」。在電影中那句傷心至極的對白:「他買走的是我一輩子的名聲,幹嘛不要?」在小說中是帶著一點滑稽感的,因為說這句話的時候,鄭山傲已經缺了三顆門牙。
這個細節,也出現在小說中的茶湯姑娘,她有著「一口齊整的牙」,耿良辰因而「有一點喜歡她吧,喜歡她的牙。牙的質地和牙床的鮮紅度,顯示出她遺傳優良,有一條長長的健康的祖先譜系⋯⋯或許,服從於健康,他和茶湯女會吸在一起,結婚生子。」比起電影當中,現代觀眾比較直觀能夠理解的浪漫愛模式,這樣「務實」的愛情,毋寧才是更寫實主義的,符合現代婚戀神話全面浸透中國以前的樣貌。
整體來說,我認為電影版的《師父》是比小說版更優秀的作品。但「牙」這個象徵的設計和串連,是小說當中少數比電影更細緻之處。或許是因為透過影像,角色們的身體感已經非常強烈了,他們身姿、動作、節奏都能很豐富地展開,「牙」這個意象即使加進去了也無法生色太多;但小說不同,用純文字去追寫動作是非常難討好的,因此小說中的武打細節非常少,取而代之的是這樣一口強硬的、酸疼的、貫穿全篇的牙。除了角色的肉體,這也連結到了「師父」陳識在小說中的武器「日月乾坤刀」。這是「最擅防守的刀」,它「手握部位裝有月牙形護手,月牙尖衝外。如果敵人兵器突破了两頭的刀,攻到近身時,仍可用月牙對拼」,防守的最後一道關卡,是「月牙」。而整篇小說的情緒核心,就是陳識的這句關於「防守失敗」的內心獨白:「日月乾坤刀是天下最善防守的刀,而自己没有守住做人的底線。」連最後的月牙都被破了,陳識已然一無所有。
除了牙齒,另一處小說跟電影不同之處,在幾個陳識與妻子相關的橋段。首先是武館終於開張的早上,電影版是陳識交代了逃亡的細節,小說版則是陳識說了一串武術如何哄騙民族的論述。陳識說,他要在武館開幕上告訴所有人:「開武館,等於行騙――這是我今天開館要說的話,武行人該醒醒啦!」有趣的是,這個橋段雖然說得大義凜然,但當場的兩個人似乎都別有心思——陳識早就決定好了,他才不會說這些話,他要的是單挑武行、刺殺林副官,為耿良辰報仇然後逃亡;而陳妻表面上全聽進去了,卻也打定主意不照行程走,要親臨武館周邊,把陳識圈在她心念範圍的兩百米內(在小說中,那隻小狗其實是為了這兩百米存在的,而不是電影中的「失去小孩的傷痛」——我個人是覺得這地方,小說中的設計也是優於電影的)。這裏產生了兩組有趣的錯位:看似在最後頗有現代視野的陳識,洞察了整個武行的虛幻之後,卻仍回到了傳統的人際糾葛去,完成報仇的心願;而終於確認了自己對陳識有愛的陳妻,卻因為這份心意而跟陳識錯身而過,小說寫到陳識穿街走巷,「終於甩掉追逐者」的時候,甩掉的可不只是其他武館的追擊。不同於電影,小說並沒有留下這兩人有機會再見的暗示,或許有機會再開展出其他詮釋。但可惜的是小說的收束過於倉促,沒留下足夠的餘地來引導讀者。
從小說到電影,從簡斷到凝鍊
如我前面已略微提及的,我認為小說和電影兩個版本的《師父》相較之下,電影是比小說更佳的。主要的原因在於,我認為電影版在故事的結構和敘事的節奏上,都比小說更完熟、老練。
從人物塑造的角度來看,從小說版到電影版其實各有千秋,加添的或略去的都能看得出道理。比如小說原著是短篇,所以自然只能繞著少數幾個人物寫,而且某些人物必然寫得非常簡略,如陳妻、茶湯姑娘、林副官,與之交接的人物關係也就比較沒有著墨。與之相對的是,小說其實花了更多篇幅解釋武學背景,對陳識與鄭山傲的武學交流有較多處理。而電影時間拉長,就有更大的空間充實血肉,於是增添了鄒館長,並且將之轉換為女性,成為一個非常鮮明的角色。除此之外,陳識與陳妻的相識相處、耿良辰與茶湯姑娘的情愫,在電影中也都描寫得比較厚實。在不足兩小時的電影當中,徐浩峰處理了數量龐大的主要人物,從而非常立體地描繪了武行這個社會階層。更難得的是,每一個主要人物幾乎都有表有裡、有算計也有執著,人物塑造和每個人物命運的收束都做得很漂亮,不僅僅是陳識、耿良辰、陳妻如此,也包括鄒館長和鄭山傲。
其中,在兩作都很精彩的人物,當屬耿良辰。小說突出了一個有些認同焦慮的形象,既想追隨師父,又不想跟腳行的舊日兄弟決裂,在故事的最後被這樣的拉扯殺傷得血肉模糊。而電影中的耿良辰,更加強調了他的浮浪與邪氣,從而反襯了他對武術、愛人以及天津身份這三件事的純粹執著。從掙扎到執著,這兩個耿良辰是南轅北轍的,但在各自的文本當中都有很好的發揮。
但很可惜的是,〈師父〉似乎不是一個適合裝進短篇小說的篇幅。由於人物多、線頭多,小說被迫選擇不斷轉換敘事觀點。而因為在短篇當中轉換敘事觀點是大忌,容易使讀者「迷路」,所以又必須切出明顯的章節,減低識別和理解的困難。因此,〈師父〉當中,雖然寫得有味道的橋段不少,但全局綜觀起來,卻是顯得有些零碎、過於簡斷的。比如底下的這兩個例子。第一例是林副官殺傷耿良辰之後的對白:
林希文:「治好傷,到廊坊坐火車,南下北上,永不要回天津――這是武行對你的懲戒。」
耿良辰:「我哪兒都不去。」
林希文:「我在山東殺人二百,土匪、刁民。」
耿良辰:「我在天津活了二十六年,一受嚇唬,就不要朋友、不要家了,我還算個人麽?到別的地方,我能有臉活麽?」
這段有趣之處在於,小說版和電影版幾乎一模一樣,但在電影版當中張力十足的對話,到了小說中讀起來卻有些古怪。首先當然是過於單純的ABAB對話模組,寫起來很像是劇本的格式,少掉了大部份小說會時時穿插的動作描寫或心理描寫。其次是對白前後的斷裂太大,在沒有動作、表情、語氣等脈絡輔助下,讀者會非常難精準捕捉角色的狀態。比如這段對白裡,林希文的第二句話,雖然意思很明確,但讀來總覺得像是沒頭沒尾插入的。相較之下,電影版當中的這個段落,光憑林副官和耿良辰兩個演員的表現,就足以使這四句對白之間的裂隙潤滑起來,也生色不少。
除了對白,在小說版的場景調度上也有類似的問題:
陳識今日是館長,作為一地之主,陪坐在林希文右側。他突然站起前行,掀開銀幕,從祖師神龕上取出一柄刀。
日月乾坤刀。陳識:「有武館,便有踢館的,我來踢館吧。誰接呢?今日我是館長,只好自己接自己了。哈哈。」
場面不祥。總有自以爲是人物的人,一館長起身打圓場:「哈哈,您這是逗哪門子的樂子啊――」旁座人制止了他。
比較這個段落和電影當中調度,更可以看出影像的優勝處。在電影裡,透過場景的剪接,就不需要有「突然站起前行」這類比較冗贅的敘述,更能有「突然事態急轉直下」之感。而在引文第二個段落和第三個段落的開頭,更是在文字上略欠斟酌。僅以一個詞、一個極短句寫開一段,後面又立刻接一名人物的對白,連續重複兩次,節奏被切得很零碎。這個場景希望營造一種詭譎的緊張感,但在這種節奏下,緊張感是無法累積的,要不就是刪掉更多細節,讓節奏明快;要不就是把每一個細節稍微加長,製造懸宕。相較之下,在影像中,只要陳識持刀往螢幕前面一站,我們自然會看見日月乾坤刀,無須多費筆墨;「場面不祥」也可以從畫面中人們的表情營造出來。
此間既有差異、也有類同。類同之處,在於徐浩峰的美學是以「簡」為上,傾向於不做過多的情節交代,而代之以比較快速的場景跳接,就如同他在受訪時提到、以及電影中的武打片段所展示的:近身搏擊之時,就只是一刀之間的事情而已。然而這種「簡」並不容易,如何做到藕斷絲連而不是一刀兩斷,就是故事能否流暢的關鍵。更進一步說,這種「簡」的美學,是每一個場景都不做到滿的,因此最好的狀態,是能不能找到一個情節猶有留白、情感卻已然飽滿的時機來煞停。做不好的時候,這會形成「簡斷」,時常讓讀者或觀眾覺得前言不搭後語;做得好的時候,那就是「凝鍊」,在有限的文字或畫面之外,彷彿還有無限的心思在流動著。
就此而言,從小說〈師父〉到電影《師父》,我認為徐浩峰確實從「簡斷」抵達了「凝鍊」之境。
(刊載於「BIOS month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