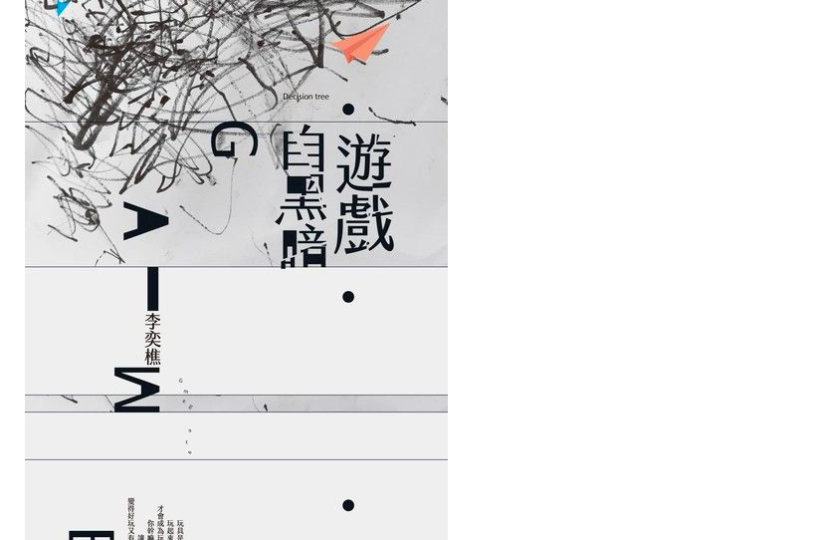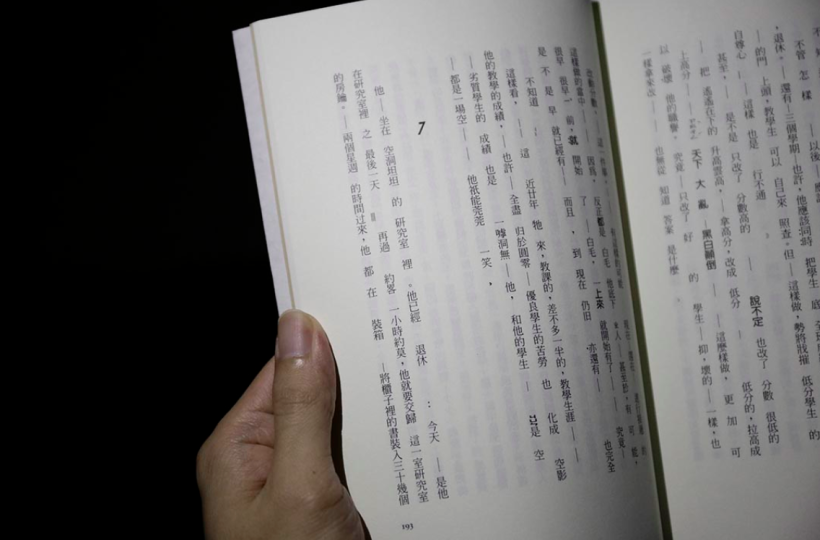若來票選文青廢文最常用的成句,「無以名狀的哀傷」一定榜上有名。雖然沒有詳細考證,但感覺源頭應該是夏宇吧。這個成句太好用了,當人們沒有辦法、或懶得想辦法去捕捉比較抽象的感覺時,只要祭出「無以名狀」四個字就好了。反正就是有,我說出不來,我說有就有。
後來,這就變成了一條小小的,我讀散文的私人標準。我不喜歡那些拿「無以名狀」當擋箭牌的散文,那些以自己無能或不願將話說清楚的為傲的散文。我偏狹地覺得:以有形追無形,以物質性的文字固定精神性的概念,這是文學創作者的工作,無以名狀的仿效者們只是拿它當做怠惰的藉口。
盛浩偉的《名為我之物》就完全是一本「可以名狀」之書。當然,傳統意義上的抒情性仍然貫穿全書,來自生活的感懷也俯拾皆是。但盛浩偉有趣的地方在於不閃避,不曖昧,每一個句子必有資訊,幾乎沒有純粹為了修辭或美學而存在的空洞描述。這說來簡單,但在台灣的散文中其實並不多見。在這種個人性很強的文類當中,不把筆墨拿去點染情緒,就意味著真的要「有話要說」,真的看了些什麼想了些什麼(否則會連篇幅都填不滿),這就對作者的知識、觀察力和思考方式設下了一道門檻。就此而言,盛浩偉顯然輕鬆過標,眼光與筆尖所指之處都真的是值得深看的細節。
這樣的直面狀態,從開篇的〈名為我之物〉和最末的〈代跋:我的懷疑〉更可清楚得見。在這一前一後,結構上彷彿括弧一般包圍了整本書的兩篇,共同思索的主題就是「自己」。佔有書名位置的〈名為我之物〉這篇,一開始看起來只是普通的童年紀事,但走筆至中段突然冷峭、後設了起來,而有了「你開始把『我』,當成一件物品,來使用。」的轉折,開展了一段對於人們如何整飾出自己的身份,以之應對社會生活的觀察。更進一步地,盛浩偉甚至將這種整飾引伸到「武器」這麼堅硬的意象上來:
所以,「我」,是什麼?「我」自古,就是兵器,是一把活生生的兵器。你得學著如何跟「我」相處,以便每日揮舞;且不只是你,人人也都憑自己的招法,使著自己的兵器。於是你與「我」,離得太遠,無以防身,靠得太近,則斲喪自己。你揮舞著「我」,他揮舞著「我」,人人揮舞著「我」;就在與其他的「我」一回又一回的過招裡,你們彼此撞擊,產生火花,發出尖銳的聲音;時而他人承受「我」,時而「我」承受他人,互相磨損,而「我」,從鋒利,變得滯鈍⋯⋯
「我」被外化、物化、工具化了,與自我的本質(如果有的話)油水分離。由此切入,這本散文集的所有篇章,都添一分文字以外的趣味來。敏銳的讀者必然會想到前幾年關於散文的「真實與虛構」論戰,此一爭論核心的倫理命題,便是「散文應當誠實」。但是,怎麼樣才是誠實呢?盛浩偉一上來就給了一個打破砂鍋退到底的答案:那就是誠實地承認自己無法誠實。要是讀者想在文字裡找到散文家的「自我的本質」(如果有的話),就會看到盛浩偉這個抱歉的微笑。
以這篇開卷,後面所有樸實勤懇的諸篇「散文」都有了至少兩層讀法。第一層當然是直接的意義,去讀文章所感所論之事。第二層是提醒讀者發問:這篇文章的「我」是什麼狀態呢?是武器嗎?是工具嗎?當他不經意閃現出鋒利的智慧,卻毫不留戀地一沾即走時,這到底是瀟灑還是欲擒故縱?當他羞澀、謙抑的時候,是在回應文類要求還是真的有此心意?還是在某些時候他真的卸除武裝了,你卻反而看不出來?
這兩篇首尾括弧的文章,成為了「強制出戲」的形式裝置。盛浩偉的小說也寫得很好,他必然很清楚:不動聲色,悄悄啟動故事,才能讓讀者「斷絕雜念」而入戲。此理在散文也通,甚至可以這麼說,散文的「非虛構」性質、散文的私密腔調,更容易讓讀者失去戒心。於是,弔詭地,散文反而成為更容易上下其手的文類。而盛浩偉的決定就是先斷了方便法門,使得更深層的思考成為可能。一旦讀者有所警覺了,作者也就少了含混的空間。
延續這樣的思路,整本書的篇章雖然長短錯落,看似隨興,但從編排方式到各篇的寫法,始終有一種清晰的內在結構貫穿其中。比如第一輯從「我」的深掘開始,擴散到第二輯的「週邊他人」,然後在談論父親的得獎作〈沒有疼痛〉之轉接下,滑入第三輯的公共參與記事。最後,從台灣出發,擴及到第四輯和第五輯的日本。這是一個明確的同心圓圖像。
「名為我之物」當然不只是及於個人而已。那是把「我」放進生活,放進親族,放進朋友,放進家鄉,放進(肉身有限可及的)世界裡。這都是使「我」可以名狀的條件。
「我」作為兵器只是其中一端,真正的我遠超於此,更多人事物複雜交織。
也因此,雖然〈給XX之歌:B-side〉和〈給XX之歌:A-side〉這兩篇並不是全書寫得最好的篇章(我私心更喜歡〈Run for your life〉、〈沒有疼痛〉和第五輯那些寫日本寫得很有味道的散文),但卻是我最在意的兩篇。純讀B面時還沒有太留神,翻到A面才被嚇到:所以⋯⋯這是一個情傷的故事嗎?一段被壓抑了表達的情傷?因此在A面才成了全書唯一一篇情緒四溢,失控而不加整飾的文章——在那冷靜的觀察者背後,還有另一個被傷口擊潰的,躲在「我」後面的人,就此浮現了。我忍不住拿這兩篇反覆對讀,想知道這中間是不是還有什麼密碼;同時大概也隱隱然知道,就算有密碼,也可能不是對我這樣的一般讀者發送、可以讀解出來的。
徒勞地嘗試幾次之後,我感覺到自己其實也沒那麼在意答案。但這兩篇的存在是令人安心的,平滑的表面終究有縫,而且還被我看到了。作為散文讀者,能親眼見到作者的情緒湧泉裂地而出的瞬間,這是多麼感人的,真摯的一刻。在那擋在作者和讀者之間的「我」,還是有暫時隱身的時候嘛⋯⋯
⋯⋯等等。真的嗎?
(本文為《名為我之物》推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