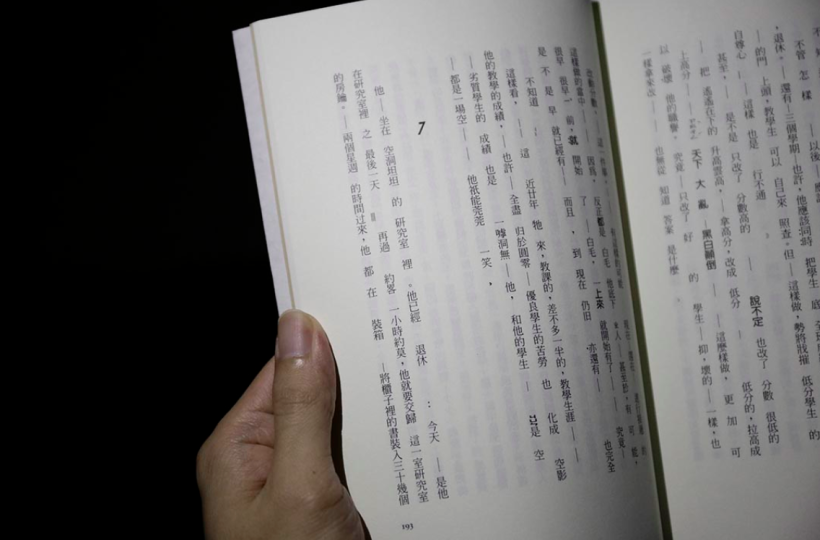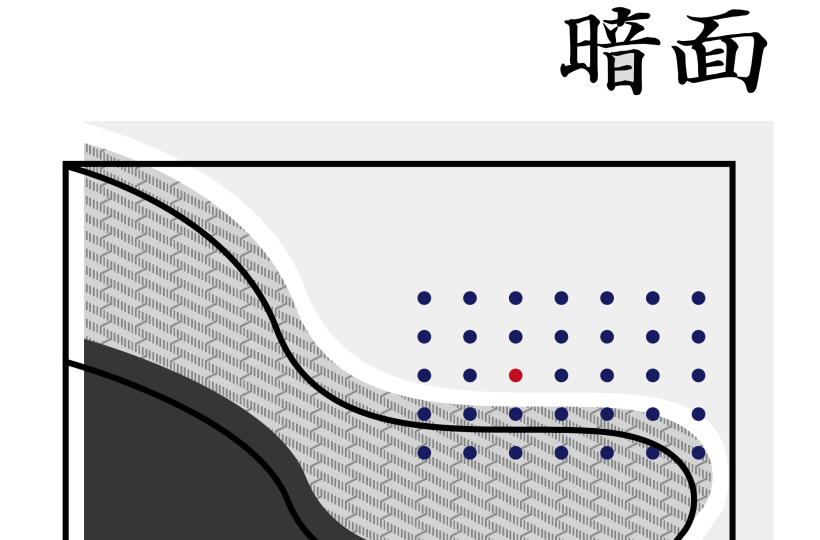為什麼我們怕讀朱天心——話可能還是得從《擊壤歌》開始說起。2010年,此書以「經典版」之姿重出,在新版的書序結尾裡,作家寫下了這段話:
這段文字饒富意義,或可作為切入《三十三年夢》或「朱天心」作為一名作家、一種文化象徵的一個開始。「你們看嗎?」是這幾年朱天心對台灣讀者提過最多次的問題,如果不說是質疑的話。從所有可見的作家訪談和文字中,反覆申述的也就是上段那些對現世的批評,說真的無甚新意,換了任何一個年長的名字都不大意外。但這段文字有趣的是最後一句:一來,2015年的年輕世代並非沒有「愛國主義」,只是愛的不與作家同一國,所以把兩造認同立場的差異說成對愛國主義的拒斥,是偷樑換柱的修辭(事實上我還擔心,部分同代人的「愛國主義」有點太高漲了⋯⋯);二來,作家在此提出了「和解」的訊號。我從不敢問,那你們看嗎?我毫無把握這些比我世故虛無、比我們資訊沛、比我們消費娛樂多樣的下一代下下代,他們怎麼看待《擊壤歌》中那單純堅定的心志和對世界純真浪漫美好的想望?對此中漫溢的愛國主義一定好教人不安吧,但,有機會能面對聆聽彼此真實的誤解,才是和解的開始吧。
這是真的嗎?我不禁驚疑了起來。
我輩讀者,多是讀朱天心長大的。從《擊壤歌》、《方舟上的日子》的爛漫時代,一路追到作家小說成就的高點《古都》、《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等作,或悼父的《漫遊者》。然而近年來,卻是越讀越怕,每有新作總忍不住想翻、但迎來的多半是傷心。作品成敗先不論,文字中的「朱天心」似乎鑽進了一個自我極化的死胡同,悲壯卻又感覺良好地往一條令人不忍的路上鑽去:拒斥台灣的一切變化,除了「我記得......」之事全不承認。在這樣的作家意志之前,我們幾乎不敢去想「和解」二字。所以與她預設答案的問題「你們看嗎?」所暗示的相反,事實上正是因為我們繼續看,所以作家與讀者都逃不出這股無望的糾纏。
(2015一整年,光憑文學作品的出版,就能引起大量讀者閱讀、在網路上發表心得與爭論的作品,除了吳明益的《單車失竊記》,就只有這本《三十三年夢》了。那是今年我臉書牆上最大規模的傷心。)
在文首那段文字的兩年後開筆、四年後出版的《三十三年夢》,確實帶來了一點點和解的契機,但只是一點點而已。我特別注意到的是在〈二OO一年 一月二十一日-一月二十九日〉這章,朱天心以留日學者黃英哲為話頭,轉接到長期推動台獨運動的黃昭堂及其弟子們,各自去念了「獨立建國後需要的OO」,表達了對他們的敬佩和同理:「我們也曾為了『反攻大陸』之後的建國做了諸多興趣之外的努力。」更進一步提到,「儘管我們對過去的認知和解釋未必相同,對當下的體會不同,對未來的判斷和主張更可能南轅北轍,但是世上有英哲和連根藤這樣對信念堅持信守的人在著,比一些曾經的友人思之要叫人溫暖不寂寞些。」(p.302)這是我印象所及,朱天心最正式對獨派陣營釋出善意的文字。而在描述參加社民黨、參加「族盟」的諸段落中,我們也時能看到一些黨外的名字閃現,想來並非孤例。
於是我們可以想像,一向被誤認為「老靈魂」、實則一直是寒臉好強的少女態的朱天心,應當覺得十分委屈吧:為什麼你們獨派還是對我一點好感都沒有?我釋出的善意難道還不夠嗎?我和這些獨派人士互相體解的情誼,難道還不足以辨明什麼嗎?這些委屈一直沒解開,終究凝結成一「怨毒著述」的情意結,與認同政治、身份政治纏繞不清:「一定是因為我的統派 / 外省身份,你們這些閩南沙文主義者 / 親日者才這樣對我吧?」於是遂有了大段篇章,寫她參與選戰和族盟的段落,那是抗議、反擊,也是自我辯護。
也許問題就在思想訓練
也許作家是釋出善意,也許作家是心有不甘,然而弔詭的是,這些段落的書寫策略與思路,正好再蹈了那個我輩讀者怕讀、她認為是「誤解」然而我們心知毫無誤會可言的路線。這樣說或許有些殘忍,但也許——有沒有一種可能是,這位被定位且又自我極化為「外省作家朱天心」,乃至難以與他人和解的小說家,真正的問題其實不是出在「外省作家」的族類標籤上,而正是出在最後那個主體本身,在作家本人的思想和風格裡?
從《三十三年夢》裡,我們可以看到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第一個比較浮面的層次是,如果我們透過這本書(和其他的著作)去認識朱天心,我們會看到一位對社會生活的理解時而無知天真,時而又計較過頭的,矛盾的作家形象。比如她熱愛逛遊日本的寺廟,卻又多次抱怨為何要收門票,不如拿同樣的錢換咖啡喝;也至少完整寫了兩次天龍寺和尚持名牌行頭追求同行女子,認為此非清修之人所應為。但既然來回日本這麼多次,焉能不知日本僧侶作為一種「職業」,本來就與漢文化大為不同;而日本的佛寺之所以能養護得當,觀光收入居功厥偉?其他如寫謝海盟吃旅館的櫻花、沿路偷摘偷採人家花木;當醫師因朱西甯罹病提及此病好發於印刷工人時,她的直覺是「每天剪報觸摸的油墨之多,也大概等於印刷工人」(真正的印刷工人聽來不知作何感想)⋯⋯這些細節說來瑣碎,但建構起來的是一個離開地面,無論真假,總之是有些不知世事、不太社會化的作家形象,她仍活在大觀園的前六十回裡。
但當提及她所不喜的人事時,這位夢幻少女又會立刻換上一張傖俗計較的面孔。比如前段戲份頗多的仙枝,三十多年來,這位已罕有人知的散文作家、胡蘭成的學生,所有粗俗無禮、貪財任性的細節,在朱天心的筆下一分不少,通通掛在帳上。胡蘭成在盛夏寄信去世,敘事的當下明知是為了寄信給蕭麗紅,也硬要透過文字剪接,先多一段文字參仙枝「寫信最勤、需索最多」一本,讓讀者感受到「是她害的!」之暗示後,再若無其事地公布正解。而在這一陣子廣為流傳的,稱吳念真為「礦子」的一段文字,也是類似的偏狹狀態。
當然,我無意對這些道德判斷進行道德判斷,這不是讀者能逾越的分際。但我想說的是,透過這些文本細節,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天真得不夠天真、清靈得不夠清靈、仙女得不夠仙女的矛盾角色,而在美醜善惡並存於一人身上的時候,讀者們覺得醜惡才是本體、美善僅是虛飾,也是理所當然的。而當這樣的角色,總是站在一種審美的或道德的制高點上,對非他族類者指謫點劃時,所引起的反感也就可以料想。
而第二個更深層、我想更難有其他評論者願意當面指出的問題是:朱天心並不是一個思想訓練紮實的作家,所以當她臧丕世事、講論政治的時候,知識水平遠勝從前的當代讀者,就越來越容易看出她的淺薄與侷限。將《三十三年夢》與同樣在意識形態上不與台灣主流合拍,並且批判人物更加銳利的黃錦樹《焚燒》並讀,就可以看出真正的「知人論世」還是需要有相應的內力才能做到。不知人、也無力論世沒有關係,並非每個作家都要寫這個路數,但偏偏朱天心不知藏拙,這是她的誠實與天真。
略舉數例,比如大段抄引胡蘭成《中國文學史話》的段落,胡寫:「王猛教苻堅掃蕩其他胡族,崔浩教拓跋魏只管出兵討平塞外,皆是為將來隋唐的統一華夏清塵除道,如云為王前驅。」(p.59)這種前件必為後件之因的謬誤,把王猛、崔浩寫成能預知未來的人物,是標準的胡式胡說,貫穿其中的也正是神義論式的大漢沙文主義,但作家引得毫無疑慮。或在論及自己的「邊緣」位置時,引用了薩伊德的《知識份子論》自況,然而並未認清薩伊德的發言脈絡,在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人的結構裡,朱天心所持守的外省身份,在歷史上其實更近於後者。而談到1990年代日本金權政治結構後,又話鋒一轉,譏嘲她最討厭的「台灣總督李登輝」,想必是非常慣熟這種政治,才會放任台灣的黑金橫行;這說法也許結論是正確的(放任黑金政治),但推理過程匪夷所思,畢竟李登輝此前好端端的窩在國民黨內,若真要探究黑金政治的「淵源」,恐怕還輪不到1945年就離開台灣的日本人。
因此,當她反擊年輕時追隨到現在的兩大標籤時——「資產階級」與「(外省人中的)既得利益者」——,所做的辯駁會一向的如此慘不忍睹,也就有了根本的原因。事實上,作家很可能並未狡辯,而是她真的不知道這幾個概念是什麼意思,有什麼樣的分析效力,那就更遑論反身思考自己的位置。她對「資產階級」的反擊不是論證自身的階級屬性(其實我覺得這算不上什麼攻擊,文學本就餘暇產物,作家承認自己的資產階級位置有什麼大不了?),而是小學生式地反指批評者:「你們不也是?」而對於「既得利益者」的辯解,是說自己沒有入過國民黨、然後同樣小學生式地指稱陳水扁和劉克襄都入過國民黨,最後才說自己已開始補修「台灣學分」。
文學的盤整
這樣的思路,其實從未認真面對「議題」本身,而將人的不同處境、位置、結構和選擇化約成簡單的私人恩怨。只有「不跟你好了」的喜惡,沒有議題,幾乎就是《三十三年夢》唯一的價值判斷標準,愛之即是、惡之即非,這樣的寫作帶有強烈的抒情性格,或許不該以世俗常理度之,但偏偏作家又多次自況「理性」。此中張力,或許可從作家念茲在茲的胡蘭成找到淵源,那樣一個純主觀的、抒情與審美的、可以憑一己之好惡(如果不說是算計的話),無俚頭地將朱天心少作與李白並列。令人感到欣喜的是,朱天心終於在此書中質疑了胡爺的判斷一次:「我始終好奇他看到的是什麼?」(p.41)但也令人感到可惜的是,作家接下來飄開思緒,只寫胡的判斷如何影響了他們的人生,而不再去試著挑戰他。從那整套胡說的世界觀中打開一條裂隙的機緣一閃即逝,而這樣不考究實事因果而僅有直觀喜惡的思維,也就熔融整本書中,再難擺脫。如同黃錦樹五千字版〈藤壺與盟誓〉所言:「胡的辯術、世界觀終究會限制了朱家姐妹。以她們的資質,在⼩說上應該可以走得更遠。」
議題並不存在,於是這就讓我們困惑了,當作家說她「只肯站在文學立場」(p.148)的時候,她的文學主張、那個立場究竟是什麼呢?除了一處提及:「美學形式在文學藝術裡相較思維、意義⋯⋯是次一等的衡量價值標準⋯⋯要做到觸及或內有思維的,才是我以為了不起的作家。」(p.177)以外,我們看到的全是負面表列。但「內有思維」是什麼?能在貧瘠的思想中種植出來嗎?難道所謂的「文學立場」就是指「不寫不看不理解那些我不喜歡的政治」?(但喜歡的政治可以寫,那仍是「文學立場」?)
也許更大的問題是:台灣的文學評價系統出了什麼狀況,會失去鞭策一位重要作家砥礪思想和知識的能力,使其陸陸續續被寶愛她的讀者超車,焦急在前方等待而不得?
是的,我們怕讀朱天心,因為讀者若在其中尋找「議題」,只能如上節一般兩敗俱傷;而我們也越來越難在她的近作中找到「文學」的經營了。兩股她最割捨不下的、以及一股她最不願妥協的力量,把她逼近了死胡同裡:胡蘭成的精神影響、來自父系的身份認同;以及台灣勢頭難止的本土化運動(依照人類學原理,如無外力變化,這勢頭才是自然現象)。如若作家能將上述批判,全視為不值一哂的俗見,專心致志發展一種美學的話,那或也自有一番風景,但總是忍不住頻頻回顧,雖也是一種有情,卻也使作品僵滯不前。
《三十三年夢》的寫法,會令人直覺地想到《擊壤歌》(而非同題的《古都》)。那樣輒起輒止,不著意佈局的形式,仰仗的就是作家思路上的輕靈,使讀者喜愛的是人格特質而非技術。但心眼已無少時柔軟,怨念更勝當年的作家,恐怕已難在這方面討得了好。因此,書中最好的篇章,幾乎都是中後段較短的幾篇,特別是那些不帶敵意的段落,比如寫黃錦樹、寫父親的亡故、寫張大春駱以軍同行的旅程、寫動保諸章。而最使人動容者,首推寫橘子貓之死的章節,無論是謝海盟磨毒果還是攜遺體重遊京都,都是能打動人心的細節。篇幅短,佈局的凌亂就不致突出;不帶敵意,就能揚抒情之長而避思想之短。
整體而言,我們仍然難見此書有太大的文學突破。當作家的書寫緊貼記憶去寫,這也就意味著思想會很大程度決定此書的狀態;而在形式上的「野放」,也就使得文章寫起來僅有熟即而流的風格標記,少有文字上的突破。比如她的讀者必然幾乎可以仿製的朱式長句:除去標點並疊合多個短句、在某些短句後方添加「的」、「著」使之形容詞化、多用「我尤愛 / 我總愛 / 一眼就愛上」之類幼小的腔調,比如:「我們一身露手露腿的夏著,顧不得原先想到河心時背背赤壁賦的只忙把手帕掏出繫頸項,一路仍只賞那漁火而不忍看那鵜鶘,只盟盟專注到、重溫她前生的營生似的。」(p.237)就此而言,〈文學答客問〉中的「藤壺」說是誠實的,此書應當視為盤整,而非高峰。
那你看嗎?我毫無把握⋯⋯
最後,我想回到第一節被我擱置的問號:和解的可能?
雖然前兩節的討論,似乎有些不容情面,但對我而言,那是一個「清創」的過程。長久以來,「朱天心」作為一名作家、一個文化象徵,已經被擁護與批判陣營雙方的大量論述淹沒,以致本體凐杳難現。而在化開「誤解」,進而「理解」、「和解」之前,這樣的開敞,我想對我們這些總是怕讀卻又非讀不可的一路追讀者來說,是必要的。在這裡我想再岔出去,說一件與文本有點關係又有點無關的事:我在自己的臉書上做了個小實驗,將《三十三年夢》中全段抄引的「族盟」宣言貼上(p.346),隱去來源,僅將「中華民國」改為「我國」,並且詢問網友是否同意這段宣言。
由於臉書同溫層的效應,向來持本土派立場的我,引來的網友光譜也就貼近於此,基本上沒有一名網友是支持泛統派者,而且多為朱天心視為難解族類的年輕世代。其中超過六成同意、不到兩成部分同意(多為對用字之商榷),不同意者不到兩成。(調查可見: http://0rz.tw/fQQFD )這個小小的調查可能沒有什麼代表性,但我希望能夠呈現的是一個訊號:我們彼此的差異,也許沒有想像中的那麼不可跨越。容或在知識上和思想上仍有落差,但這不是善與惡的鴻溝,而是理解與不理解的差別。雖然對於我這樣的讀者來說,看到連戰、謝大寧、張亞中這些名字在書中被正面評價時,確實必須勉力壓抑心中的怒火。
但我提醒自己,這本書並不只有這樣而已。它也對黃英哲、連根藤這樣的人正面評價了,它也提出了我們能夠接受的主張,從而有了和解的契機。如果真能回到切實的知識和思想裡來,理清那些歷史的糾結;如果作家能夠理解到,在比三十三年前更複雜的當代世界裡,「敢於對它[現實]有意見」,需要的不只是她認定的「誠實、正直、英勇」(p.436),還需要真正智識的視野,那和解絕非不可能的。這對作家、對讀者、對台灣的文學,會是多好的一件事。
只是,「那你看嗎?我毫無把握⋯⋯」
就算只有一點點的可能,仍是我們這些讀者想要珍惜的。
(刊載於「端傳媒」)